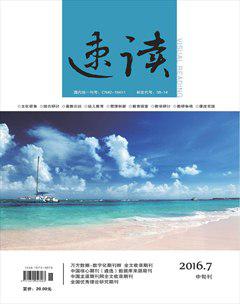試論形聲字聲符的表音功能
孟凡玉

摘 要:自東漢許慎以來,有關形聲字聲符功能的研究就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對其基本的表音功能的研究缺乏重視。本文從形聲字聲符表音的程度、示音功能較弱的原因等方面著眼,討論形聲字聲符的表音功能。
關鍵詞:形聲字;聲符;表音功能
一、形聲字聲符表音度
關于形聲字,許慎在《說文解字·敘》為其下定義:“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注:“譬者,諭也。諭者,告也。”由于造字及歷史音變等原因的影響,聲符不可能與所構成的每個形聲字絕對同音,大部分只能是相近、相似,有的差異還比較大。
(一)讀音完全一致
讀音完全相同,即形聲字的讀音和它的聲符在聲母、韻母和聲調方面完全一致。例如“皇huáng”作聲旁的有“凰、惶、蝗”等字都讀huáng;以“耳ěr”作聲旁的有“餌、洱、珥”等字都讀ěr。從表一所顯示的數據中,我們可以得知,這種完全一致的情況在漢字中還是有一定比重的。
(二)讀音不完全一致
李燕等建立的“現代漢語形聲字數據庫”,對此進行過細致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如表二。
周有光先生(1978)對《新華字典》(1971年版)的全部8075個正字進行了分析,最后得出形聲字的聲旁表音率為39%。由此可知,形聲字聲符的表音功能還是很普遍的,我們完全可以在教學、應用等實踐活動中,充分利用形聲字的這一功能。
二、聲符與形聲字讀音出現差異的原因
周有光先生在《聲旁的表音功能》一文的開頭,提出了“在現代漢字中有多少聲旁能準確表音”的問題。他把“準確表音”定為聲旁表音功能的理想標準,最后得出39%的結論。標準的形聲字,本應要求聲符的聲、韻、調與全字的聲、韻、調完全一致,但事實上,要做到這點,是有難度的。因此,實際造字時,往往是三要素聲、韻、調全同的組合較少,大多是聲、韻、調兩項同或某一項同即可。
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將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成兩點:造字原因和古今語音演變。
第一,造字的原因。
首先,按照語言的經濟原則,在選擇聲符時,不宜用生僻或繁復的字充當,為了照顧這一方面,聲符的語音條件就會變得相對寬松。其次,形聲結構的分化字,有一些在產生的時候就和聲旁不完全相同。最后,不得不考慮到漢字的書寫問題,漢字由筆畫構成,有些筆畫很復雜,若聲符筆畫太復雜,必然影響整字的認讀和書寫,因此,形聲造字之初大量使用省聲。省聲也是使聲符表音準確度的弱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古今語音的演變。
(1)聲母變化。關于上古聲母,清代學者錢大昕的結論:“古無輕唇音”和“古無舌上音”得到了后世學者公認。發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聲母的轉換,b聲母“披”、“疲”、“坡”,轉換成p聲母“波”、“玻”、“被”等。
(2)韻母變化。相對于聲母,韻母的變化從古至今,規則性都比較差。
(3)聲調變化。聲調的變化,可歸納為“平分陰陽、濁上變去、入派三聲”三條規律,涉及到入聲的變化時,會比較復雜,另三類聲調變化還是比較清晰的。但是,如果聲調與聲、韻變化交織到一起時,問題就變得復雜起來了。
另外,形聲字的用字也會使其表音功能發生變化。
(1)字形變化。漢字形體演變經歷了古文字與今文字階段,從甲骨文、金文、篆文到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種種形體變化,形體的演變使形聲字整體字形或聲符字形趨于簡化。如:“含”字中的“今”,“代”字中的“弋”,與字音已完全沒有共同之處,這些字的聲旁,現在都變成了部件,表音功能消失。
(2)簡化字的影響。從1964年發行的《簡化字總表》,可以明顯看出簡化對形聲字聲符表音準確度的影響。例如:暇—噸,郅—鄧,瑕—環。這些簡化字,已不能憑簡化后的聲符推讀整字讀音。“這類字在常用字的簡化字里就占了一定比例,無疑也大大削弱了形聲字聲符的表音作用。”
三、結論
形聲字的出現,解決了漢字同音混淆、多義混淆等問題。音義兼表的形聲字是有理據的,“它最適合表達漢語編碼的理據性。”正是由于形聲字具有很強的理據性,語文教學和對外漢語教學中的形聲字教授才更加科學、系統。因此,我們應立足于形聲字聲符表音這一基本功能,正確認識并進一步深入對于漢字表意體系的研究,逐步完善和發展現代漢字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尋求解決信息時代漢字相關問題的方法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