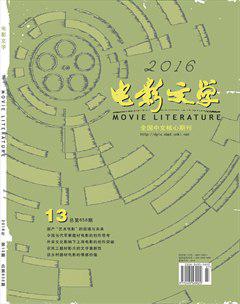蒂姆·伯頓“暗黑童話”的美學風格探析
[摘 要]能獲取好萊塢“鬼才導演”稱號者鳳毛麟角,而蒂姆·伯頓則是其中名副其實的一位,在他的藝術實踐過程中,他將“暗黑童話”的美學風格運用得淋漓盡致。“暗黑童話”并非僅為伯頓所涉獵,但就這一美學風格而言,伯頓卻是其當之無愧的發揚光大者。并且就其本人對影片的介入程度而言,伯頓已經以電影作者的姿態將暗黑童話當成了自己電影獨特風格的代名詞。文章從詭譎美、荒誕美、溫情美三方面,分析伯頓“暗黑童話”的美學風格。
[關鍵詞]蒂姆·伯頓;電影;暗黑童話;美學風格
能獲取好萊塢“鬼才導演”稱號者鳳毛麟角,而蒂姆·伯頓(Tim Burton,1958— )則是其中名副其實的一位,在他的藝術實踐過程中,他將“暗黑童話”的美學風格運用得淋漓盡致。
一、電影作者論與“暗黑童話”的起源和發展
要討論蒂姆·伯頓“暗黑童話”的美學風格,便有必要對伯頓與該風格進行定位。“暗黑童話”并非僅為伯頓所涉獵,但就這一美學風格而言,伯頓卻是其當之無愧的發揚光大者。并且就其本人對影片的介入程度而言,伯頓已經以電影作者的姿態將暗黑童話當成了自己電影獨特風格的代名詞。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特呂弗為代表的法國“新浪潮”運動電影人們提出了電影作者論,特呂弗在《法國電影的一種傾向》中指出導演應該在創作之中突破傳統的以劇本為核心的創作方式,強化自己的主體地位。[1]蒂姆·伯頓的影片可以以作者電影理論來考量,在他的電影作品中,始終貫徹著鮮明的個人風格,伯頓本人(甚至包括伯頓前妻海倫娜·伯翰·卡特)一直都處于電影創作中的核心位置。對于伯頓來說,劇本或文學原著更多的只是電影的基礎,伯頓還需要發揮主觀能動性對其進行再創作,在電影之中灌注自己獨一無二的人生見解或藝術追求,這種對于創作自由的堅守使伯頓能夠擺脫商業電影運作方式的束縛,他別具一格的“暗黑童話”美學風格也就得以不斷地在其作品中延續下去。
真正意義上的“暗黑童話”誕生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后現代主義風行整個西方社會之后。當時的世界陷于冷戰格局之中,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正在高速發展工業,而機械化與物質的高度發達帶來的統一、麻木、僵化等危害則侵蝕著人們的精神。在藝術界,人們試圖以反叛、戲仿、解構的方式來擺脫死板的現實社會,觸動處于迷失中的人們。原本甜蜜、溫馨,帶有歌頌色彩的童話電影也受到了沖擊。如湯姆·戴文波特創作的《漢塞爾和格雷特爾》等電影將童話移植到了當時的美國,人物性格也從原來單純的好壞二元對立變得更加復雜,原著之中美滿和諧的表面被導演毫不留情地撕裂。這樣的顛覆傾向一直延續至今,如亞當·艾略特的《瑪麗和馬克思》、亨利·舍利克的《鬼媽媽》等都是當代“暗黑童話”的代表。因為“暗黑童話”突破著兒童更容易接受的英雄救美、王子公主等俗套,滲透著創作者對舊有理念的質疑與對社會矛盾的觀察,因此對受眾的要求也更高,也被稱為“成人童話”。
二、蒂姆·伯頓電影的詭譎美
蒂姆·伯頓是其電影的創作主體,他在電影中實體化呈現著他本人的審美追求的同時,也有意無意地關聯著自己的人生經歷以及哲學經歷帶給他的氣質和稟賦。伯頓的個性是極為內向且孤獨的,這與他封閉、陰暗的童年是分不開的。伯頓的父母對他缺乏關心,伯頓父親在事業上郁郁不得志,而母親則因為神經質而性情孤僻另類,伯頓或是被父母禁足于房間之中,或是被交給與他難以交流的祖父母撫養,導致伯頓長期只能依靠繪本和電影,尤其是B級片來打發時光,這也導致了他有著相較于同齡人而言極為豐富的內心世界,并偏愛詭譎、黑暗、恐怖的元素。對于自己的童年,伯頓坦承:“我經常一呆就是一整個下午,我喜歡魔鬼,他們外形丑陋可是心地并不壞,他們甚至比某些人類都可愛。”[2]伯頓固守著自己的審美偏好,以至于在入職迪士尼動畫組時,感到當時迪士尼的童話風格與自己格格不入,于是在迪士尼給予他獨立執導作品的權力時,伯頓以一部充滿詭譎美感的短片《文森特》(Vincent,1982)宣告了自己對迪士尼歡樂、明快風格的全然否定和對“暗黑童話”路線的選擇。
在《文森特》中,主人公文森特·馬洛伊帶有明顯的伯頓本人的影子,在他的幻想之中,他是當時著名的恐怖片演員文森特·普萊斯的兒子,而普萊斯則為伯頓(馬洛伊)的偶像。文森特個性離群,熱衷于想象自己是一個恐怖科學家。年僅七歲的他不但在幻想中出現了大量蜘蛛、蝙蝠等容易觸發人驚慌情緒的事物,甚至還出現了活埋妻子、將姑姑做成蠟像、將狗做成僵尸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徑。而文森特本人的理智也告訴他這樣的古怪想法是罪惡的,但是奇特的念頭卻又總是鉆進文森特的腦子里,即使是站在一面墻壁面前,他都能幻想自己的影子變成某種牙尖爪利的怪物。這種精神上的分裂最終讓年幼的文森特不堪重負,他在自己的幻想中以美國著名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的方式“殺死”了自己,讓自己在所謂的“末日之塔”(實際上是母親禁足他的房間)中陪伴著自己莫須有的“妻子”的畫像長眠不醒。
短短五分鐘里,一個活在詭異、幽暗冥想之中的男孩被塑造得極為立體。更重要的是,對于文森特的長輩來說,生活是正常而陽光的,文森特是禮貌得體、富于教養的,而文森特私底下給自己創造的鬼怪世界則是無人理解的,文森特的母親因為自己的花園被挖就以自己的方式處罰文森特,卻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對文森特意味著什么。這種反差增加了影片的恐怖感。可以說,文森特最初選擇用小制作獨立動畫的方式來大展身手,正是因為動畫這種更為自由的表現方式能更好地讓他釋放自己對詭譎美揮之不去的熱愛。
三、蒂姆·伯頓電影的荒誕美
伯頓被認為是當代哥特風格的集大成者,但是他又能夠在繼承哥特離奇、怪誕藝術風格的同時,賦予哥特藝術更高的美學意義,這主要就體現在其電影中的荒誕之美上,伯頓在電影中處處樹立荒誕的情境與人物,讓它們表達某種并不可怕而是溫婉浪漫的情調氣質。[3]
例如《剪刀手愛德華》(Edward Scissorhands,1990)所給予人的更多的是一種荒誕感而非詭譎感。主人公愛德華外表奇怪,蒼白的臉上遍布疤痕,發絲凌亂而紛雜,一身黑色服裝,更為奇怪的是擁有一雙鋒利猙獰的剪刀手。但愛德華的形象并不旨在給予人恐懼感,甚至相反,愛德華有點像恐懼電影之中所謂的“正常人”。愛德華的出身是荒誕的,他是一個沒有建造成功的機器人,由于設計者的辭世,愛德華只能居住于陰森的古堡之中,在一個意外中,愛德華被化妝品推銷員佩格引入了人類世界。由于愛德華善良而純潔,他一開始受到了人們的歡迎,但卻發現他最終依然無法徹底融入人群中,尤其是在愛上了金之后,他更是發現自己的剪刀手讓他失去了擁抱愛人的權力,從此跌入了深淵。整部電影的故事框架是荒誕的,伯頓將哥特藝術之中的古堡、怪人等元素與傳統童話中天使般的少女、漫天飛雪等元素相結合,創造了一個外表怪異但是內心簡單的形象,伯頓也有意違背了“美救英雄”或“王子公主”的童話套路,讓愛德華與金最終分道揚鑣,愛德華依然不屬于金的世界,金明知愛德華就住在古堡中卻只能在年邁時感慨“我已經老了,我希望他永遠記得我年輕時的樣子”。
值得一提的是,伯頓并沒有以“審丑”的態度來勾畫審美對象。電影中的場景多美輪美奐,愛德華為人們打造的樹雕惟妙惟肖,為人們設計的發型也新潮生動,這些美全是建立在愛德華本人是一個擁有真善美信念的“怪人”基礎之上的。與之類似的還有《僵尸新娘》(Corpse Bride,2005)中被未婚夫殺害而淪為僵尸的艾米莉,她渾身腐爛,形容枯槁,然而卻愛上了活人維克多。維克多瘦弱膽小,伯頓有意將他們都打造為并非能給予觀眾美感的對象,甚至艾米莉的僵尸身份還有點陰郁駭人。艾米莉帶領維克多見識了歡樂而和睦的死人世界,維克多也多次穿越于兩個世界、兩個新娘之間,片中的荒誕感在兩人舉辦盛大的,帶有狂歡意味的婚禮時達到最高潮。最終艾米莉放棄了維克多,促使他在陽間獲得幸福,伯頓的想象空間不僅超越了生死兩界,同時也再次打破了“王子與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舊套路。
四、蒂姆·伯頓電影的溫情美
“暗黑童話”畢竟屬于童話,并不意味著電影中充斥的都是無法讓人親近的事物,它只是轉化著人們看待那些恐怖元素(如鬼怪、怪胎等)的角度,使人們對其從拒斥到接受,將不和諧變為和諧,最終收獲的是思考甚至是溫情。最為典型的便是以“父親的傳奇”為核心的《大魚》(Big Fish,2003)。在電影中,父親愛德華選擇以環游世界來度過自己的青年時代,路上他所遇到的各種稀奇古怪之人在日常生活中是容易讓人敬而遠之的,如破壞力極強的巨人,夜晚便會變回原形的狼人,共用同一個下身的連體雙胞胎姐妹,其中最為可怕的則莫過于一位有著可以預見一個人生死的玻璃眼珠的垂老女巫。但是這些令人不適的角色卻在愛德華的串聯之下成為美好的、溫情脈脈的童話。由于自己幼年時曾經在女巫眼中看到過自己的未來,愛德華始終能夠對未知事物保持熱情,并且在面對任何惡劣的現實時(如參加朝鮮戰爭,為了生計而在不同的州之間奔波,在深林中迷路等)都以“我的命運不是在這里結束的”來安慰自己,使自己保持足夠的勇氣。影片因為愛德華對污濁的現實世界進行變形而成為童話,因為諸多怪異、丑陋角色的設置而帶有“暗黑童話”的一面,伯頓通過愛德華之子威爾對這些光怪陸離之事從不相信到理解的歷程為觀眾揭示了童話的意義,即正是因為現實充滿了磨難與平淡,人們才需要給生活插上想象的翅膀,如父親最后變成大魚一樣獲得自由。然而父親的形象依然帶有伯頓電影中孤獨的,來自異世界的主人公的特點,盡管愛德華深愛著威爾,威爾卻直到父親不久于人世才真正理解父親的用心。
伯頓還有一部分電影溫情之美相較于詭譎和荒誕美的比重更大,如同樣涉及父子親情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廠》(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2005)。《查理和巧克力工廠》改編自英國作家羅爾德·達爾的同名小說。電影中愛吃巧克力的查理·巴克特參觀威利·旺卡先生開辦的巧克力工廠的整個過程無疑是引人入勝的,巧克力工廠中的一切也十分離奇,如飛流而下的巧克力瀑布,以棕色糖漿流淌而成的河,大片大片的口香糖草地等,這些都是電影作為童話所必備的奇遇性,然而這依然是一部“暗黑童話”電影。不僅威利·旺卡本人是一個有性格障礙的怪胎,巧克力工廠的多姿多彩還對應著現實社會的壓抑乏味、冷酷黑暗。如查理一家十分貧困,七口人中只有父親一個勞力,查理買巧克力的錢都是在地上撿的,但是他們一家其樂融融。而相比之下,與查理一起競爭巧克力工廠繼承權的小朋友們則大多出身于有權有勢的家庭,可以為了中獎而整車整車地購買巧克力等,也正是因為他們出身的優越使他們沒有戰勝巧克力工廠中的種種誘惑,輸給了查理。最后旺卡先生與自己的父親重歸于好,而查理則獲得了足夠吃一輩子的巧克力糖和其他糖果。影片在延續著伯頓一貫的吊詭、瘋狂、充滿玩心的風格之余還帶著濃郁的溫情。[4]
當前沖擊觀眾視聽的“大片”時代已經降臨,部分電影導演為了爭取更多的票房,追求更多的利潤而不惜將電影當成純粹的商品,在電影中更重視視覺沖擊、話題效應,而不是藝術審美性。而蒂姆·伯頓的電影卻帶有迥異于商業大片的特質,他始終以電影作者的姿態在作品之中書寫著自己的價值觀和藝術追求,在好萊塢固有的制片工廠制度中依然踐行著自己以詭譎美、荒誕美和溫情美為核心的“暗黑童話”風格,為觀眾打造出一個個難忘的童話王國,他的電影也由此成為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品,而非僅僅是一時娛人耳目的消費品。
[參考文獻]
[1]孟君.作者表述:源自“作者論”的電影批評觀[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02).
[2]Tim Burton.Burton on Burton[M].London:Faber & Faber,Revised edition,2000.
[3]孫健.黑色的純真:蒂姆·伯頓的電影世界[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8(04).
[4]王婧.《查理和巧克力工廠》的懲戒主題[J].電影文學,2010(16).
[作者簡介]黎丹(1970— ),女,廣西陽朔人,碩士,南寧學院公教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際、英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