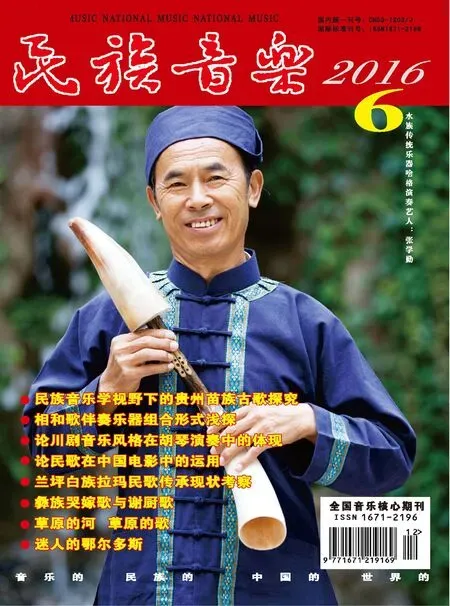相和歌伴奏樂器組合形式淺探
■權霖泓(北京市中關村學院)
相和歌伴奏樂器組合形式淺探
■權霖泓(北京市中關村學院)
相和歌的名稱,最早見于《宋書·樂志》,廣義上講,它是漢代各種民間歌曲的總稱。《樂府古題要解》曰:“樂府相和歌,并漢世街陌謳謠之詞。”“街陌謳謠”即指民間歌曲,不過這應是最初的相和歌形式——徒歌。因為民間歌曲一般都是勞動人民即興創作隨口而唱的,不可能加上伴奏樂器。在徒歌的基礎上加入幫腔即“一人唱,三人和”,叫作“但歌”。這種發展同樣受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勞動的影響,比如在勞動時所喊的勞動號子,即是一人喊眾人和的的形式。再進一步發展就成了“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宋書·樂志》)的形式。其基本特點是:一人領唱,多人幫腔,管弦樂做局部配合。“節”在這種演唱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由領唱者親自掌握。相和的意思就是“絲竹更相和”,至此為止后世所稱的真正意義上的相和歌才開始形成,狹義上的相和歌即是指這種“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的藝術形式。這種藝術形式在漢魏時得到了充足發展,不但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更是得到了當時統治階級的推崇,可謂風靡一時。但這種歌曲是如何“被之管弦”、如何“絲竹更相和”的,至今學界還沒有一個清晰的脈絡。針對現狀,本文就此問題試論一二,還望能引起學界有此志之士的興趣以共同探討。本文就以下兩個方面進行論述:
現人研究狀況
(一)音樂史專著中的相和歌伴奏樂器組合形式
楊蔭瀏先生在其《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中指出:相和歌的伴奏器樂,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曲調種類的不同,而有著出入。他認為,相和歌所用的伴奏樂器最多時有8種,即笙、笛、篪、節、琴、瑟、箏、琵琶(即現在的阮);到了南朝在南方唱奏的時候,就減少了一些。指出笛和笙是伴奏中的主要樂器,每段器樂是先以笛和笙開始,由它們在旋律的高低和花腔上做了一些變化,然后別的器樂再加進去一同合奏;在每段樂器演奏完畢的時候,還要加上一個尾聲[1]。夏野先生其著作《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中提出,相和歌的伴奏樂隊,通常是用笙、笛、節鼓、琴、瑟、琵琶、箏7種組成,有的則加篪而成8種、有的不用節鼓而改用筑等等。總的都是加用了新興彈撥樂器“琵琶”[2]。吳釗和劉東升二位先生在其《中國音樂史略》中提到:相和歌的樂隊至少應有“絲竹”(竽、瑟)與鼓。漢末三國之際其伴奏樂隊已由笛、笙、節鼓、琴、瑟、箏、琵琶等七種樂器組成。 這種樂隊實際應用時樂器的多少是靈活的,有時可不用節鼓,而用筑。認為西晉初,其樂器配置已較固定,除原用的箏、笛、節鼓外,尚有琴、瑟、琵琶與笙等,有時還加用篪與筑[3]。劉再生《中國音樂史簡述》同樣認為相和歌常用的樂器有節、笙、笛、琴、瑟、琵琶、箏等[4]。金文達先生《中國古代音樂史》根據《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據王僧虔《宴樂技錄》和張永《元嘉技錄》二書研究的結果,相和歌所用的樂器,主要為笙、笛、篪、節、琴、瑟、箏、琵琶等7~8種。指出其中的琵琶可能是阮[5]。由喬建中先生主編由馮潔軒、喬建中、張振濤居其宏撰稿的《中國古代音樂史》也是這種觀點。即:絲竹類伴奏樂器有琴、瑟、箏、琵琶、笛、笙、篪,而由歌唱者敲節鼓統一節奏[6]。
(二)相關學術文章中的相和歌伴奏樂器組合形式
專門研究相和歌伴奏樂器的文章少之又少,即使有這方面的論述也是零星的見諸于相關專題的研究中。如黎傳緒《雜論漢俗樂及漢樂府詩》提及相和歌的伴奏樂器時說,其樂器以管弦樂器為主,有笙、笛、簫、節、琴、瑟、箏、琵琶、鼓等[7]。
(三)相關專著中相和歌伴奏樂器的組合形式
錢志熙著《漢魏樂府的音樂與詩》一書中有這樣的表述:相和歌的伴奏樂器,主要有琴、箏、箜篌、簫、笛等,其中箏與簫、笛尤其常用。相和歌主要是以歌為主,絲竹則起渲染氣氛及定調的作用,“節”則是歌舞者用來定節拍的。認為相和歌的器樂伴奏不像一般的藝術歌曲的伴奏,而像說唱藝術的伴奏。其完整的唱奏結構是:艷——執節者歌——解——執節者歌——解……趨——亂[8]。
由以上現人研究狀況可看出,今人的研究大都限于相和歌高級階段的伴奏樂器,或定型時期相和歌伴奏樂隊的研究。那么早期相和歌的樂器伴奏形式究竟怎樣呢?
相和歌的伴奏樂隊
(一)相和大曲的伴奏樂隊
相和歌的發展有這樣幾個階段:徒歌—但歌—相和歌—相和大曲或但曲(不含聲樂舞蹈的純器樂演奏形式)。從無伴奏的一人唱的徒歌,到1人唱3人和的但歌,再到有簡單伴奏的發展中的相和歌,到最后發展為有著龐大規模和復雜結構的相和大曲,其最顯著的發展變化是器樂的加入,和伴奏樂器組合的變化。《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詞一曰:凡相和,其器有笙、笛、節歌、琴、瑟、琵琶、箏等7種。我想對這里所講的伴奏樂器應有兩種理解:一、指的是相和大曲或但曲的基本的樂隊配置;二、指大多相和歌唱奏時所能用到的樂器之和。這些樂器在一首相和歌中,有時可能全都能用上,有時可能只用其中的一兩件,不同的相和歌根據不同的需要配置不同的樂器。
相和歌在魏晉之際發展為相和大曲[9],而西晉初相和歌的樂器配置已較固定[3],可見相和大曲的樂器配置在其形成之時就較為固定。相和歌最初有平、清、瑟3調,后來又加入了楚、側二調。不同的曲調種類有著不同的樂器組合形式。所以相和大曲的樂器組合形式也有幾種,據《樂府詩集》卷三十《古今樂錄》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平調有七曲:一曰《長歌行》,二曰《短歌行》,三曰《猛虎行》,四曰《君子行》,五曰《燕歌行》,六曰《從軍行》,七曰《鞠歌行》。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箏、琵琶七種,歌弦六部。”張永《錄》曰:“未歌之前,有八部弦;四器俱作,有高、下、游弄之后。凡三調歌弦,一部竟,輒作送歌弦。”卷三十三《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清調有六曲:一《苦寒行》,二《豫章行》,三《董逃行》,四《相逢狹路間行》,五《塘上行》,六《秋胡行》。”其器有笙、笛(下聲弄、高弄、游弄)、篪、節、琴、瑟、箏、琵琶8種。歌弦四弦。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五部弦,又在弄后。晉、宋、齊,止四器也。”卷三十六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瑟調曲有《善哉行》 《隴西行》 《折楊柳行》《西門行》 《東門行》 《東西門行》《卻東西門行》 《順東西門行》 《飲門行》 《上留田行》 《新成安樂宮行》《婦病行》 《孤子生行》 《放歌行》《大墻上蒿行》 《野田黃爵行》 《釣竿行》 《臨高臺行》 《長安城西行》 《武舍之中行》 《雁門太守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福鐘行》 《艷歌雙鴻行》《煌煌京洛行》 《帝王所居行》 《門有車馬客行》 《墻上難用趨行》 《日重光行》 《蜀道難行》 《棹歌行》 《有所思行》 《蒲阪行》 《采梨橘行》 《白楊行》 《胡無人行》 《青龍行》 《公無渡河行》。”其器有笙、笛、節、琴、瑟、箏、琵琶7種,歌弦6部。張永錄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后。晉、宋、齊止四器也。”其中卷三十“四器俱作”指琴、瑟、箏、琵琶4種樂器齊奏。清、平、瑟三調曲所用伴奏樂隊可列表如下:

?
由上表可知,相和大曲所用到的樂器有笙、笛、筑、節、篪、瑟、琴、箏、琵琶9種。
⒉一般相和歌的伴奏樂器
以相和大曲為支點往上溯源,其早一點的形式即脫離僅清唱的但歌,剛被“被之管弦”的一般形式的相和歌。這種形式的相和歌還處于不成熟的發展階段,其歌唱形式及樂器配置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并且器樂伴奏形式也較簡單。如新野縣樊集漢墓出土擊鼓歌唱畫像磚(《南陽磚》圖94),見圖1:

圖中有二樂人,一人擊筑,一人邊揚臂擊鼓邊引亢高歌,另一俳優做滑稽表演。此圖中伴奏樂器只有筑和鼓。同為此墓出土的另一畫像磚(《南陽磚》圖106),見圖2:

圖中一人彈琴,一人擊小鼓伴奏,另有二伎人揮舞張口,邊舞邊相向而歌。其伴奏樂器為琴和鼓,這和上圖所顯示的只有筑和鼓的伴奏形式,可能都是“被之管弦”的相和歌的早期形式。此時對“被之管弦”還沒有嚴格的要求,不一定管弦兩類樂器必須同時使用,且此時的“被之管弦”很可能是對所有“被”與“管”的和“被”于“弦”的,及同時“被”于“管弦”的相和歌的統稱。只用管樂伴奏的歌唱形式,見1969年河南省濟源市泗澗溝第八號西漢末期墓出土樂舞歌唱陶俑(《豫·大系》圖2.5.7),見圖3:

此組樂舞俑共6人,右起第一俑站姿,第二俑端坐,二俑皆將手伸于胸前,似在歌唱。中一舞俑,正揚袖起舞。后排三人,吹排簫和塤伴奏。這可能就是早期“被”于“管”的相和歌的形式。
相和歌最初是流傳于民間的民間歌曲,到漢武帝設立樂府,它才開始正式進入宮廷,才使得那些清唱的歌詞配以樂,這時相和歌才開始有自己的伴奏樂器。隨著琴的形制的逐漸定型,及琵琶、笛等樂器傳入我國,相和歌的伴奏樂隊的規模也逐漸發展壯大。東漢時相和歌的伴奏樂隊明顯較西漢時龐大,見下列出土樂舞俑及畫像石(磚),圖4:

這是一組東漢前期的樂舞俑,于1965年出土于洛陽市老城西北燒溝漢墓區系14號墓。這組樂舞俑共6人,舞者男女各一位。其余4人席地端坐,前排一人鼓瑟,一人雙手捧烏塤做吹奏狀,后排藝人吹拍簫,一人雙手做擊節狀[10]。可見,由瑟、節、塤、排簫所組成的樂隊也是相和歌的一種伴奏形式。1951年出土于四川資陽縣東漢墓的奏樂歌唱俑,則展現了當時相和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見圖5:

這四俑皆成坐姿,作為一擊鼓俑,面帶微笑,左手撫鼓,右手握鼓槌高舉過頭,邊擊鼓邊歌唱。左二為鼓瑟俑,此俑雙手古色,頭顱高抬,張口歌唱。另外兩個為撫琴俑,亦面帶微笑,邊彈邊唱。這組用本出土有6件,但現存完好的只有這四件,至于另外二俑奏何種樂器就不得而知了。但至少可以看到相和大曲伴奏樂隊中所沒有的“鼓”。南陽市軍帳營出土東漢墓“相和歌”演唱、演奏場面畫像石(《豫·大系》圖2.3.7)。見圖6:

圖中共有12人,右起第一人撫琴,第二人吹塤,第三人吹笙,第四人鼓瑟,另四人端坐似吹排簫,左起三人站姿歌唱。在這幅畫像中的伴奏樂器有絲類樂器琴、瑟,管類樂器塤、笙、排簫,沒有節奏性樂器。
從這些出土實物可看出,相和歌的伴奏樂器發展的一般規律:單個樂器的數量由少到多,樂器種類由單一到多樣。若拿文獻同出土實物相印證,可以發現文獻記載當是相和歌伴奏形式的一個大體概括。從出土實物中,不僅可以看到文獻上記載的,如相和歌的主要伴奏樂器中的琴、瑟、筑、笙等,還可以看到文獻記載上所沒有的鼓、塤、排簫等樂器。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相和歌早期的伴奏樂器很不固定,其器樂組合也很自由,當時的“被之管弦”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同時加入管樂和弦樂,而是一種通指。隨著經濟的發展,相和歌伴奏樂器的組合形式也在發展。大概到了東漢時,管弦兩種樂器才真正同時出現在相和歌的伴奏樂隊中,此時的樂器配置也不固定,但已有了一些限制,如必須管弦齊全。再到后來,隨著琵琶等樂器傳入我國,相和歌的伴奏樂器更加豐富起來,這就到了魏晉時的相和大曲。
結 語
漢代相和歌是承接先秦“楚聲”和“國風”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漢代民間歌曲。隨著被統治階級重視程度的加深,它的器樂伴奏形式不斷發展完善,直至魏晉時發展為具有固定伴奏樂隊的大曲,達到了相和歌藝術形式的頂峰。一種藝術形式達到頂峰后,要繼續發展,就必須為其注入新的血液。高度發展的相和歌在魏晉時,與當時流行在南北兩地的“吳歌”“西曲”合流形成了清商大曲。隋滅陳,建立隋朝,成立七部伎、九部伎,清商大曲即被列入其中成為單獨的一部伎樂——清商伎。直到唐朝,成立九部伎、十部伎,清商伎還作為單獨的一部伎存在其中。再到后來,唐大曲、法曲還都受相和歌發展的清商大曲的影響,樂曲中多有楚聲。這些樂曲的伴奏樂器,也是主要在相和歌主要伴奏樂器的基礎上,加入當時新傳入我國的樂器而組成。如果說我國傳統音樂是一條河,那么漢時興起的相和歌,則是這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的中游,它起著承接和發揚傳統的重大作用,為以后我國傳統音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冊.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
[2]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上海音樂出版社,1989.
[3]吳釗,劉東升.中國音樂史略.人民音樂出版社,1993.
[4]劉再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人民音樂出版社,1989.
[5]金文達.中國古代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1994.
[6]喬建中.中國古代音樂史.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
[7]黎傳緒.雜論漢俗樂及漢樂府詩.南昌教育學院學報,2003,18(1).
[8]錢志熙.漢魏樂府的音樂與詩.大象出版社,2000.
[9]孫繼南,周柱銓等.中國音樂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3.
[10]修海林,王子初.樂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注]:本文中圖1、2、3、5、6引自李榮友著《漢畫像的音樂學研究》.京華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圖4引自修海林、王子初著《樂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