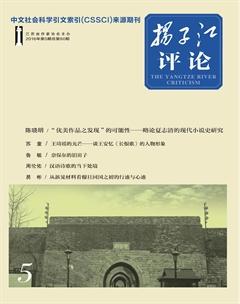當代兒童小說的生態女性主義解讀
王帥乃
自1974年法國女性主義者弗朗索瓦·德·歐本納首次提出“生態女性主義”這一概念后,爭取性別平等與保護生態環境就被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將父權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相聯系,指出這兩種意識形態背后蘊藏的等級制觀念與邏各斯中心主義,女性與自然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框架內被客體化為“他者”,成為較“劣”的一類。生態女性主義的核心理念有以下四個方面:首先,由于女性生理特點以及女性長期來履行的養育性社會角色使得女性與“身體”保持了更為親密的關系,女性被認為與自然更為接近,從而可與自然互為隱喻;其次,生態女性主義反對等級制度,認為男人與女人、人與自然中的其他生物都是生態網絡中的一點,并無高低之分;再次,生態女性主義強調差異,認為健康的生態系統應該保持多樣化狀態;最后,生態女性主義批判二元對立思維,認為“男/女”與“自然/文明”兩種對立背后的邏輯是一致的,因此解決其中任一難題都會對另一組關系的重構產生啟示意義。在中國當代兒童小說創作中,包含生態女性主義傾向的作品在主題思想上大致分為三類,即以班馬的《沉船謎書》a為代表的二元對立之思,以彭學軍的《你是我的妹》b為代表的對“鄉村烏托邦”想象之質疑,以及以韋伶的《幽秘花園》c為代表的對建構女性主體與自由多元世界之追尋。
一
當現代工業文明與消費文化的推進對自然環境造成侵蝕、破壞,特別是當生態危機伴隨著現代文明發展帶來的虛無化等精神困境初露端倪時,對工業文明產生的焦慮使得人們將自然生態與現代文明對立起來——作為人類面對生態問題的早期態度,這種理解是較為符合認知發展規律的。《沉船謎書》就是該類將“女性—農業文明—自然生態”作三位一體思考,將之與男性形象帶來的科技文明與生態破壞相對立后進行敘事的代表性文本。
《沉船謎書》講述的是兩千多年前古羌高原王子用三棵神樹造了一艘瑰麗精妙的樓船,駛出古三峽而后從容自沉于長江中游的“舒鳩”無人河灣里,兩千年后“仿古心理學家”老木舅舅和漁女紅妹子用“古人心境”而不是用現代思維破譯“沉船之謎”的故事。文本開始交代紅妹子及其姑婆荷姑住地時,便有意識地將故事的這個主場景神秘化。小說多次提到這一江段是一個“迷宮”,九曲回腸,被白霧和茂盛的蘆葦包圍,外界很難得知這里有別樣的美景存在,考察隊的大船也開不進這里細長狹窄的河道。顯然,這是一個現代工業文明尚未侵入的原始生態系統。而沉船所在的河灣,則是一個“葫蘆形狀的大河灣”,它水體清澈、孕育著別處沒有的游魚;紅妹子黃昏沉潛入水時,她的感覺是“水下一收了光線就如同完全關閉了的密室一般,成為絕對的黑暗……她還想游下去,卻已經不知道手腳的劃動和時間了,好像進入無盡的冥冥之中”d;老木進入巨大的沉船時,覺得自己“步入一個沒有時間的地方。這場所十分陌生,但又像是昨日曾來過似的,那船艙內的……都在水中靜靜映照著明暗的光線,幽蕩一種遙遠卻又暗暗親切的情緒”e。神奇的江段、葫蘆狀的大河灣,以及這艘千年古船,在小說中都呈現了類母體抑或類子宮的樣貌,這里昏暗混沌、逃逸出“時間”概念之外,這個搖蕩著的水環境提醒我們想起記憶最深處那給予我們滋養的溫暖而混沌的地方。從全文看,這片水域和這艘大船確實是兼具“死亡”與“新生”兩種功能意蘊的所在,而“死”與“生”的交替循環與“永生何以可能”也正是《沉船謎書》重點探討的哲學命題。
這個故事發生在孕育生命和象征更替、流動的“水”的環境中,引導故事發展的關鍵人物紅妹子則是繼承了姑婆巫女靈性的少女,她被水文勘測隊從西藏帶回故鄉時父母均已失蹤,其姑婆身世更是離奇——她是嬰兒時坐著荷缸漂到此地的。這兩個女性人物是解開沉船之謎的關鍵,她們對自然感知的靈性與自由不羈的處世方式為考古隊所詬病。考察人員面對停電和大霧這樣的突發狀況恐懼不已、惶惶不安,將之定性為“有鬼”;另一方面,紅妹子和她的魚鷹也直覺地不信任、不喜歡以純科技思維、依賴器械進行探測古船的考古人員,不愿意和他們一起工作。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者卡洛琳·莫瓊特曾指出,在“機械”的世界中,對自然、社會和自我的理性控制正是通過這種機器隱喻而實現的f。在后來的故事中,考察隊員把紅妹子點著燭火的家說成是女巫的幽靈鬼火,隊員阿炳甚至錯殺了保護他的魚鷹“簍子”,這些情節說明,人類已經習慣了對與自己相異的人事先入為主地抱有敵意、習慣了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而父權話語支配下工具理性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社會,在二元對立體系中將男性與理性、文化相聯系,女性與感性、自然等概念相聯系,進而定義前者相較于后者更高級,從而逐步合理、合法化男性對女性和自然的統治,被定義為與“科學技術”相對的女性和自然被社會強勢話語言說而難有對等的機會去真正言說自我。
從笛卡爾的人本主義到培根的“知識時代”,人類中心主義與理性中心主義總體呈強化趨勢,科技的發展使得自然被客體化、物化的程度逐漸加深,法國思想家埃德加·莫蘭認為人本主義“挖掉了所有迷信和宗教的根本。但是由此一來,人本主義把人作為一個超自然的主體,又為自己創造了神話。”g在《沉船謎書》中,男權與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遭遇了顛覆。首先,小說的男主人公是一個掌握現代科技文明卻將自己放逐于主流研究界之外堅持“仿古心理學”(聲稱考古必須要體察古人之心),甚至穿戴仿古、工作時總是關閉現代科技工具的“邊緣學者”,正是因為這一特質,他得到了紅妹子和魚鷹“簍子”的信任,也得以成為古船制造者千載之下的知音。其次,文本突出了以紅妹子、羌族王子等生態型人格者的高智慧,其中羌族巫師教導王子與樹交流感情、學習樹的智慧那一段敘述可以說是全文的理念核心:第一,人若與樹同呼吸共命運,人的悲喜樹都會記得;第二,在樹頂觀看世界,懂得“大事情都要用很長的時間才能做成”;第三,生命可以轉換成不同形式,人可以和樹一樣去思考永生的命題。羌族王子以其超越時空的識見,為自己在千年之后安排了極致的“死亡”和“重生”,同時也提醒現代社會的人類注意到那已被破壞的生態。沉船事件從發生到被發現到最后的順利結束——由于水質被污染導致魚類種群變化,進而被魚鷹察覺這一變化,再至紅妹子在魚鷹的帶領下發現沉船告知外界,最終是燒船后留予后人的王朝文明秘密——都在這位掌握了人與自然秘密的古人的計劃之中。最后,羌族王子之所以能夠留給后人這樣的秘密,是因為他沒有在父權斗爭中被“異化”而失去愛的能力,他從始至終都與靈魂之樹相伴,這三棵大樹幾經形態的改變也始終以它們獨有的方式保護著這位人類智者直到千年以后。所有這些都表現了文本對工業文明的反思,與把生態系統的整體利益作為最高價值的理念——“把是否有利于維持和保護生態系統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為評判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標準。”h
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沉船謎書》這樣的敘事安排一方面展示了感性力量、女性與自然力量的強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承認了傳統性別結構的定義,強化了性別的本質主義,它沒能徹底地突破“女性—感性”體系代表自然、進而代表“正義”的思路,并且固化了“自然—現代文明”必然對立的思維模式。這種文化生態女性主義傾向的思路選擇性地忽略女性與自然之間的差異,這樣不單可能遺忘在對自然造成的傷害中女性可能處于一種共謀的地位,還可能會歪曲自然實體真實的需求(關于這一點本文的二、三部分還將重點討論)。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家內斯特拉·金認為,生態女性主義思潮的最終目的是“將(女性與自然的關系)當作創造一種不同的文化政治的有利因素來使用,這種文化政治能夠把知識所包含的直覺的、心靈的和理性的不同形式都融會在一起,讓科學與‘自然的魔力合而為一;它促使我們改變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并且創造一個自由、生態的未來社會”i。而以《沉船謎書》為代表的如《小綠人》《山鬼之謎》等一類小說,最終均無奈地承認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生態維護似乎難以兩全,生態型人格的主人公要么遠離自然并對世人遮蔽他們所知的秘密,要么選擇歸隱自然與現代文明割斷聯系,這等于是表達了對二者共生發展某種程度上的絕望。從這個角度而言,這一類小說尚沒有能夠實現生態女性主義文本的最高理想,屬于早期觀念覺醒階段的文本。
二
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將自然與女性相聯系,在相關作品中最常看到的也就是將流動變化的天象水文、大地、生物(尤其是植物)與女性互為隱喻。上文已經分析了在早期具備生態意識的作品中比較常見的處理是將“女性—自然”緊密聯系,與另一組隱喻以不能互融的形式出現。這一部分選擇考察的文本《你是我的妹》屬于鄉村題材的小說,但它的獨特之處在于超越了上述處理,對“女性—自然”這一隱喻既有繼承性的敘寫,更提出了質疑,這就從某種意義上松動了二元對立的僵化思維模式。
《你是我的妹》是湘西女作家彭學軍的代表作,其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講述跟隨下放的母親來到湘西苗鄉桃花寨的“我”與妹妹老扁、阿桃一家以及半瘋的阿秀婆的故事。桃花寨名副其實,在初來乍到的人眼里,整個村落仿佛生長在一片安詳溫馨的粉紅中。小說的核心人物與次要人物幾乎都是女性,甚至故事的一開始,連“我”的父親都被作者“放逐”到“另一個地方搞工作組”去了,因而整個文本給讀者一種“紅粉桃花女兒國”的印象。然而,這并不代表這個“她鄉”式的小村能夠避免男權話語的侵蝕——阿桃的戀人龍老師明知沖喜是迷信,仍然選擇做“孝子”棄困境中的阿桃于不顧而另娶,阿桃的父親每見妻子生一個女兒就砍一棵結婚時種下的象征愛情的桃樹,這些行為背后隱含的是將女性物化的思維:女人是沖喜的物事,是生育的工具。延留著宗法制殘余的鄉村父權社會企圖借女性的軀體延續自我衰朽的生命,而女性個體的意志被無視、掩埋,成為只剩下一具符號化身體的空洞能指。
小說中桃花寨最大的危機是野豬吃人,而作者就曾這樣描寫過阿桃爸:“阿桃媽生下四桃時,阿桃爸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張著一張闊嘴撲哧撲哧直喘粗氣,像一只走投無路的野豬在堂屋里打轉,兩只眼睛東瞄西望,尋找著發泄的對象和途徑。”j阿桃爸媽的愛情曾是村里的佳話,而如今阿桃爸成天黑著臉,阿桃媽為求得子不停生育,生產時無人作陪,生產后以淚洗面、憂心忡忡,農耕文化下的男權思想甚至將那一刻的阿桃爸“異化”成與“吃人”的野豬無異。然而,阿桃爸連年砍樹,剩下的樹卻越來越繁盛,一年一個女孩接連降生,那最后一棵象征著“妹”的桃樹在決定它生死的那一天忽然開得如火如荼如詩如畫,這是對以“盼子”為表征、企圖扼殺女性生命的父權文化的反諷與抵抗,“暴怒的父親被震撼了,原本朝向花樹握著砍刀的手慢慢垂下,仿佛一個高大強悍的成年男性和他所代表的父權文化在女性的生命場里黯然頹敗。”k最后為野豬所害的“妹”被葬于樹下,原來的樹邊居然抽出了小樹的嫩芽,作者讓女孩與桃樹永遠融合在一起,讓生命以另一種形式存在,將希望的種子留給讀者。
但我們也進一步發現,桃花寨里對女性的不尊重根源在于落后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農耕文明在《沉船謎書》中代表的是與生態整體主義的和諧,而在《你是我的妹》中則呈現出小農經濟的另一面:正是它帶來的貧弱才使“生子”成為改善生活的一種可能,它與生俱來的封閉也使得人們難以在思維上有新的變化突破。面對來自山林的野豬之害,人類顯得幾無抵抗能力,最后依靠阿秀婆的母性之愛以同歸于盡的慘烈方式結束了這場禍事。“妹”憑借桃樹繁盛的花事消弭了父親眼中“絕望的、黑豹般”的野獸性、“吃人”性,最終卻難以逃過被野豬吞噬的命運。自然在這里并不是完全與女性一體的象征,真正的自然也正是如此,萬物與人類作為自然的一份子,彼此之間存在著緊張又矛盾復雜的聯系。人性在這里更多的是被挖掘與贊美,因為愛,因為對美與生命的感悟,男性的眼睛也可以被那“瑰麗無比的色彩滋潤得平靜起來、柔和起來”,即使有主流男權文化的桎梏,阿桃的父親最終仍選擇了“不順從”于扼殺生命與美的丑陋的意識形態,人性之高貴也正由這代表著人類自由意志的選擇中顯露。換句話說,小說《你是我的妹》暗示著人類彼此之間的可溝通余地是更大的,真正應該解決的是農村落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問題。文本的這種解決策略符合帕特里克·D·墨菲在《代言另一種自然》里提出的建立一種非等級制的、不拒絕(男性—女性、自然—文明)聯系的“差異意識”,建立非“他者”的“另者”觀l。可以想見,“對話”在這其中將需扮演重要角色。
《你是我的妹》揭示了男權背后的重要根源,即它與貧窮、封閉往往有著相生關系。小農經濟主導的社會中,生存困境中的人類總是更容易選擇將女性作為犧牲品,重男輕女觀通過農村社會長期的男權話語機制的運作本身被固化的同時又反過來固化了貧窮。女性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生存,承受的是自然與社會的雙重枷鎖,阿桃在阿秀婆葬禮上忘情的擂鼓與舞蹈不如說是小農社會文化下貧弱之地女性的歌哭;作為“干部女”的“我”和阿桃姐妹情深,可是當“我”要回城時,阿桃卻仿佛忽然記起主人公“干部女”的身份與之產生了隔閡,這是階層差異造成的隔膜——即使是一樣擁有女性的軀體,她們各自的苦惱、最強烈的訴求仍然是不一樣的,亦即此處在諸多“身份”(Identities)中,階層身份的重要性超越了性別身份——就像西方女性主義在其發展完善過程逐漸中認識到不同種族、國別、階級的女性受壓迫的狀況不同,誰也無法為誰作“完全代言”,文本暗示了主流社會的女性亦需省思自身的生活是否建立在對邊緣社會女性的壓抑之上。
在《你是我的妹》里,主流社會與少數民族鄉村社會的女性之間最終實現的是彼此間的滋養與共生。城市出身的“我”在目睹阿桃姐妹相依為命的感情后,逐漸轉變了對妹妹老扁的自私態度,認識到“是阿桃教會我怎么做姐姐的”,姐妹之情越來越融洽。作為主流社會中的知識女性,原是市文化館工作人員的“母親”,下放時主動要求到苗區來,這是女性在政治高壓環境中的一種變式突圍——她盡最大可能地維護了自我的意志,選擇此處是因為能夠實現自身的生命價值,這一舉動將政治意識形態對個體的編碼轉換成了女性主體的積極選擇。在文本的最初和最末,“母親”扮演了重要角色,她臨走念念不忘的是“阿桃應該離開那兒”。多年后,母親終于將阿桃的作品帶到了國際文化展上,成為令阿桃走出山村的伯樂。“她想寫一本少數民族文化風俗、發展歷史方面的書。她喜歡和一些走路顫顫巍巍、耳聾眼花的老人打交道,她十分吃力、很有耐心地和他們促膝交談,并四處收集一些陳磚舊瓦、破碗爛罐,甚至死人骨頭,拿不走的就把它們一一畫下來。母親對自己的事業如癡如醉……很多年以后,當兩鬢斑白的母親將一部城磚一般厚重,圖文并茂、裝幀精良的《少數民族史志》遞到我面前時,我才認識到母親的偉大。”m讓藏匿深山的苗鄉女性的智慧與文化為中外所知,這本身就是一個邊緣女性浮出歷史地表的隱喻。而更深層的意義是,這是一次由女性群體內部自覺發起、完成的超越階層、民族的融通互助,是女性自我完成的對于女性的書寫。
三
生態女性主義要實現其最終目標、沖破傳統的男權話語體系,必須使女性走出心靈束縛,重新發現、認知自我,而女性的個體經驗各自不同,建構主體性的方式也必然隨之不同,韋伶“生態/女性”書寫的經典之作《幽秘花園》就充分調用了藝術、童年、自然等概念的文化符號意義,書寫了一個關于“救贖”與“希望”的文本。
《幽秘花園》以第一人稱、幻想小說的形式講述一對文革期間遭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夫婦的故事。小說前兩章的存在將文本分成兩個敘述層次,從現實落筆,自第三章才進入正式的故事,交代了白老頭、白婆婆退休教職工的身份。這對夫婦隱居在其他教職工家對面的山坡上,“與世隔離,永不與人往來”,成人們都嚇唬自家孩子說這對夫婦是瘋子,小孩去對面玩會被用棍子趕走。“瘋子”也許是主流社會賦予邊緣群體最通用的污名,齊澤克曾將“稱謂”所包含的賦權職能定義為“稱謂的意識形態維度”,它是一種協定。通常這種協定或者說被主流社會所認可的“稱謂”的基石,是父系律法n。與成人管夫婦倆叫“瘋子”相對的是,文本讓敘述者“我”(韋三妹)在知道兩人真正姓氏的情況下仍堅持用“白老頭”“白婆婆”稱呼他們,體現出一種對“稱謂”的特殊敏感;不難發現,這對夫婦的困窘還表現在其住所的特殊性上,“對面小山坡上孤獨的一所房子”也讓他們處于一種被集體“凝視”的狀態中,“這邊山坡”和“那邊山坡”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讀者后來知道老夫婦的家屢次被紅衛兵打砸破壞,在小說敘述者“我”所代表的兒童的純真之眼中,這些沒有主體性可言的打砸搶者始終被符號化地指稱為的“戴紅袖章的家伙”而連“紅衛兵”這樣的明確稱謂都沒有;老夫妻的八個孩子很可能是在文革迫害中死去,正是這點給白婆婆帶來了難以釋懷的傷痛,使她丟棄了過去的記憶,沉溺于園圃;至于白老頭最珍貴的畫作,也被紅衛兵一次又一次地毀壞,這暗示著在極權社會中,話語只能是單一的。繪畫作為“藝術”的一種“在根本上是異在的……是一種理性的、認知的力量,揭示著一種在現實中被壓抑和被排斥的人和自然的維度”o,故而它們極易遭到政治高壓社會的扼殺。上述之外,小說中“我”對擺放在白婆婆相片下的小相片中人身份探尋的結果,更是象征著從古裝相片女子到胡蝶到白婆婆甚至再到“我”,一代又一代女性如同斷翅蝴蝶一般或因權貴所喜或因政治高壓或因話語圍墻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囚禁”在“花園石墻后面”的囚徒命運。凡此種種都說明了故事發生的主要場所是一個受到話語監控的場域,其間的主人公如何在單一的意識形態話語里突圍,是文本的中心所在。
白婆婆的“花園”是這片話語禁區里最迷人的所在,這里是她用以忘卻憂愁療治心傷之地,是孕育萬千生命、展現女性偉力的地方;但同時它也是囚禁白婆婆心靈的牢籠,令她被喪子之痛纏綿束縛住而困守于此,不肯回憶起完整的自己,不肯重新拾起童年時“去遠方”的夢想,女性的主體人格得不到真正生長。因此,花園意象在這里具有雙重功能,忽視任何一面都是不妥的。正如上文所強調,單純突出女性與自然之間本質性聯系的方式“不僅支持統治性意識形態,而且還限制生態女性主義者促進社會與文化改變的能力”p。實際上,這里的“花園”可被看作白婆婆內心世界的實體化存在。“我”正是在這里初次感覺到了“花園起舞”的美好,這種經驗延續到成年之后,讓“我”受益不盡。文本用了大段文字描繪這種舞蹈帶來的精神之樂,而白婆婆被政治傷害割裂的記憶和被封閉的內心童年自我,也正是在遇見韋三妹后,在其舞蹈引起的共鳴下方才蘇醒。如果以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的觀點來看,這正是因為“藝術通過讓物化了的世界講話、唱歌甚或起舞,來同物化作斗爭。忘卻過去的苦難和快樂,即可把人生從壓抑人的現實原則中提升出來。反之,追憶又激起了征服苦難和追尋永恒快樂的沖動。”q花園通向“外界”(也是通向白婆婆童年自我“瑰瑰”)的那個小洞,一直都存在,只是沒有人去移開那塊明明只是“畫”上去的石頭。當韋三妹因為兒童的好奇天性移開石頭偷爬出花園遇見瑰瑰并把她帶回園內與白婆婆相對時,白婆婆的心結也自然被打開。童年的瑰瑰和如今白發蒼蒼的老人,不約而同地成了三妹的朋友,這本身就說明白婆婆最初的希望從未被真正放棄,也因此女童三妹才能遇見她們、引領她們相遇。在這里,“兒童”作為一種“復演”的原始人類、一種更“貼近原始自然”的文化符號被運用,其承擔著特殊的引領意義。
與花園相比,白老頭留在門窗上的生態之畫——那借助門窗構造和光影作用讓人分不清虛實真假的“海洋/沙漠”圖,才是作者真正認可的精神歸宿,這種承認不論性別為何與自然均可聯系的寫法也許是克服二元對立論的一種重要方式。“海洋/沙漠”圖打通的不僅是空間之隔,還有聯系心靈的路徑。白婆婆曾不再相信“沙漠與海洋”,將其連同丈夫的繪畫創作一并斥為謊言,囚禁自己的同時也囚禁丈夫渴望重新振作的心靈。當然,這是因為“文革”的思想鉗制和子亡夫走帶來的巨大創痛。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視角下,女性在男權社會中承受著雙重壓迫,即作為“女人”需要面對的性別壓力,和作為“人”需要面對的生存異化。面對壓抑和異化,《幽秘花園》提供的“生態解決法”微妙之處在于它并不是以自然實體而是白老頭畫在房屋上的畫作為象征,亦即以人類藝術文明的形式表現的“自然”。藝術的作用在于“維護和保護著對立——對分隔了的世界的不幸意識、挫敗的可能性、未完成的希望,以及被背棄的承諾”r,以虛構法造人精神的實境。“我”在初見“門窗畫”時就震撼于沙漠和海洋這對奇異的生態系統組合,它們將現實的不可能抽象到藝術世界的可能,沖擊人們固有的審美想象與思想維度,象征著精神自由的廣闊天地和永將追尋的遠方。因此,白婆婆總是能夠在畫上看出丈夫走到哪里,想要去哪兒,而白老頭也能在千里之外感受到妻子內心,當她想起從前渴望他回到身邊時,便立刻風塵仆仆地回到家中。曾經阻止丈夫作畫的白婆婆在重新發現自我后,親手完成了一幅許多游魚和男孩女孩們牽手飛翔的“大地藝術”,這也意味著她借藝術完成了對自己的最后治療、重建了自身主體性,她拾起了曾被拋棄的承諾、最初的遠方之夢,韋三妹后來在門窗畫上看到夫婦二人跋涉于沙漠海洋的身影也印證了這一點。《幽秘花園》試圖證明,生態自然與人類文明通過“藝術”之橋梁是可以相通相聯的,這就自然而然地打破了早期刻板的二元論框架下將女性與自然同男性與文明對立起來的理念之圍。引入后結構女性主義的思路,利用類似《幽秘花園》中的寫作策略,承認并推動女性復雜、變動的主體性的建構,而不是簡化女性的身份使之變得單一、靜態,這也許是生態女性主義文本創作可以嘗試突破的一種方向。
從敘事學角度看,《幽秘花園》的雙層敘事結構也說明了作者對故事寫作掌控力的自信。在內層故事中,二位老人終于離開小屋去尋覓遠方的新世界,小屋被地震帶來的凹陷永久保存在水里。經歷了多年,政治災難終于還是結束了,“我”把這個童年故事告訴了孩子們,孩子們意欲尋找小屋。小屋成了跨越兩個敘事層面共同存在的實體,屋內的圖畫永遠不能被證實是否存在了,故事也因此多了虛實相生的張力。而不論是內層故事里出走的老人還是外層故事里以前者為“美”的兒童,都是自由平等意志最終在文本中得以實現的載體。《幽秘花園》告訴讀者的是,“希望”在永遠的“前方”,在自然,在藝術,在允許多元思想的社會和純凈的心靈中。
小 結
性別話語的規訓,往往從孩提時代就已經開始,兒童文學作為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少年精神成長的陪伴者,值得文學研究予以特殊的關注。當代兒童文學作品中已有漸醒的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聲音,其已隱隱包蘊“去中心化”、解構傳統性別話語的意識,這確然是值得欣慰的文學現象。筆者通過對上述包含生態女性主義傾向的典型文本的分析,也發現當前兒童文學領域內的“生態女性主義書寫”尚未發展至自覺、成熟的階段,但這不意味著現有文本沒有深度解讀與再解讀的價值。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研究視角與意識形態分析理論,將會供給我們新的考察與衡量文本的尺度,而這不論對文學研究抑或是對理論本身的拓展與完善都將有所裨益。
【注釋】
a班馬:《沉船謎書》,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年版,又名《巫師的沉船》,《沉船謎書》是再版后最新的書名。班馬(1951~ ),原名班會文。當代兒童文學創作者、理論研究者。1976年后歷任上海《少年報》編輯、廣州師范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講師。1984年開始發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小說集《那個夜,迷失在深夏古鎮中》(合著),長篇小說《六年級大逃亡》,童話集《現代夢幻童話》,散文集《星球的細語》,文論集《游戲精神與文化基因》,專著《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與構想》、《前藝術思想》(國家八五重點圖書)等。《星球的細語》獲全國第二屆優秀兒童文學獎,其作品還獲全國首屆兒童文學理論優秀論文獎、第一屆陳伯吹兒童文學獎。《沉船謎書》是其幻想小說代表作之一。
b彭學軍:《油紙傘》,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版。彭學軍(1963~ ),女,湖南長沙人。當代兒童文學作家,作品主要涉及少女題材,尤擅以湘西為代表的鄉村少女題材的寫作。1989年開始發表作品。199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終不斷的琴聲》、《你是我的妹》,中短篇小說集《油紙傘》、《歌聲已離我遠去》等十余部。長篇小說《腰門》獲中宣部第十一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并入選新聞出版總署2009年向全國青少年推薦優秀圖書,短篇小說《油紙傘》獲1995年陳伯吹兒童文學獎,作品《冰蠟燭》獲第2屆“周莊杯”全國兒童文學短篇小說大賽特等獎。《你是我的妹》是其重要的代表作,曾獲第六屆宋慶齡兒童文學獎小說類大獎、海峽兩岸少年中篇小說征文一等獎,并被改編為電影《阿桃》。
c韋伶:《幽秘花園》,21世紀出版社2002年版。韋伶(1963~ ),當代兒童文學作家,廣州市女作家協會副會長,少女文學和文化研究者。作品均涉及少女題材,反映青春發育期的少女文化。1982年開始兒童文學創作,2000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幽秘花園》《尋找的女孩》《月亮花園》《山鬼之謎》《魚幻·裸魚》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散文多部。作品獲國家圖書獎、冰心新作獎大獎、臺灣好書大家讀年度獎等國內及海外多種獎項,并被譯介到日本、美國、泰國等地。長篇小說《幽秘花園》是其代表作之一。
d班馬:《沉船謎書》,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頁。
e班馬:《沉船謎書》,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頁。
f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 ic Revolution, New York:Harper Collins US, 1980, 192~193. 轉引自蘇賢貴:《生態危機與西方文化的價值轉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
g[法]埃德加·莫蘭:《反思歐洲》,康征、齊小曼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45頁。
h南宮梅芳:《生態女性主義:性別、文化與自然的文學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頁。
iYnestra K.,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Plant J. ,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21~30. 轉引自武田田:《生態女性主義思潮中的溫馨小品——論〈與狼為伴〉中的兩性欲望與自然之關系》,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
j彭學軍:《油紙傘》,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頁。
k陳莉:《中國兒童文學中的女性主體意識》,海燕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頁。
l[美]卡拉·安布魯斯特:《水牛女孩們,你們今晚不出來嗎——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的越界需吁求》,轉引自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蔣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頁。
m彭學軍:《油紙傘》,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4頁。
n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87~102.
o[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4、237頁。
p[美]卡拉·安布魯斯特:《水牛女孩們,你們今晚不出來嗎——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的越界需吁求》,轉引自格蕾塔·戈德、帕特里克·D·墨菲編:《生態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蔣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頁。
q[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頁。
r[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審美之維》,李小兵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