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小說都是一根纖細的手指
李靜塵

“特里宜蘭,一個擁有百年歷史的先驅者村莊,被環抱在田野和果園之中。一座座葡萄園沿東邊斜坡延伸開去。一排排杏樹生長在臨近的公路旁。紅瓦屋頂沐浴在古樹的濃郁蔥翠中。”
這是阿摩司·奧茲筆下的特里宜蘭村,一個據說是在20世紀初期由猶太復國主義拓荒者創建的村莊,有著叢林、果園、百年農宅和紅色屋頂,甚至被視為以色列的普羅旺斯。
“這源于我做過的一個夢,在夢里面,我當時正走過以色列最古老的猶太村莊之一,這個村莊比以色列建國的歷史要久得多,是國父和國母在開國前150多年就創建而成的。夢中的村莊寂靜無聲,包括田野、農莊、房屋,所有都是空曠的。而我在尋找一個女人,后來情勢突變,變成別人在找我,我開始逃跑,躲藏。”早晨醒來,奧茲便決定以這樣的村莊為背景來開始創作自己的新作品,名為《鄉村生活圖景》。此次,阿摩司·奧茲帶著自己的這本新書來到了中國。
阿摩司·奧茲,以色列國寶級作家,主要作品有《愛與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爾》、《一樣的海》等。獲過包括以色列國家獎、費米娜獎、歌德文化獎在內的多項大獎,是諾貝爾文學獎多年的熱門人選。
“????(你好)”,奧茲用希伯來語和我們打招呼。他說在希伯來語中,這個詞有“你好、再見、和平”的三重含義。“在我們以色列,打招呼要說這個詞,離開跟人家道別的時候要說這個詞,在夢中祈禱和平的時候也要說這個詞。”
他穿著簡單的藍襯衫,黑西褲,袖子微微卷起,露出纖瘦的小臂。頭發是全白的,臉上戴著一副金屬框的眼鏡,鏡片雖然擋在眼睛前面,卻擋不住那股深邃且有神的目光,像一泓玉泉,又像一輪清月,透著猶太民族與生俱來的睿智。
故事是沒有結局的
奧茲的寫作生涯,始于母親的死。在他12歲的那年,母親不堪忍受沒有色彩的日常生活而選擇了自殺,而這給年幼的奧茲帶來了強烈的震撼。沒有擁抱,沒有解釋,母親就這樣不告而別了,他不解,甚至生母親的氣。平時的母親即使對路上的送貨人、門口的小販,抑或完完全全的陌生人,都會送上一個友好的微笑,幾句溫暖的問候,而又為什么會一聲不響地拋下了最親的人呢?他也生自己的氣,肯定是因為自己哪里出錯了,讓母親失望了,這才決定狠心地離開他。不過也正因如此,奧茲才開始用文字去思考生活的真相和人生的真義。在作品中,他時常關注形形色色、截然不同的家庭,家庭悲劇和夫妻情感成了他的主要內容。
《鄉村生活圖景》中的8個故事沿襲了奧茲一貫的主題和風格,而與以往不同的是,所有的故事似乎都沒有結局,沒有傳統的開頭、高潮和結尾,常常在讀者看到興起時結束,給人一種失重的感覺。
在開篇的《繼承人》中,一個自稱“遠房親戚”的陌生人闖進了阿里耶·蔡爾尼克的家,試圖說服阿里耶把年邁的老母親送到療養院,而后賣掉現居的老宅子來大賺一筆。陌生人的聲聲誘惑暗合了他內心偶爾冒出的陰暗想法,有時,與年邁母親分別的可能令他內心充滿憂傷和恥辱,有時他幾乎又在期待母親最終離去為他開辟種種可能。而后,陌生人竟然尾隨阿里耶走進房主老太的房間,“他脫下鞋子,親吻她沒牙的嘴,躺在她的身邊”。阿里耶也躺到了床上,陌生人一邊撫摸、親吻房主老太,一邊喃喃地說“我們會照顧這里的一切”。故事到這句話便戛然而止,讓讀者不禁懷疑是出版商漏印了后面的一部分,還是作者忘了寫結局呢?不只這一篇,書中的另外7個故事也篇篇如此,看不到結局,好像還未完待續。
對此,奧茲卻說, “除了死亡,我們人生當中的很多故事就是沒有結局的,是開放結尾的。有一對夫妻結婚十年了,離婚了就再也不見面,你覺得這就是結局嗎,這絕對不是結局,因為他們自己內心總會關懷另外一個人,或者他們有一個孩子,而且他們都會愛這個孩子;有一個人在工廠上班,有一天他被開除了,不論是他自己的錯誤還是其他人的錯誤,他就被炒魷魚了,你覺得這個會是故事的結局嗎?這個也不是。這個人內心深處會為了這件事情痛苦很多年的,對于開掉他的這個老板,他有時候夢里也會想起這個人。所以你問我結局,你告訴我到底什么才是結局?很多電影或電視劇的結局是兩個人結婚之后就非常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或是英雄把所有的壞蛋都殺掉了,整個世界就美好了,但是這并不是結局,故事是沒有結局的。”
好奇心是人類崇高的道德之翼
1789年,阿摩司·奧茲和他的同道成立了“現在就和平”的左翼組織,強烈反對戰爭,呼吁以色列執政當局承認巴勒斯坦人的自決權和建國權,要求以色列政府通過和平談判以及相互妥協的方法解決曠日持久的巴以沖突。
因為奧茲是一個愿意妥協的人,他相信妥協是可能的。他認為大部分以色列人都是溫和的,巴勒斯坦人也一樣。不過,小時候的奧茲卻不是這樣,他極度崇拜猶太恐怖主義者,曾經自己做了土火箭,想象著拿它摧毀白金漢宮。歲月的洗禮讓奧茲變得溫和、通達,他相信有一種比流血更好的解決爭端的方式。不過,奧茲的提倡遭到了一些年輕左派的指責,甚至有人說他是以色列的恥辱。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奧茲對這些不同的聲音既不惱怒,也不怨恨,反而覺得這是一件好事。“在以色列這樣一個大家庭中,有很多人一點都不喜歡我,一些人認為我是這個家庭的恥辱。但是這沒有關系,我很喜歡以色列的多樣性。我也不希望以色列就好像是一個獨奏的演唱會一樣,我希望它是一個由各個樂器合奏的音樂會。”
猶太人就是這樣一個不斷質疑和創造的民族,經常挑戰權威,有很多獨立的思考,猶太文明就是一種不斷批評他人和自我批評的文明。“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猶太人,包括了摩西和耶穌,斯賓諾莎和卡夫卡等等,大家如果閱讀他們的自傳的話,會發現他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思想之父,但是這些偉人又背叛了他們的父親,我也相信這就是創造力的源泉”。 《圣經》中也有這樣的例子, “上帝非常不喜歡索多瑪這座城市,就決定要把這座城市從大地上完全抹除,亞伯拉罕就對上帝說,稍等一下,如果索多瑪這座城市里面有50個好人,你還想毀滅這座城市嗎,上帝說這座城市太糟糕了,你絕對找不到50個好人,亞伯拉罕繼續說如果有40個人呢,哪怕30個、20個或是10個人呢?在跟上帝討價還價的過程中,他一點也不覺得害怕。”
身為猶太人的奧茲也深受這種文明的浸潤,好奇心和創造力讓他成為了一名優秀的作家。
除此之外,奧茲還認為“好奇心是人類崇高的道德之翼”,因為“一個有好奇心的人會比那種沒有好奇心的人更好”。因為有好奇心的人習慣換位思考,會時常問自己“如果我是對方,我會怎么樣呢?”所以,一個有好奇心的人會成為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更好的學者。
Q&A
Q:您如何看待自己在以色列文學中的地位?
A:但是如果你問我自己的地位,我會告訴你我不知道,這個是要讓我們的讀者和文學批評家決定的,可以說我國每一位讀者,每一位文學批評家自己心里面都會有一個作家的排名。我本人這一輩子從來沒有這樣的一個理想或者想法要成為什么領域的第一名,我上學的時候從來不是學生里的第一名,我也從來沒想過要當第一名,我當兵的時候也不是最好的士兵,我也從來沒想過我要做最好的士兵,我當時也從來不是最受女孩子歡迎的,但是我確實是很想受到女孩子歡迎。現在我成了一個作家,我自己內心也從來沒有想過說我要做第一,當然了,我希望我的作品被讀者喜愛。如果有一個讀者夜晚無法入眠,我會很高興他從書架里抽出來我的一本書,讓我陪伴他入眠,如果你問我在以色列文學這個排名里到底是排第一第三第五,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Q:您覺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沖突最終會和解嗎?
A:以色列是以色列人唯一的家園,巴勒斯坦也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家園,現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還不能在一起創造一個幸福的大家庭,因為他們不是一家人,也并不開心。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沒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所以現在唯一的一個解決方法是把這樣一個很小的房子分隔成兩個更好的隔間,我們雙方就可以毗鄰而居,可能不會彼此相愛,但是至少是和平地在一起。如果你問我什么時候會達成這個解決方案,我不知道,但是總有一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會居住在彼此的隔壁,甚至有一天你的鄰居可能會把你邀請到家里面來一起喝杯咖啡。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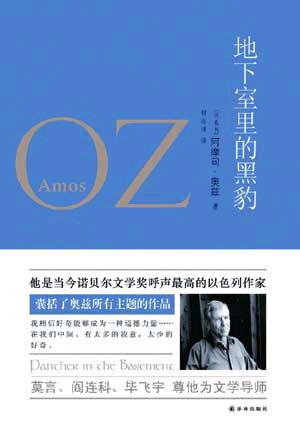

奧茲的記憶小說《地下室里的黑豹》希伯來語版首發于1995年,以其童年經歷為基礎,又融進了豐富的文學想象。在《我的海米爾》《鬼使山莊》等作品之后,奧茲再次把小說的背景設置于1947年夏天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階段,觸及了這一特殊歷史時期中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用奧茲的話說,故事本身來自黑暗,稍作徘徊,又歸于黑暗。2008年,該小說被美國導演林恩·羅斯改編為電影,講述了1947年以色列建國前夕,12歲的以色列男孩普羅夫和英國軍官丹羅普亦敵亦友的故事。


奧茲發表于2002年的自傳體長篇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被學界視為奧茲最優秀的作品,小說出版后沒幾年就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其英語版不僅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又于2007年入圍“布克國際文學獎”。小說以二戰之后飽受戰爭蹂躪的耶路撒冷為背景,從一個小男孩的視角講述了一個破碎家庭的悲劇故事,以及以色列誕生之時世界的動蕩與變化。奧斯卡影后娜塔莉·波特曼執導了《愛與黑暗的故事》同名電影,并攜這部導演處女作亮相2016年北京國際電影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