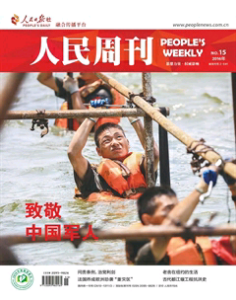法國咋成歐洲恐襲“重災區”
閆志剛
7月14日,法國國慶日。這個由“法國大革命”延續而來的日子,對于法國人而言意味著無限的榮耀。然而今年的國慶日卻充滿了“血色”。繼去年遭受兩次嚴重恐怖襲擊后,法國又一次遭嚴重恐襲。為何又是法國?這樣的襲擊是否還會發生?這是許多人心頭的疑問。
血色“國慶日”
當地時間7月14日晚22時,在法國南部城市尼斯,一輛卡車沖進正在觀看國慶日煙花表演的人群,造成至少84人死亡、300多人受傷。隨即,法國總統奧朗德就此事件發表電視講話。奧朗德表示,尼斯發生的這起事件明顯是“恐怖行徑”,他呼吁國內加強安保,同時宣布將法國目前的緊急狀態延長3個月。
令人震驚的是,這是去年1月《查理周刊》遭襲以來,法國遭受的第三次嚴重恐怖襲擊,法國儼然成為歐洲恐襲的“重災區”。
2015年1月7日,兩名男子攜突擊步槍闖入嘲諷雜志《查理周刊》的巴黎辦公室,造成包含8名漫畫家在內12人死亡。隔天在巴黎郊區1名女警遭槍殺,另有一間猶太超市發生持槍劫持事件,4名人質死亡。
2015年11月13日,在巴黎國家體育場附近,以及距《查理周刊》漫畫家們遭殺害的地點僅數步之遙的巴塔克蘭劇場,有9名男子分別引爆炸彈,向在酒吧與餐廳外享受夜晚的民眾開火,共造成130人死亡、350人受傷。IS在11月14日聲稱是他們所為。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周譚豪告訴記者,法國一直是恐怖襲擊多發地,在這三次恐襲之前,恐怖勢力一直將法國視為主要襲擊目標。據有關統計,2013~2014年,法國遭受恐怖襲擊的數量占到歐盟國家的39%左右。
為何又是法國
一年多時間發生三次嚴重恐襲,200余人遇難。人們心痛之余,不禁要問:為什么法國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傷”?在周譚豪看來,法國恐襲事件多發并非偶然,這與法國特殊“國情”相關。
從地理位置看,法國在歐洲申根區,距離中東、非洲比較近,恐怖分子容易滲透。尤其是當前的歐洲難民潮,讓IS等極端組織有機可乘。據黎巴嫩官員數據,前往歐洲的難民中有2%的比例牽扯極端組織,這個數量比較大且很難監管。
相比其他歐洲國家,法國穆斯林群體比較大,他們中的一些人容易受到極端思想的影響。而法國的移民政策則加劇了這一狀況。周譚豪介紹,歐洲對移民的融合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德國的“客工”模式,從哪里來回哪里去。第二種是英國的“放任自流”模式,彼此之間“井水不犯河水”。第三種則是法國的“強制同化”模式。按照法國前總統薩科齊的講法就是“身在法國皆為法國人”,在法國的伊斯蘭變為“法國的伊斯蘭”。
再往深層次原因,則是法國社會融合不夠。德國是單一民族,民族共識比較強,國民對政府的信任感比較強。而法國是國家建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在安全問題上,打個比方,如果社區發現異樣情況,德國人第一反應是觀察并報警,而法國人往往選擇躲避。正如學者所言:法國一向以高度多元融合而自豪,但實際上,不同信仰與文化的融合遠未實現。
與此同時,法國自身安防力量比較薄弱。法國在2015年才制定史上第一部《情報法》,法國的全國反恐中心建設也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在恐襲多發情況下,法國情報機構形同虛設,即便出臺了一些反恐措施,也因為國內政治掣肘在落實上大打折扣。7月15日,法國Ifop市場調查公司所做的調查顯示,67%的受訪者稱,不再相信總統奧朗德和政府能夠應對和打擊恐怖主義。
“同為西方國家,英美強調自由優先,法國則強調平等優先。因為過分強調平等,從政府到民眾,對情報安全部門在心理上是抵觸的。如果談起國內安保、情報工作,法國主流媒體首先會強調負面看法。相比于英美政治推崇的‘妥協文化,法國人骨子里有一種‘革命情懷,這一點從法國‘街頭政治盛行可見一斑。”周譚豪介紹說。
盡管如此,在周譚豪看來,恐襲多發的根源還在于法國經濟困境。2008年以來,法國經濟基本處于停滯狀態,許多人都覺得自己的“蛋糕”變小而變得不滿意。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又往往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此外,近年來法國先后在利比亞、馬里、伊拉克和敘利亞動武,引發極端勢力報復。而不少法國人受極端思想蠱惑成為潛在恐怖分子。據有關統計,為“伊斯蘭國”效力的3000多名歐洲圣戰分子中,有近一半為法國人。
“未來”會怎樣
恐襲多發對法國的打擊是顯而易見的,首當其沖的是法國本來就比較糟糕的經濟。作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旅游業占到法國GDP的7%。去年兩次嚴重恐襲后,今年1~4月,赴法旅游人數減少了13.7%,對法國經濟造成了不小沖擊。本次恐怖襲擊從巴黎蔓延到外省,所造成的沖擊會進一步加大。
周譚豪介紹,當前“伊斯蘭國”的策略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集中打擊少數國家,直到把這些國家的心理防線打崩潰為止。“心理上的恐懼對法國是最致命的”。
除了經濟沖擊,恐襲多發對法國乃至歐洲安全形勢也會造成負面影響。實際上,極端組織發動的恐怖襲擊,就是利用歐洲內憂外患之機,挑撥極右勢力與穆斯林移民之間的矛盾,從而造成極右勢力進一步做大,“樊籬主義”抬頭,進而讓局勢陷入惡性循環。有學者認為,法國恐襲多發反映出國際恐怖主義在歐洲的扎根,可能比人們想像得還要復雜,歐洲國家的防范力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周譚豪看來,當前歐盟正面臨經濟與安全雙重困境,英國“脫歐”對歐洲一體化進程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歐盟會有一個持續、深遠、廣泛的影響。“歐盟本來就內憂外患,本次恐襲后,歐盟所面臨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等于在本來就很渾的水中又撒了一把泥沙。基于對經濟與安全的現實需求,歐盟各國的博弈會進一步加劇。”
實際上,法國遭受恐襲后,并沒有坐以待斃,法國包括歐盟也出臺了一些措施,但回過頭來看所提出措施大同小異,而且真正落實的很少。原因一方面在于歐盟本身硬實力欠缺,另一方面則是“博弈太厲害,進程太曲折,形勢變化太快”。
“經濟與安全本身就是一個矛盾。確保安全就需要花錢,就需要更多的法律基礎保障,但發展經濟需要寬松的環境,需要人員的流動,這個度如何把握是一個問題,因此,歐盟未來的安全政策可能還會停留在‘小修小補層面,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周譚豪坦言道。
未來會怎樣?似乎并不容樂觀。正如媒體所言:事實上,法國每發生一次恐襲,就會帶來一次社會撕裂的隱痛,就會進一步引發排外情緒與極右翼政黨勢力的上升。奧朗德總統稱反恐“道路漫長且艱巨”,但誰該為無辜平民的傷亡負責,更是法國乃至整個歐洲要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