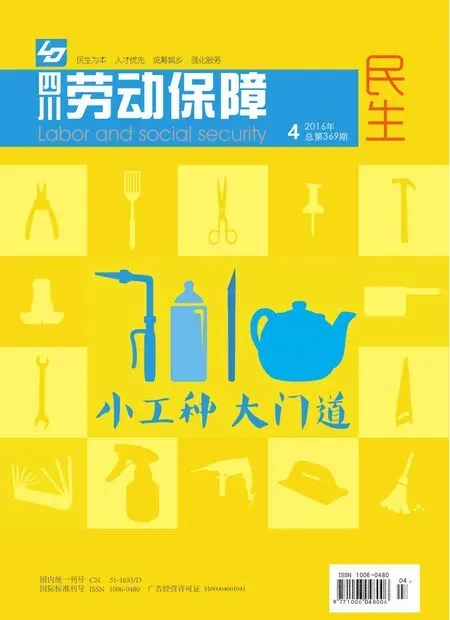突破困境讓農民工從“城市過客”成為“城市主體”
——專訪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進
文本刊記者 蔡蘭
突破困境讓農民工從“城市過客”成為“城市主體”
——專訪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進
文本刊記者蔡蘭

無論是“十三五”規劃,還是2016年的政府工作安排,都在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方面,做不遺余力的努力。但在實施過程中,仍然面臨很多現實困境。
黃進是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近年來,承擔了有關“新形勢下農民工社會政策轉型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合研究課題,他立足農民工的發展訴求,深入尋找農民工市民化的影響因素,以推進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日前,黃進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探討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意義,分析如何突破困境,讓農民工從“城市過客”成為“城市主體”。
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記者:您認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意義何在?
黃進:現在我們的問題是什么?農村凋敝,農業不景氣,農民日子清苦。事實上,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得到解決。首先,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市民化之后,農村人口減少,土地實現規模化經營,農業的問題可以得到改善。其次,農民工市民化之后,生活水平提高,農民的問題也可以得到解決。最后,農民工市民化,加上新農村建設,農村的問題也隨之得到改善了。
另外,農民工長期處于城市社會的邊緣,既難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更享受不到城市市民應有的權利。還有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流動兒童等都成為重大的社會不和諧問題。只有農民工市民化,才能讓農民工在城鎮定居安家,認同城鎮,增強對城市社會的責任感,促進新市民與老市民的和諧。
當然,農民工市民化也是產業轉型發展、擴大內需、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需要,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必然階段,我們應當順應歷史潮流,積極推進農民工市民化。
不愿農轉非 需除后顧之憂
記者: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使農民工真正市民化,將是“十三五”期間的一個重要任務。但四川省統計局發布的《2015年四川農民工市民化調查現狀》顯示,半數以上農民工不愿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您覺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黃進:農民工不愿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主要原因之一還是不愿放棄農村土地經營權。對農民工來說,最大的物質資本就是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土地承擔著農民多項社會保障的功能。對于大多數農民工而言,帶著美好的愿望離開家鄉投入到城市建設中,因為無法在城市獲得穩定的生活保障,而沒有真正地離開農村,割舍對土地的眷念。這就需要促進農民工在農村的存量資產轉化為市民化的資本,如土地承包權、宅基地等。
在實踐中,要探索實行股份合作、“大園區+小業主”等多種形式,依法自愿有償推進土地承包經營權規范有序流轉,搭建土地經營權流轉平臺,維護農民工在農村的利益,為農民工市民化提供更多的物質支持。同時,宅基地在本質上是農民作為國家公民應當享有住房保障權的體現,也是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當享有的經濟權利。農民工進入城鎮也應當享有住房保障的權利,但實際上一旦農民離開農村,其住房保障權利處于實際的“落空”狀況,因此關于農民工在務工地的住房保障問題,是其公民權的體現,是解決農民工發展訴求的必然環節。
提升社會資本 讓心理同步“進城”
記者:多數農民工在市民化進程中,雖然人已經進城了,但他們在思想觀念、社會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并沒有同步“進城”,這樣的狀況應如何改善?
黃進:我認為我們常說的市民化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職業的市民化,從農民到工人;其次是身份的市民化,從農村戶籍到城市戶籍;最后是心理的市民化,在文化、心理層面融入城市。最后心理市民化階段才是市民化的終極目標,同時,也是最難實現的。
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是政府,社區、社會組織、農民工自身都需要努力。首要是農民工要實現穩定地就業,才能讓其在市民化之后體面地生活。其次,提升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最后,不能將農民工孤立起來,政府為農民工修建的廉租房、公租房不能太偏遠,應該跟城市居民融合居住,加強交流溝通,增強城市認同感。幫助其構建城市網絡、社會關系、實現穩定就業等。
新生代農民工是“漂泊”的一代
記者: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相對于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有哪些特點?
黃進:在新生代農民工的成長階段里,國內經濟、社會、文化、體制發生了重大改變,與此同時,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急劇發展,全球化的步伐也在加快,令年輕一代農民工身上帶有這個時代特有的色彩。
新生代農民工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較高。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各類信息,相對父輩眼界寬廣,對個體的發展訴求強烈,有很強的自我實現意識。同時,新生代農民工對在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質量相對于老一代農民工有更高的期待,市民化訴求更高。一方面,思想意識、行為方式、生活習慣已經趨于城市化,對土地的情結也日趨弱化。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不再滿足于在城市維持生存,不再僅僅注重薪酬,而是開始關注掌握一門可在城市立足的技術,關注工作環境和權益保障,關注個體的精神感受。
記者:目前新生代農民工的市民化有哪些困境?
黃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新生代農民工更趨向于“雙重邊緣人”,出生在農村(也有的出生在城市),生活在城市,既不是農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我們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村的距離越來越疏遠,無任何務農經歷的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為50.7%,在15—30歲的農民工中,無務農經歷的比例高達56%。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農村已經沒有了留置的物質依托。他們滿懷希望地來到城市,卻遭受排斥,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和主流生活,而他們又不愿意回到農村。調查結果還顯示,24.58%的農民工非常愿意到城鎮永久居住,25.42%的農民工比較愿意到城鎮永久居住,二者合計達到50.00%,高達72.42%的新生代農民工不愿意回到農村。
而且,新生代農民工資本缺乏、能力貧弱,是導致農民工問題仍然嚴重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第一代農民工,但是與城鎮青年的受教育程度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同時,新生代農民工雖然生活在城市,但單一的社交關系并沒有幫助他們建立起以業緣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網絡,使得其并沒有建立起再生性社會資本。
需要制度頂層設計
記者: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改革涉及公共服務制度、社會保障制度、住房制度、財稅制度、土地制度及戶籍制度等方方面面。對此,您有什么思考和建議?
黃進:如何解決農民工問題,提出適合時代發展需要和農民工自身需要的農民工政策是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目前關于農民工市民化很大的問題在于政策的區域性和分散性。盡管國家已經出臺了保障農民工權益的綱領性文件,但對于農民工市民化這一基本訴求的具體政策性文件還非常少。
舉個例子,一個農民長期在廣州務工,現在他想回到四川發展,可是他在廣州這么多年繳納的社會保險怎么辦,能不能轉回四川?在現實中轉不了。他最多只能將自己繳納的部分提取出來,單位繳納的部分只能被放棄。
不僅如此,農民工的社會保險在全國存在多種不同的模式:以成都、上海為代表的獨立型綜合模式,專門給農民工建立了單獨的社會保險,獨立于城鎮職工基本社會保險體系。深圳、廣州是另一種模式,將農民工社會保險統一合并到城鎮職工基本社會保險。當然這種模式在近期已經改變了。
區域性的政策不能適應農民工的流動性需求,這就要求系列化的頂層設計,從國家、中央層面進行政策的保障和完善,給農民工市民化確定的預期,這才是未來農民工市民化的可持續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