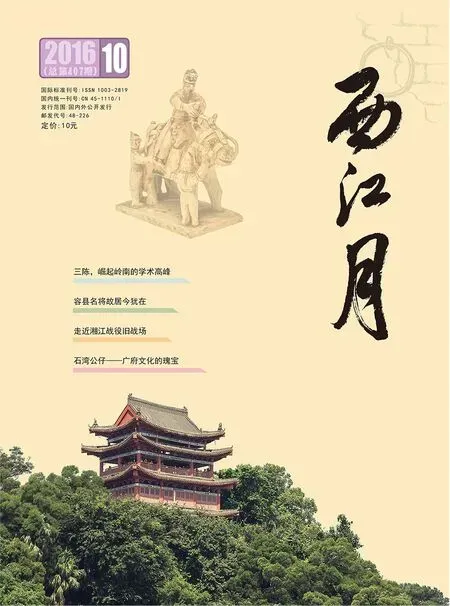拜謁興教寺有感
木 子
拜謁興教寺有感
木子

終南山下的護國興教寺
早就聽說終南山下的護國興教寺是瞻仰玄奘遺跡的勝地,于是我帶著一腔虔誠前往拜謁。人還未至山門,便遠遠聽到寺院里傳出的鐘聲,沿著終南山傳揚開來。那木頭撞擊鑄鐵的余音,散發出凝重的顫音,深遠而充滿禪意,似乎要穿透寂靜,又似乎在冥冥中召喚,讓凡人忘卻諸多煩憂。
走進寺內,我仔細端詳和撫摸這見證了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古剎。這座當年的大唐護國興教寺,坐北朝南,殿堂、經院等一應建筑依山而建,蔚為壯觀,那氣勢曾一度壓倒京城長安。
凡物皆可來,凡物皆可去。在時光流逝和風雨侵蝕中,那曾經出入無數皇親國戚的磚木構筑的山門,早已失去了以往的恢宏和莊嚴,但那份從容,卻彰顯著萬事隨緣的心態。沿著靜謐的山道行走,老樹的虬枝斜斜地倚靠著古舊的山門,唯有殘垣斷壁上的朱紅色,仍讓人心頭為之一動。如今興教寺周圍已少有人跡,但千百年的風雨,卻無法掩蓋它在鼎盛時受萬人膜拜的輝煌。
寺廟周圍樹木蒼郁,時有誦經之聲響起。此時此刻,感覺你、我、時空皆成了景致。置身于迷蒙的云海中,光線從綠色間隙中漏下斑斑點點的碎光,大殿上的脊獸、飛檐下的鈴鐺皆為風景,此時的寺廟,把天地的氣息與靈性全部凝結其中,神秘而又華貴,容納了人間諸多的精神祈求。
人在寺院中,鳥語花香處處。在唱經聲和鐘聲的余音里,我和一位在樹下掃地的僧人交談,他的淡然如花開花謝,沒有對名利的渴望,沒有對世俗的羈絆,有的只是悠長鐘聲之后的清澈沉靜。一聲佛號一聲心,聲聲佛號蕩滌著人們內心的焦躁。置身寺中,無論觀光的行人還是朝拜的信徒,身心都可以在幽靜中漸漸放松。
從山門到大殿,從經堂到僧院,無論走過多少回塵緣,不變的是無比的虔誠,不變的是自然景色和莊嚴建筑的相融。那些不經意的景色,恍若錯落有致的畫卷,靜寂下令人油然而生相見恨晚的感覺。身處寺廟,身心泰然,情緒也如山間清泉一樣透徹,如同穿越到了另一個世界。寺廟的內斂、安靜、大度、容納以及獨處一域的格局,表現出一種古今融合的宜人氛圍。墻外是茁壯拔節的蔬菜、姹紫嫣紅的花叢、蒼翠蔥郁的松柏竹林,那是一代代僧人們日日勞作的心血。日落山水靜,為君起松聲。這樣的和諧環境無法不讓人的身心安靜下來。一千多年來,終南山里眾多寺廟興衰交替,而興教寺更多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無所謂是否被喜歡、被理解。
興教寺雖多次歷經戰火,幾度坍塌荒蕪,但玄奘和兩個弟子的舍利塔卻一直得以幸存,三座靈塔呈品字形排列,在樹的掩映之下,似乎依舊在述說著行善積德的修禪妙法。當年玄奘大師跋山涉水,冒著生命危險從天竺取經歸來,帶回了657部經卷,那些傳世2500多年的梵文真經里,滿含著一位僧人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執著。雖然真經現今留存在世的真跡不足20片,但片片經文背后都是一種精神的弘法。
唐貞觀七年,玄奘大師從印度取經歸來,他沒有留戀盛世長安的繁華,自從受到唐高宗厚待邀請至此后,他19年中幾乎沒有好好休息過,將全部心思都融入了佛經之中。當20萬字的煌煌大典《大般若經》譯完的那一刻,他并沒太在意國內外佛學界的強烈反響,而是獨自面對著蒼蒼終南閉目誦經,并在當夜圓寂了。眾弟子舉行完佛事活動后,將玄奘的遺體運回長安。唐高宗聽到噩耗后不住落淚,并宣布舉朝為玄奘致哀,連連哀嘆:“朕痛失國寶矣。”隨后敕令將玄奘安葬在長安東郊的白鹿原上。
白鹿原地勢高坦,風和日麗之時,能從皇城的含元大殿內看到白鹿原上玄奘的墳墓。唐高宗常常是屢看屢次傷心落淚,于是詔令將玄奘的遺骨遷葬到遠離長安城的樊川風棲塬上,修建了五層靈塔供人拜謁。玄奘塔為方形五層磚木結構,唐肅宗為玄奘的舍利塔題寫了塔額“興教”二字,其意是要繼承玄奘的事業,大興佛教,之后千余年間,幾度枯榮,歷盡滄桑。傳說玄奘塔建好后,附近的百姓經常會發現塔尖上有佛光環繞,皆認為是佛祖顯圣,便在塔旁興建起了龐大的寺院,命名為大唐護國興教寺,為唐代八大寺院之首。
走出寺院,我恍若過了千年。回首興教寺,我的腦海中仿佛響起了盛世大唐的鐘聲,那鐘聲如同滑落的樹葉飄向遠方。我想,此生我來,雖然只是匆匆而又匆匆的一瞬,但至少也算是在凡塵中的一次修行了吧?
責任編輯: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