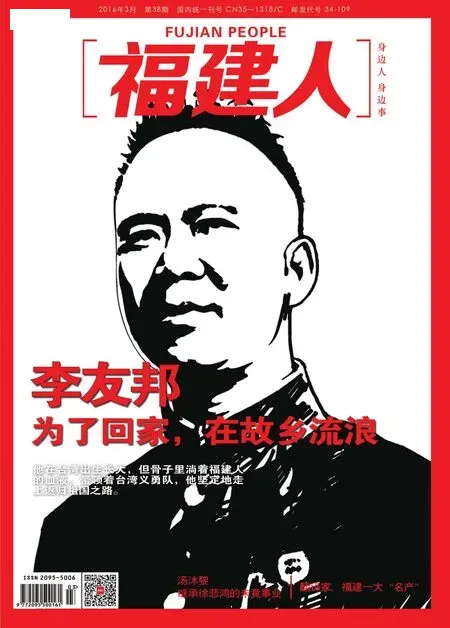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單位、地域能夠把一個翻譯家定義為什么籍、什么派只有閩籍翻譯有這種資格
中國從來沒有一個單位、地域能夠把一個翻譯家定義為什么籍、什么派只有閩籍翻譯有這種資格

鄭振鐸翻譯的《飛鳥集》。
2015年7月,翻譯界里出了件大事。作家馮唐翻譯的泰戈爾名著《飛鳥集》面世,譯文中類似“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解開褲襠”“有了綠草,大地變得挺騷”“我會給你新生噠”這樣的句子在網絡上受到了廣泛關注,被指“充斥著荷爾蒙的味道”,質疑之聲鋪天蓋地。
《人民日報》更是在2015年12月24日這天,刊文《莫借“翻譯”行“篡改”》,批評馮唐的譯文“低俗不雅”,缺乏對經典的尊重。文中引用了嚴復在《天演論》例言中提出的翻譯理論,并提及:“《飛鳥集》的近十個中文譯本里,公認以鄭振鐸譯本為最佳,讀者在批評馮譯本的時候,也往往引用鄭譯本作為對比。”
其實,像嚴復、鄭振鐸這樣的翻譯界大牛,福建還有很多呢。
福建什么人多?翻譯家呀!
從現在開始,外省人問你福建有什么名人,別老是和他們扯張靜初、姚晨、陳赫、方舟子、陳凱歌了,你應該驕傲地告訴他們,咱們福建盛產翻譯家,不僅多,還都厲害著呢!
估計在大多數人的心里,翻譯這事,是近現代才出現的。其實早在18世紀初,莆田人黃加略就已經旅居法國,成為第一個把中國小說譯成法文的人,還獲得了“法國皇家文庫中文翻譯家”稱號,被譽為譯壇先驅。
敢第一個吃螃蟹的,那都是牛人。林則徐的名字算是家喻戶曉了,可他“倡西學之始,開新學之路”這事,還是值得大書特書。他最早組織翻譯班子,譯了大量的外文書籍和西方報刊,開了中國現代翻譯的先河。由他根據英國人慕瑞《世界地理大全》匯編而成的《四洲志》,則是我國第一部較系統的地理著作。
1850年,林則徐逝世,這對于翻譯界來說真是一大憾事,而就在這一年,又一個厲害人物——羅豐祿出生了。這個福州人會五國語言,是李鴻章的英文秘書、外交顧問兼翻譯,在外交界里混得那叫一個風生水起,號稱“民國第一外交家”。
和羅豐祿同樣在福州船政學堂讀過書的陳季同,號稱“東學西漸第一人”。他率先把《聊齋志異》翻譯成法文出版,一年里就再版了三次,在法國那叫一個受歡迎。更了不得的是,陳季同不僅自己搞翻譯,在他的影響下,他的弟弟陳壽彭也搞起了翻譯。
1713年10月至12月這段時間,在黃加略的巴黎寓所里,孟德斯鳩和黃加略高談闊論。雖然不知道這兩人有沒有一起看雪、看月亮,但他們卻實實在在從中國的宗教談到刑法,從服飾談到墓葬,從文學談到科舉,從婦女地位談到國家性質。為了紀念彼此純潔的友誼,孟德斯鳩還特地做了筆錄,將談話內容整理成文,最長的有20頁之多,題目就叫《關于中國問題與黃先生的對話》。

林則徐開了中國現代翻譯的先河。

羅豐祿會五國語言,是李鴻章的英文秘書、外交顧問兼翻譯。
以下這兩位福州人,也是知名的外交翻譯家。
凌青:新中國外交元老,林則徐玄孫,上世紀80年代任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并四次出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
羅旭:中國外交界“五朵金花”之一,她的叔曾祖就是晚清出使英、意、比三國的羅豐祿,祖父羅忠堯曾任晚清駐新加坡總領事。
除了陳季同、辜鴻銘、林語堂,還有不少閩籍翻譯家把中文著作推向了世界。
許孟雄:最早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多篇著作譯成英文。
張培基:譯注了《英譯中國現代散文選》,編寫的《英漢翻譯教程》被許多高校選定為英語專業翻譯課教材。
羅郁正:將中國古典詩詞翻譯、編輯成《葵曄集》《待麟集》在美國出版,并把北島、顧城等人的“朦朧詩”譯為英文介紹給西方讀者。
陳壽彭和他的妻子——中國第一位女翻譯家、同樣是福州人的薛紹徽,第一次將凡爾納的《八十天環游地球》翻譯成了中文,在國內掀起了一股凡爾納熱潮。總之這一家子呀,是和翻譯“杠”上了。
說到福建的翻譯家,有個被提了又提,又不得不提的人。估計你也猜到了,就是那個不會外語,卻翻譯了《巴黎茶花女遺事》等180多本外國小說的林紓。
當然了,說到奇,林紓的段位還是遠遠比不上“清末怪杰”辜鴻銘。這位祖籍惠安的老先生精通9種語言,獲得過13個博士學位,極為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他把四書里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翻譯成了英文,在西方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怪不得外國人要說:“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你以為這就完了,不不不,福建的翻譯能人還多著呢。林語堂、鄭振鐸、冰心、許地山、楊騷、梁遇春……這些人都是近現代文學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文采斐然毋庸置疑,而在翻譯這事上,他們也是棒棒噠。

陳季同率先把《聊齋志異》翻譯成法文出版。

辜鴻銘把四書中的《論語》《中庸》和《大學》翻譯成了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