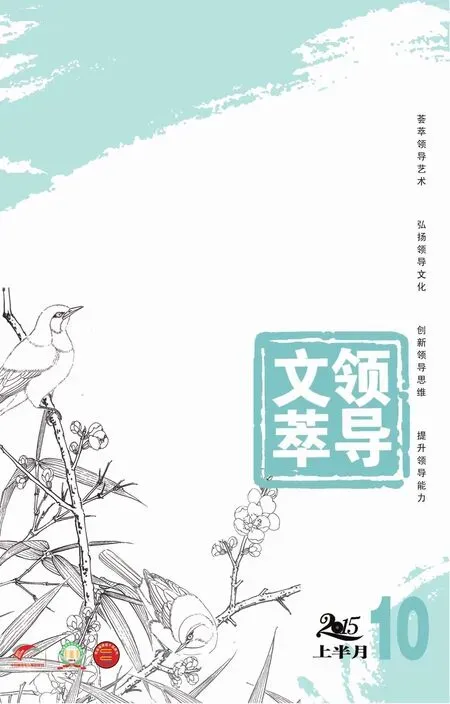宋朝官員難欺上有何玄機
李之亮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宋朝為官的常態
宋朝建國不久,朝廷陸續在州郡設立了“通判”一職,宋朝設通判的本意,是想讓這個角色對知州知府起到監察的作用。通判的設置,為知州知府加上了一道緊箍咒,有效規避了州府一把手獨斷專行的可能,他們不受知州知府甚至上級路分大員的轄制,直接對朝廷負責。與漢代設立部刺史相比,明顯嚴密了很多。
宋朝政區劃置采取三級制,即中央之下設路,路下設府、州,府、州下設縣。一般說來,路里設安撫使司(帥司)、轉運使司(漕司)、提點刑獄司(憲司)、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司(倉司),統稱“四大監司”。帥司主軍政,漕司主漕運,憲司主刑獄,倉司主倉儲,各管一攤,互補統轄。看上去四個平行的職能部門除了“各管一攤”的分權理念之外,另賦予各司主管官員以監察之權,這就好比朝廷在每個官員的身邊同時安裝上諸多的“監控探頭”,令所有官員都心懷畏謹,不敢輕易欺瞞朝廷,一旦其欺瞞作假的行為被任何一個“探頭”監測到,后果將十分嚴重。對宋朝官員來說,“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是為官的常態,為官者率皆如此,最高統治者獲取各方面信息的渠道就大為暢通了。
宋朝官民有多種傳遞信息的渠道,甚至可直達御史臺
宋朝統治者對信息暢達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上情下達者如通進司和進奏院。《宋史·職官志》記載,通進司掌接受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的奏牘及文武近臣表疏章奏,具其要點進呈皇帝。進奏院掌三省、樞密院宣札及六曹、寺監的符牒,然后頒于諸路。下情上達者如登聞檢院和登聞鼓院,掌受官員及士民所上章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理雪冤濫等,在登聞鼓院遞上奏狀,如不能及時得到處理,可到登聞檢院繼續申訴。《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七載,仁宗天圣七年再置理檢使,由御史中丞親自兼任,原因是“冤濫枉屈而檢院、鼓院不為進者,并許詣理檢使審問以聞”。這說明宋朝官民有各種傳遞信息的渠道,甚至可以直達御史臺,即使中間某些環節發生打壓欺瞞、不作為或亂作為,也封不住任何一個人的嘴。
宋朝官員很難堵塞信息傳遞之門,下情上達的
信息渠道非常豐富
除上述通判、監司、鼓院、檢院等制度外,宋朝還有一些臨時性或輔助性措施,如“風聞”,指的是不必證據確鑿,只要聽到風聲,即馬上進行深入調查核實并予以處理。“體量”和“照勘”(勘會)等詞語在宋朝史籍中也經常出現。所謂體量,即下層出現問題后,朝廷便派官員到事發地進行“一對一”的精準處置。《長編》卷八八(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戊申)載,河北轉運使隱瞞了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澶州(今河南濮陽)、相州(今河南安陽)的霜旱災情,當地民眾不得不到京城擊登聞鼓訴冤。宰相請命當地轉運使體量災情,真宗說道:“因為轉運使隱瞞了災情,使當地民眾沒得到朝廷應減免的稅賦。為弄清實情,朝廷必須再派大員到當地核查,按實際情況進行稅賦減免。”宋朝的體量制度具有很強的機動性,且涵蓋各類事務。而所謂“勘會”,即朝廷派專員到事發地詳細核查,代表朝廷進行案件的審理處置。
從以上諸例可以看出,宋朝信息渠道的設計是十分嚴密、豐富而暢通的,任何一個環節的官員想堵塞信息傳遞之門都很難做到。
腐敗致紀綱毀壞,信息渠道和監察手段成為徒有虛名的擺設
然而事物總是處在轉化中,宋朝對官員弄虛作假的監控手段再嚴密再合理,也很難一勞永逸地施行下去,究其原因,還是官場腐敗惹的禍:制度都是人定的,又都是由具體人來實施的,一旦實施這些制度的人特別是高層官員蛻變成了貪瀆之徒,制度和規矩便成了一紙空文。上面提到的通判,本是監察郡守和縣官的人,這樣的人變了質,結果可想而知。王明清《揮麈余話》卷二說:“丁廣嘗任保州(今河北保定)教授。郡將武人,而通判者戚里子,悉多姬侍,以酒色沉縱。會有道人過郡,自言數百歲,能煉大丹,服之可以飽嗜欲而康強無疾,然后飛升度世。守、貳館之,以先生之禮事之。選日創丹灶,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于背。”由此可知,知州是個沒文化的武夫,通判是個紈绔成性的外戚子弟,兩人為長生不老享樂無極,連正常郡務都撂在了腦后。奇怪的是,這樣的官員居然沒受到路分監司的糾察,可見此時的監司大員、知州通判都已成了什么樣子,靠這樣的官員治理地方,再嚴重的問題也不可能如實反映到上層,朝廷設置的所有信息渠道和監察手段,都成了徒有虛名的擺設,何談吏治清明,下情上達?不光是宋代,歷朝歷代的覆亡無一不是因“紀綱毀壞”所致,因此采取各種有效手段杜絕腐敗,才是執政者的頭等課題。
宋朝的頂層設計值得后人借鑒
宋朝的監察、問責、多渠道疏通等制度堪稱完密,這種煞費苦心的頂層設計是很值得后人借鑒的。
第一,最高層不能奢侈腐化。為什么從宋太祖到宋神宗這段時期貪瀆腐敗難成氣候?根本原因是這幾代帝王身為表率,宰輔大臣皆以國事為重。同樣還是宋朝,同樣是太祖太宗的子孫臣民,到了徽宗朝,政風民風怎么就變得烏煙瘴氣了呢?究其根源,還在帝王本身,徽宗不恤國事,生活極度荒淫腐化,成了引領壞風氣之先的罪魁禍首。有這樣的帝王帶頭,上起宰輔,下至民商,無不效法,再談治國理民清正廉明,無異于癡人說夢。
第二,為保政令暢通、下情上達,必須要做到法治嚴明,當重懲者絕不能手軟。北宋前期統治者除了能以身作則之外,對膽敢以身試法者的處置也是非常嚴厲的,輕者罷官,重者流放編管直至死刑。如果一個官員犯了律條,僅僅給他個不疼不癢的處分,不僅不能令萬眾悅服,也完全起不到懲前毖后的作用。當官場風氣敗壞到令人發指的地步時,作為統治者就必須用“重典”加以整肅,才能使官吏產生敬畏之心。
第三,連坐制度仍可借鑒。上層官員保舉對象如果出現大的過錯甚至犯罪,則保舉者必須受到相應的處罰,這是肅清吏治亂象很有效的一種制度,它不單會使保舉者心有所畏,還能杜絕結黨營私。只有出以公心保舉人才,才能激發舉薦者的責任感和正能量。
第四,鼓勵和保障官民通過多種渠道向上傳遞信息,這也是確保各級官員不敢欺蒙朝廷的有效手段,如上面所引《長編》例,盡管河北轉運使隱瞞了大名府等地災情,百姓還可以通過登聞鼓院向上反映。試想如果沒有登聞鼓院,這三州百姓豈不是有苦無處訴了?
(摘自《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