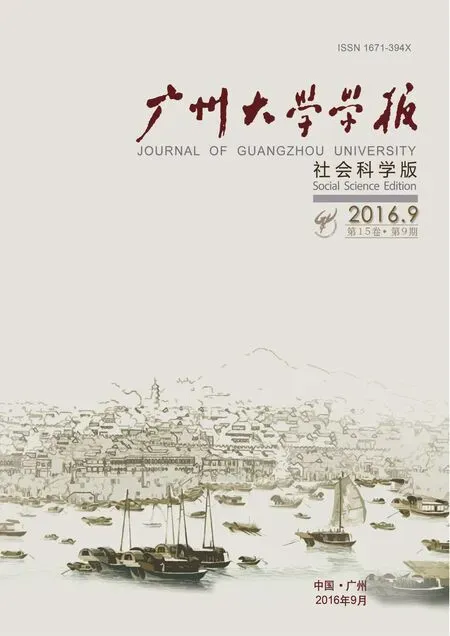汪辟疆與《水經注》——以新發現的批本為核心
孫 靖, 王 媛
(南京大學 文學院, 江蘇 南京 210023)
?
汪辟疆與《水經注》
——以新發現的批本為核心
孫靖, 王媛
(南京大學 文學院, 江蘇 南京210023)
著名學者汪辟疆先生十分重視《水經注》一書。南京大學文學院圖書館藏有《水經注》十冊,經著名學者汪辟疆批校。書中保存了汪氏大量的批點文字,并有其手書題跋多通,頗具文獻價值。
汪辟疆;《水經注》;批校
一、 汪辟疆手批《水經注》概況
汪辟疆(1887~1966),名國垣,字笠云,號方湖、展庵,江西彭澤人。先生是近代著名目錄學家、藏書家,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目錄學研究》《光宣詩壇點將錄》等,另有程千帆先生編《汪辟疆文集》,學術事跡詳見張亞權編《汪辟疆學術簡表》。先生藏書豐富,曾于南京曬布廠五號建“小奢摩館”庋藏之。其中不乏古籍善本,但因抗戰西行入蜀而損失殆半。余者由其后人于1976年和1978年分兩批捐入南京大學圖書館,計有經部21種,史部66種,子部41種,集部202種,類叢部5種,新學1種,另有鈔本6種,共計342種3 865冊。筆者近日在整理南京大學文學院圖書分館善本古籍時,發現贈書中有經先生批校本《水經注》,頗有文獻價值,故撰文予以揭示。
汪氏自幼受于庭訓,秉承家學,及長博學多識,建樹頗多。雖不專治酈學,但關注《水經注》由來已久。其在為學生霍松林藏《杜詩鏡詮》所撰題識中,將《水經注》與《詩經》《莊子》《楚辭》《史記》和《杜工部詩》并列,并認為此六書“為治文學者必須熟誦而詳說者。首訓詁,次語法,次考證,最后通義旨,不可放過一字,不可滑誦一句,不可忽略一事物,寢饋勿失,終身以之,有余師矣”[1]641。先生早年著手《水經注》的相關研究,至中年而用力更勤。先生嘗云:
在抗戰初起的時期,我因避亂到重慶鄉間居住,偶然地把手邊戴震《水經注》,從頭至尾細細讀過了一遍。……但是因為借書困難,而我行篋所攜,只有趙一清乾隆五十一年重刊本和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不全稿本,后來又借到沈炳巽《水經注集釋訂訛》、王先謙《合校水經注》,仍然闕乏甚多,這工作只好擱下。[2]118-119
可惜先生龐大計劃最終未能實現,僅有數篇文章問世。據陳橋驛統計,此類文章可見者共九篇,*此九篇文章為:《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時事新報》副刊《學燈》1940年第69、70期)、《致胡適論〈水經注〉書》《水經注疏》(1943年)、《熊會貞遺事》(1943年)、《李子魁攜〈楊守敬熊會貞合撰水經注疏〉全稿》(附于《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后)以及《楊守敬熊會貞傳》(《中國學報》1943年第1卷第2期)、《分析〈水經〉和〈水經注〉作者的分歧問題》(《江海學刊》1958年第1期)、《〈水經注〉與〈水經注疏〉》(《中國》文學第1卷第4期)、《〈水經注〉的版本和整理工作》(《申論》1948年第1卷第10期)。其中后四篇收入《汪辟疆文集》。(陳橋驛:《水經注論叢》,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31-132頁)。另有《為什么要研究水經》一文,刊登于《讀書通訊》1943年第65期。其中《分析〈水經〉和〈水經注〉作者的分歧問題》考訂兩書作者,論證精辟,結論公允。《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則縱橫評價明清六百余年酈學研究,甚見功力。然學界對汪氏酈學之成就論證有限,僅陳橋驛《汪辟疆與〈水經注〉》一文有所發現,且此文重在辯證由于李子魁的作偽導致汪辟疆“把一部雜湊而成的楊熊舊作誤作《水經注疏》的‘謄清正本’”[3]137,并未深入研究汪氏酈學。故此本之發現,對于剖析先生的治學歷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南京大學圖書館及文學院分館藏有汪辟疆先生捐贈《水經注》不同版本十種,如明嘉靖十三年(1534)黃省曾刊本《水經注》、明萬歷十三年(1585)吳琯刊本《水經注》、明鐘惺譚元春評崇禎刊本《水經注》、清戴震校乾隆三十九年(1774)武英殿刊本《水經注》、清趙一清校乾隆五十一年(1861)畢沅刊本《水經注釋》、清光緒十八年(1897)王先謙刊本《合校水經注》、1935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永樂大典本《水經注》、1957年科學出版社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等,其中只有本文所述黃晟刊本《水經注》與朱謀瑋《水經注箋》經先生批點。而先生手批《水經注箋》匯合眾本予以校勘,批文或轉引他書少有考證,或據他本校正鮮下己義,多襲前人舊說,且先生所參考校本難以明確斷定。先生嘗將戴震《水經注》校語抄于天頭,時有“戴云”如何,然后加以己意按斷,多有批駁戴校之處,惜此種批文數量較少。對于經注區分,先生則多據他本(疑為殿本)以改。故《水經注箋》批文,多據他本作精細校勘而少有先生個人觀點,其價值尚有待進一步發掘。
汪氏批校本《水經注》四十卷,題漢桑欽撰,北魏酈道元注,索書號:善D686/22,凡十冊。每半頁十一行,行大字二十一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單黑魚尾,魚尾下記書名、卷次,版心下記頁次、字數。書前有牌記“天都黃曉峰校刊/槐蔭堂藏版”*黃曉峰即黃晟(1684~?),字東曙,一字曉峰,號退庵,安徽歙縣人,遷居揚州,著名刻書家、藏書家。先以經營鹽業致富,后轉向藏書、刻書。刊刻有明王圻、王思義父子合輯《三才圖會》一百零六卷、《太平廣記》五百卷、王士禎《帶經堂集》九十二卷等。書印有“黃晟東曙之印”“曉峰一字退庵”“黃晟東曙氏一字曉峰”和“重校刊于槐蔭草堂”等。,又有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李長庚序、元歐陽玄《補正水經序》、酈道元《北史》本傳,書后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新安黃曉峰跋。字體屬清中期流行之寫刻,柔軟工整,頗有顏體與柳體融合之貌,亦是乾隆時期的字體特征。卷一有六方朱文藏書印,其中三方屬汪辟疆,從上至下依次為“辟疆校讀”朱文長印、“方湖長”朱文方印、“汪辟疆”白文方印;*據張亞權考證,汪辟疆先生1954年中風致右肢癱瘓,遂以左手代寫,而汪先生手稿中有“方湖左手”款并鈐“方湖長”印,此印當為1954年之后所用。故此批本所鈐“方湖長”恐為日后所補。“汪辟疆”印則出自傅抱石之手。以上數印辨識參考張亞權《汪辟疆先生“方胡行篋所攜”印譜考釋》,《古典文獻研究》第十三輯,鳳凰出版社,2010年6月。另有“異書多自散余收”白文方印、“漪主人”朱文方印。卷一首行有題識一行:

甲辰四月讀于開封 國垣記。
書后又題識兩行:
此本為余十八歲時所讀,就中章句點逗,頗有失誤。偶從敗麓中得之,獨為完好,遂付裝潢,以存少年時校讀之跡,并留示子孫,不足為外人道也。甲子三月靜便。
題識后并鈐有“汪辟疆”朱文方印。由汪氏生平可知,“甲子”當系1924年,此年先生在江西。“甲辰”則為1904年,此年先生“十八歲”,隨父入豫,進河南客籍高等學校,至1909年均就學于此。卷首目錄后又有六行題識:
前清光緒三十年,隨侍梁園,客有在先生座上談六朝酈道元文章之美,而其所著之《水經注》尤視為讀《史》、《漢》佐證,揭水道以疏古今地理,而并詳其經流之古跡勝覽。山水靈奇,丘壑存廢;金石標題,孕育靈秀。沾溉靡盡,心竊志之。是年二月,于相國寺售書攤得朱謀瑋《水經注箋》原印本,頗為珍視。嗣又得黃晟本于“好古堂”,即此本也。黃刻頗存朱《箋》而文又削剔之,又不標朱說,似欲竊為己有。然以刊刻尚佳,頗便誦讀,因日讀四五頁,逾年而畢。惜爾時閱書不多,就中頗有失讀處。今亦不更正,一存其真。己巳六月,方湖記于老灣新舍。

光緒三十年為甲辰年,即公元1904年,己巳年為1929年。是則先生1904年2月在河封相國寺獲明朱謀瑋《水經注箋》,尋又得清黃晟刊《水經注》,于4月開始批閱,約至次年讀過一遍,并有批校。此后先生輾轉北京、上海等地,多次搬遷。至1924年3月,先生在南昌心遠大學教授時,又從“敗麓”中揀得《水經注》,并作書后兩行題記。至己巳年(1929)六月,即抵南京次年,先生回憶批讀往事,又作書前六行題記以存紀念。先生讀書頗重史部,以《史記》、《漢書》、《通鑒》為甚,嘗言:
班《書》為傳記之正宗,《通鑒》為編年之極則。讀史不先從此事于此,無當也。太史公自屬奇作,視班尤高。[1]65
與題記合觀,可知在先生看來,《水經注》作為中國地理學的扛鼎之作,正為讀史之良佐,故重視此書淵源有自,因而有悉心批閱之事。
關于黃晟刊本所用底本,黃跋并未明言,只提及于《水經注》有功者數人,*跋中提及北魏酈道元、金蔡正甫和明朱謀瑋三人。但“嗣后朱謀瑋附增注箋,蔡正甫又作補正”之語,將蔡、朱二人時代先后順序顛倒,可見黃曉峰于酈學并非內行。便“爰取舊本,重為校勘”。[4]依先生題記所言,“頗存朱《箋》而文又削剔之,又不標朱說,似欲竊為己有”,可知先生認為底本當為朱謀瑋《水經注箋》。且據先生批點校勘結果來看,黃刊本確有不少內容直襲《水經注箋》,尤其是對后者訛誤承襲,其中不少迥異于他本,更是明證。據黃跋所言,此本刊于清乾隆十八年,即公元1753年,全祖望、戴震和趙一清三種校本均未付梓,因無所憑依,故校勘質量有限,尤其是經注相亂情況尚未厘清。*如卷二《河水》“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混入經文。全祖望于乾隆九年(1749)至乾隆十五年(1755)七次校勘《水經注》,直至光緒十四年(1888)才刊行;戴震校《水經注》由武英殿刊行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趙一清《水經注釋》多認為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畢沅刊于開封,縱使如范希曾《疏補答問補正》卷二所言“《水經注釋》四十卷,《刊誤》二十卷,趙一清,原刻本,乾隆十九年趙氏家刻”,亦在黃刊本之前。故上述諸本黃氏均無法親睹。
二、汪批本《水經注》特色
《水經注》向來號稱難懂難讀:一方面由于其中涉及眾多州郡城邑、河道水系之名,且古今地理沿革和地名變換導致的混亂關系難以縷清;另一方面則由于《水經注》自宋以來便殘缺不全,加之經注混淆,錯訛滿書。鑒于此,先生批點側重名物訓詁、駁誤質疑,尤其是在古今地名對照和古地名注釋方面甚見功力。概括而言,汪氏批點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古今地名對舉。如卷二《河水》“右會大夏川水”一句,眉批:“大夏,今河州。”卷十五《瀍水》“瀍水出河南谷城縣北山”一句,夾批:“谷城,即今河南府新安。”卷三十二《江水》“新汲”一地,眉批:“今洧州。”

第三,指出古跡位置。如卷三《河水》“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一句,眉批:“碑在山陰縣。” 卷六《汾水》“汾水西徑虒祁宮”一句,眉批:“虒祁宮在曲沃。”卷三十三《陰溝水》“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墟荒,今屬苦”一句,眉批:“《地理志》云:‘有賴鄉祠在苦縣城東,老子所生地。’”

第五,注釋人名。如卷一《河水》“漢大司馬張仲”一句,眉批:“張仲當是張戎。”
第六,揭示用典。如卷一《河水》“盤石之隥”一句,眉批:“‘盤石之隥’一段是采《漢書》杜欽語。” 卷九《淇水》“東北徑枉人山”一句,眉批:“《哀江南賦》山名‘枉人’,當本此。” 卷二十六《淄水》“齊所以為齊者,以天齊淵名也”一句,眉批:“《漢書·郊祀志》亦云:‘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
第七,補充評述。卷十五“司馬遷謂之人魚”一句,眉批:“《史記注》:‘人魚似人形,長尺余,出東海中。’今臺州有之,則不獨在伊水也。況既有四足,則不似人形矣。此謂其聲似人,彼謂其形似人,未審孰是。” 卷十九《渭水》“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一句,眉批:“戾太子之敗也,從覆盎門出亡。” 卷二十六《淄水》“《列仙傳》: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小吏,才巧,舉手成器”一句,眉批:“鹿皮公舉手成器,班孟潑墨成字,神仙多才如是。” 卷二十九《湍水》“(張敏)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傷。自后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一段,眉批:“為此碑者大愚,后人不發此墓亦愚,世人皆愚人之所愚也。”
第八,駁誤質疑。汪氏態度審慎,于有疑處仔細推敲,不知處則闕疑待考。如卷九《清水》“太公望君,河內汲人也”一句,眉批:“《史記》:‘太公望者東海上人也。’亦不應是汲人。”卷二十《丹水》“漢祖入關,亦言下淅、酈”一句,眉批:“析、酈兩縣,考之諸書,則在今南陽、河南兩府界。師古云‘析縣,今內鄉’,則今內鄉即析縣也。然《圖經》云‘盧氏在析縣職之北鄉’,則今析川乃是析縣。若是,則析縣又屬內鄉,又系析川,既為可疑,而酈縣注云‘即菊潭縣也’又在何處耶?當再考之。酈當時內鄉,析當時淅川,恐師古所謂內鄉非今內鄉耳。”卷二十一《汝水》“水出南陽雉山,亦云導源雉衡山”一句,眉批:“雉衡山在南陽府城,若云高文通乃葉縣人,此山當在葉縣耶?”卷二十三《獲水》“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一句,眉批:“然則今之姓盛者皆奭氏之后耶?”卷二十七《沔水》“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句,眉批:“武都沮縣,當在今鞏昌兩當縣界,河池今徽州也。一說沮縣即今漢中寧羌略陽,非兩當也,兩當自屬武都耳。”
第九,文字賞析。文學賞析并非重點,但先生精煉的評價卻有畫龍點睛之感。如卷六《澮水》:“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一句,眉批:“古詩煉句。” 卷二十《丹水》“丹水東南流,至其縣南,黃水出北予山”一句,眉批:“丹、黃水其名故佳,又加以墨山赪壁,天然圖畫,不假繪設矣。” 卷二十二《洧水》“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一句,眉批:“乘、空兩字,妙極形容。”
尤其值得引起關注的是對《水經注》文字校勘的批注,其反映了汪氏早年在古籍校勘方面的理論與實踐,約可分作三類。
第一,存異文。如卷三《河水》“至是乃為河之巨險”一句,夾批:“一本無‘河之’二字” 今案:各本均有“河之”二字,明朱謀瑋《水經注箋》無,[5]卷三陳橋驛先生《水經注校正》有“河之”二字。同卷《河水》“圁水出西,東入河”一句,“東”字旁夾批:“一作‘南’。”今案:戴震校殿本《水經注》作“東”,并有校語:“案:‘東’近刻作‘南’,蓋后人所妄改。”[6]卷三《水經注箋》《水經注釋》均作“東”,《水經注校正》同。
第二,補脫文。如卷十九《渭水》“駕白鹿見漢武皇帝,將臣之”一句,夾批于“將”字前補一“帝”字。今案:諸本均有“帝”字,《水經注校正》同。卷二十《漾水》“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山”一句,于句前補一“丹”字。今案:各本均有“丹”字,《水經注校正》同。
第三,正訛文。如卷一《河水》“東上岸尼拘律樹下作修”一句,眉批:“‘尼衢律’即是上‘尼拘律’。”今案:《水經注箋》《水經注集釋訂訛》均作“衢”,《水經注釋》、殿本《水經》作“拘”,《水經注校正》作“拘”,衢與拘音近而訛。又如卷十六《谷水》“世祖嘗宴于此臺,得走鼠于臺上”一句,眉批:“‘走’字當是‘廷’字之誤。”今案:《水經注釋》作“廷鼠”,“走”“廷”形近易混。殿本作“鼮鼠”,《爾雅》唯有“鼮鼠”而無“走鼠”“廷鼠”,《水經注校正》正作“鼮鼠”。又如卷二十六“東北流山”一句,“山”字旁批:“當是‘由’字。”今案:此句下原有注文“‘山’字疑衍,或有脫誤”八字,先生并未迷信盲從。殿本《水經注》《水經注釋》均作“由”,《水經注校正》同。
先生亦難免有誤校之處,如刪衍文,卷一《河水》“于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一句,夾批:“‘于’字疑衍。”今案:《水經注箋》此句下有注文“‘于’字疑衍”四字,[5]卷一殿本《水經注》、沈炳巽《水經注集釋訂訛》《水經注釋》均有“于”字,《水經注校正》同。*此例先生誤校,但仍可作為先生參考《水經注釋》之證據。
此外,汪氏已注意使用理校之法,所據者多系全書文意與體例,但在沒有版本依據的情況下,常只作初步判斷。可見先生之態度嚴謹,校改十分慎重,這與古籍校勘中強調的“慎改”原則若合符契。如卷二十四《汶水》“汶水又西徑汶陽縣城北而注”一句,眉批:“疑有訛字。”今案:《水經注釋》作“汶水又西徑汶陽縣城北而西注”,[7]卷二十四殿本《水經注》同,句下并有“案:近刻脫‘西’字。”《水經注校正》同。此可為先生未見《水經注釋》與殿本《水經注》之證據。又如卷九《清水》“謂之清河,即淇河口也”一句,眉批:“有訛字。”今案:《水經注箋》同,殿本《水經注》作“謂之清口”,并有校語“案:近刻訛作‘河’字”。《水經注釋》作“謂之清口”,《水經注校正》同。此外,還將一些詞語抄于天頭以引起重視,如卷一之《河水》“鹿野苑”,卷二《河水》之“津逮”、卷十一《滱水》之“八渡馬溺”、卷二十六《淄水》的“時水”等。
事實上,汪氏對于《水經注》的研究有著系統規劃,早年批閱與日后研究工作關系密切。汪氏從胡適回復的信函中得知《水經注》的版本信息后,*先生曾在1946年冬天致信胡適,論及《水經注》,胡適的復函中提及其本人在海外所見二十余種版本以及國內存珍貴版本八種。以上均見《〈水經注〉的版本和整理工作》,收入汪辟疆著,程千帆編《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認為相關整理工作當分兩步進行。關于校勘工作:
我們正好利用這些珍秘的材料,再來一次縝密校勘的工作,并且應用科學的方法,以期尋根徹底,探求前人所以偽誤的根源,庶幾使這一部奇書,神明煥然,了無疑滯,替千百年后的學者辟一坦途。[1]121-122
關于進一步的工作整理:
在戴、楊、熊三家既已發起端緒,我們又在科學進步的時代,正好利用地理學、地質學、考古學和測量新技術,以證實一千四百二十二年以前酈氏當日水道的實況。[1]122
且在抗戰期間,就有實現這一龐大計劃的初步設想:
此外在重慶時,曾取早年手校《水經注》,重加校正,擬撰輯《水經注集解》一書。又以楊疏多乖誤,并擬撰《水經注楊疏訂訛》。當時以生活未能安定,迄未寫定。[3]690
1943~1944及1947~1948年,汪氏亦在中央大學教授《水經注》課程,[3]689欲繼續酈學研究,惜先生宏愿終未實現,誠為憾事。
三、結 語
《水經注》在宋代已有殘缺。*《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為四十卷,尚為全本。北宋仁宗年間成書的《崇文總目》著錄三十五卷,較之原本,已殘五卷。然《崇文總目》成書稍早于《新唐書·藝文志》,故后者著錄當沿襲《舊唐書·經籍志》,非有完本重現。宋代以降,雕版大興,北宋前期有崇文館閣本(即《崇文總目》著錄本)三十五卷,已缺五卷;北宋后期有成都府學宮刊三十卷本,再缺五卷;哲宗元佑二年(1087)刊四十卷本,割裂舊文,雖稱足卷,但非原貌。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地理類”但著“水經”二字,不得其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并無《水經》或其注之記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八著錄。可見,全文共計三十余萬字的《水經注》無論在抄本時代還是在雕版印刷初期,其保存難度可想而知,殘損錯亂在所難免。以上參考汪辟疆《分析〈水經〉和〈水經注〉作者的分歧問題》(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水經注疏》代序,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徐中原《〈水經注〉研究》(民族出版社,2012年)。及至明代,刊本漸多,原本殘缺不全、書簡散脫的現象才慢慢得到改觀,這種改觀得力于眾前輩學者接連不斷、日益深入的研究。在歷代學者的研究歷程中逐漸產生了考證、詞章、地理三派。*三派之分采陳橋驛說,參見陳橋驛《論酈學研究及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水經注論叢》。注重校勘考據、糾謬補缺的考證學派,以朱謀瑋、全祖望、趙一清、戴震、孫星衍、王先謙、王國維等人為代表,旨在廣搜散籍,恢復原貌原樣;側重文學欣賞的詞章學派,代表學者如朱之臣、鐘惺、譚元春等,旨在發掘書中的文學意蘊,從而達到修身養性的目的;至于黃宗羲、顧祖禹、胡渭、閻若璩、楊守敬、熊會貞等講求經世致用的地理學派,*在陳橋驛《酈學概論》(《水經注論叢》,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中,將疏解《水經注》者如楊守敬、熊會貞等人與在研究地理時利用《水經注》內容者如黃宗羲、顧祖禹、胡渭、閻若璩等人歸為同類,統名曰“地理學派”。此種分類實可商榷。因做疏解者必定涉及地理學研究,故二者共通性自無可置疑;但研究目的及出發點卻大相徑庭,可謂區別明顯。然此種分法以人系學,非以書判學,亦有其合理之處,故仍采舊說,備考。則與后世歷史地理學頗有共通之處。汪辟疆于以上三派之間逢源其中,左右采獲,兼收各長。批文以《水經注》地名注釋為核心,將《水經注》相關版本對讀比勘,參考前四史,又對照圖經,主訓詁為而兼及校勘,在兩個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南大文學院此批本不僅展現了汪先生早年即已具備相當深厚的學術功底,其批閱方法更是對后世有相當的啟發意義。汪氏在文學史、文獻學史上貢獻非凡,此本的發現不但有助于研究《水經注》民國時期批本的情況及其演進過程,亦有利于對汪氏學術思想發展及學術成就的探索。限于學識,本文僅對此本作一初步發覆探索,祈請學界進一步探索與研究。
(感謝業師武秀成教授、文學院圖書館黃靜館長以及師兄李軼倫的幫助。)
[1]汪辟疆,著,程千帆,編.汪辟疆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陳橋驛.水經注論叢[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
[3]張亞權.汪辟疆學術簡表[M]∥汪辟疆詩學論集.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4]酈道元.水經注·卷首序[M]. 清乾隆黃曉峰刊本.
[5]酈道元,撰.朱謀瑋,箋. 水經注箋[M].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李長庚刊本.
[6]酈道元,撰.戴震,校.水經注[M].清乾隆武英殿刊本。
[7]酈道元,撰.趙一清,校. 水經注[M].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責任編輯卓禎雨]
Shui Jing Zhu Annotated By WANG Pijiang
SUN Jing, WANG Y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China)
WANG Pijiang, a well-known scholar,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Shui Jing Zhu for a long time. There are ten volumes of Shui Jing Zhu at the Liberal Arts School Library, Nanjing University, which were annotated by Wang. These ten volumes are highly valuable because a lot of his comments were kept in these books.
WANG Pijiang;ShuiJingZhu; annotation
2016- 01- 14
陜西省十二五規劃重大古籍整理項目(SG13001)
孫靖,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從事文獻學、學術史研究。
K204
A
1671-394X(2016)09- 0085-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