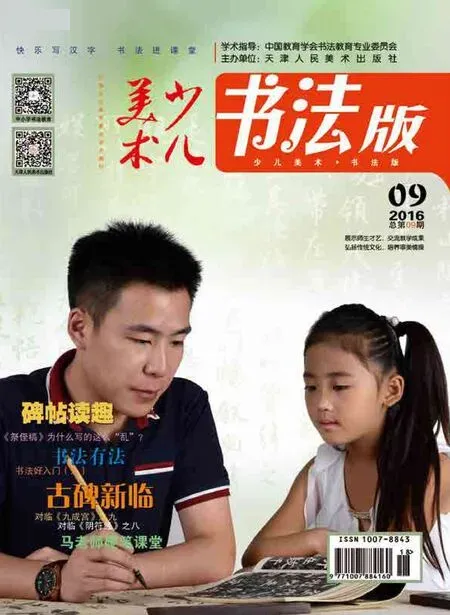龐說篆刻(八)文化的篆刻 多能的印人
龐說篆刻(八)文化的篆刻 多能的印人

在藝術的百花園中,篆刻雖然只是個小門類,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篆刻的形制不大,涵蓋的學科卻很多。對初學者來說,在短時間內掌握一定的刻制技法或許不難,熟能生巧;但要提高自己的藝術水平并達到一定的高度,則絕非易事。篆刻創作需要熟悉文字演變,需要掌握印章源流,需要體悟繪畫書法,需要感受工具材料,需要關注觀念更新,需要理性升華審美,需要哲思浸潤心境……這些都不是朝夕之事,而需長期修為。
篆刻藝術在方寸天地所呈現出的萬千氣象,讓人沉醉執迷;但或許也正是她的這種深刻與豐富,她的小而不簡,讓人望而卻步,從而影響了她的受眾與普及。與她的姊妹藝術國畫和書法相比,篆刻沒有繪畫的直觀,更沒有書法那樣的群眾基礎,人人都可提筆寫字。“謝家最小偏憐女”,篆刻愛好者人口之少實在難以與書畫所擁有的眾多愛好者相提并論,這是她的劣勢。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篆刻屬性的過于專業固然有她曲高和寡的一面,其實也在成就著篆刻者的綜合素質。
中國文人藝術向有詩、書、畫、印“四全”的主張,這一傳統在現代社會的大背景中已逐漸消解。繪畫者不會題款、書法者不懂刊印、書畫者不能作詩文的現象比比皆是。但與篆刻相關的這些社會群體卻仍對篆刻作者有著近乎一致的“全能”苛求,文字學家可以以不合《說文》來指責篆刻印作中的用字篆法乖謬,從不操刀治印的書法者也要居高臨下地對印人頤指氣使,用一些所謂“善印者必善書”“七分篆三分刻”之類的古訓來顯示書法的高貴,畫價動輒數萬的畫家只將篆刻印章作為畫中可有可無的點綴……歷史的傳統和現實的尷尬同時在“逼迫”著印人做出自己的選擇,要么做全才,要么放棄。
面對這樣的窘境,執著的追求者當然不會放棄,必然是全面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文人篆刻從興起的那天起,就在確立著自己的文化品位。從古代印工質樸自然的創造,到文人書齋中的優雅休閑,再到現代社會藝術家張揚個性、釋放情感,篆刻印章的社會功用經歷了實用——雅玩兼實用的文人篆刻——現代藝術的轉型,篆刻藝術的創作理念和審美觀也在隨社會的發展不斷嬗變,也正是在這樣的演進中,篆刻的獨立品格不斷得以強化,印人的自主精神不斷得以升華。
說吳昌碩、齊白石是“詩書畫印”全能的藝術巨匠,似仍只是以藝術的角度在觀察,實際上,吳昌碩的海派宗師形象,齊白石的婦孺皆知,其中所隱含的細微社會文化心理都可深入挖掘。印史上的許多重要人物,我們都不可能忽略其所擔負的社會文化角色。西泠印社成立一百多年,卻先后有五十多年的時間空缺社長一職,更多的在于它的文化高標定位。出任西泠社長一職,必須三者兼備:1.藝術大師,書畫印俱佳;2.學術泰斗,有理論著述;3.文化名人,須要有社會影響力。三者缺一不可。這是一種文化精神的守望,也是印人文化操守的堅持。
龐涌湃,別署尋齋,1970年生,河北衡水人。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河北省書協篆刻委員會副主任、篆書委員會委員,滄海印社理事,雙棲印社社員,中國篆刻網藝術論壇休閑區總版主、駐京特約記者。
張福義,號子宜,祖籍山東,1956年生于天津。當代書法家、篆刻家。自幼喜書畫篆刻,青年時代拜著名書法家龔望先生為師,并問藝于孫其峰、余明善諸先生。楷書初習唐碑,后及魏隋,尤傾心于漢隸,對曹全、禮器、張遷、衡方、石門頌等碑用功尤長。書法氣象雄渾、飄宕遒麗,重情致,棄乖僻,力求高古,不慕時尚。印宗秦漢,對明清諸家均有問從。刀法師黃牧甫,追求簡潔明快之印風,多字小印尤見功力。藝事遵“士先器識,而后文藝”。將藝術的表現,理解為人的性情與品格的再現。作品多次入選國內外重大展覽,被多家博物館收藏。



▲ 永壽嘉福

▲ 有漢都尉之裔

▲ 花長好月長圓人長壽

▲ 名是無窮壽

▲ 真如貝葉(附邊款)

▲ 見賢思齊(附邊款)

▲ 無量壽(附邊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