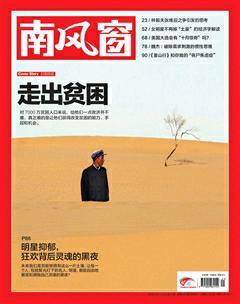“一線城市永遠漲”可能只是個神話
譚保羅
“一線樓市永遠漲”,這可能只是一個神話,但卻越來越被人們所相信。這讓我想到一個故事。
幾年前,我曾經接到過記者生涯里最匪夷所思的一條新聞線索,這件事就發生在某一線城市的郊區。一位三四十歲的男子A先生向我控訴,他被人用鋼管活生生地砸斷了幾根肋骨,痛不欲生。而且,他覺得還很恥辱。我說:你應該找警察、看醫生,而不是找記者。
和他溝通的過程中,我發現他一直在“選擇性”地描述事情的經過。之外,還有很多“隱情”。最后,在我的追問下,他終于把事情和盤托出。
事情很簡單,“被砸斷肋骨”的起因是5塊錢的公交車票價。原來,這一天是周末,這座城市郊區的一條公交車線路的票價漲了5塊錢。這條線貫穿這座“一線城市”的一處城鄉結合部,乘坐者多為農民工或者收入并不高的“白領”。
這些結合部的公交車,很多都是私人承包,“夫妻店”特別多,即丈夫開車,妻子是售票員,小舅子做跟車保安或者“押運員”。監管混亂,車輛衛生一般,票價也不固定,周末和節假日漲價是常態。
但A先生卻不以為然,在公交車上,他開始與女售票員理論,你為什么要漲價5塊錢。他的鬧騰,導致整車乘客都情緒高漲,紛紛要司機退費。后來,A先生和售票員對抗得越來越厲害。我不確定他們是否動了手。
除了售票員和司機,這輛車還有一位“押運員”。在這些城鄉結合部,公交車也會考慮自己的安全問題,因此經常會找一些同鄉中的青壯年擔任這個崗位。根據A的描述,這個“押運員”牛高馬大,從駕駛臺抽出一根鋼管,徑直朝A先生砸來。
第一下沒砸到,雙方于是開始扭打。A先生認為自己根本就打不過別人,而對方看起來已經發了狂,似乎一定要砸破他的腦袋。于是,A先生從窗戶跳了出去,而這時的公交車正在高速行駛。A先生不是詹姆斯·邦德,也不是杰森·伯恩,他從公路邊爬起來之后,感覺肋骨一陣劇痛。
這個讓人吃驚的故事,A先生就是這么給我講的。他之所以要找媒體,是希望媒體能報道,讓這個司機和押運員丟掉線路承包權。我把這個線索轉給了突發新聞部的同事,但他們認為無法核實事情真偽,所以沒有興趣,報道也就不了了之。
不久前,我到事發地的城鄉結合部走了一圈,想到了這個幾年前的爆料線索。現在,這里的公交車和以前差不多,地鐵沒有通,環境也不怎么樣。企業群體依然是工廠、作坊和昏昏欲睡的路邊攤,沒有什么高科技轉移到這里。“城市的又一個次中心”,只是一種宣傳。
而且,這一帶的醫院很多依然是民辦醫院。從那些充滿救死扶傷味道以及代表高貴品德的醫院名字來看,莆田系的可能性極大。
幾年了,這里公共設施依然糟糕,什么都沒有變。唯一變的是房價,以前不到1萬元,現在最貴的賣到了5萬元。到處都是新樓盤,供應充足。售樓的小伙子、小姑娘在路邊發著三四萬一平的物業銷售傳單,與這里的環境顯得不匹配。
在一個正常的市場,高房價的本質是高標準公共服務的可得性,市中心的房子貴,不是因為房子漂亮,而是它代表著好的學校、好的醫院、較低的通勤成本以及高密度精英人群的可接觸性。
但在所謂一線城市的很多地方比如郊區,高房價真的有點很莫名其妙,這里既沒有名校,也沒有好的醫院和好的交通。生活在這里,你的孩子未必有上學指標,醫保也無法統籌使用,換句話說,你根本體會不到是一線城市,相反會感到一種被一線城市的排斥感。但問題在于,這里的房價就是一個字—“高”!
不過,支撐這種“高”的東西,除了“一線城市永遠漲”的神話,可能再也沒有別的了。實際上,伴隨著高房價的脫韁之勢,一線城市所謂的就業優勢也在被慢慢瓦解。房租和薪水,兩者正在反向變動,這難道不是一個注腳?
A先生講述的這個一線城市的“故事”,讓我想到了這么多。
伴隨著高房價的脫韁之勢,一線城市所謂的就業優勢也在被慢慢瓦解。房租和薪水,兩者正在反向變動,這難道不是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