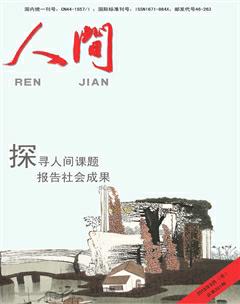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有效性及方式
肖寧卉
摘要:本文將圍繞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有效性進行討論,對保險金與遺產進行區分,并且對保險受益人如何進行更改以及生效要件進行探討,從而對我國保險法以及繼承法的連接與過渡提出筆者的建議。
關鍵詞:遺囑;保險受益人;變更權;通知
中圖分類號:DF438.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9-0075-02
一、保險金與遺產的區分——保險金請求權的獨特性
甲向某保險公司投保了一份以自己為被保險人的人身保險合同。考慮長子乙生活困難,指定其為身故受益人。之后,甲生病住院,次子甲從未進行探望,而次子丙日夜守護。甲臨終前,通過親友代書遺囑,在沒有通知保險人的情況下,遺囑中進行了保險金的受益人修改。甲去世后,兩個兒子就保險金的歸屬產生了爭議。[1]通說認為,通過遺囑不能對保險金進行處分,那么,在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行為,其是對保險金的處分?還是對遺產的處分?
在此,筆者需要考察一下保險金與遺產的區別。從財產的歸屬上來說,保險金并不是被保險人實際擁有的財產,而是以被保險人身故為條件的附期限的權利。即使被保險人死亡后,保險金也并不當然屬于被保險人,比如保險法中規定的“自殺條款”等,皆嚴格約束了保險金的歸屬問題,可以這么說,其歸屬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作為取得保險金的權利人,受益人一旦指定,其變動需要經過特定的程序,所以受益人是相對穩定且現實中不常發生變動的。[2]而對于遺產,屬于公民的合法財產,其不需要該公民進行身前的積極行為,如若其自殺或不在承保范圍內的死亡,其繼承人依舊可以合法繼承其財產。再者,遺產繼承人的變動比之保險金更為隨意,如遺贈撫養協議、遺囑、特留份額都會對繼承人的范圍進行一定的變動。相比來說,遺產的繼承上,被繼承人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而對于保險金的請求,通過合同以及一定行為進行變更,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途徑唯一性。從制度上來說,保險金是無須償還債務的,是被保險人通過參加含有希望因素的人身保險合同來轉移因其死亡所產生的經濟風險。[3]同時,死亡保險金在納稅程度上也比遺產少的多,各國通常會給于人身保險稅收優惠。[4]
綜上所述,遺產與保險金屬于兩個制度領域內的財產,對于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處分客體進行討論時,筆者認為需要明確處分的客體,即使存在《保險法》第四十二條規定的未指定受益人按遺產處理時,遺囑指定受益人的客體也應是保險金而不是遺產。針對保險金與遺產在理論上的混亂狀況,以及將保險金轉入遺產后可能產生的問題,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就是對現有法條作出簡單修改,不能將保險金列為遺產而改變保險金性質,僅借用《繼承法》對遺產的處理方式處置保險金。結合各位學者的建議,筆者認為此種立法方式是比較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即將《保險法》第四十二條中,“被保險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險金作為被保險人的遺產,由保險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規定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修改為“被保險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保險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規定,向被保險人的繼承人履行給付保險金的義務。”[5]從而,明確通過保險金不能納入遺產并與之區分的立法態度。
那么,問題就回歸到遺囑處分保險金是否可行?亦或是保險法中改變受益人的方式,遺囑指定是否是一種改變方式?
二、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有效性——處分保險金是否可行?
關于遺囑是否可以處分保險金,學界主要分為兩種觀點。支持派認為人身保險的受益人可以通過遺囑進行指定[6],此觀點的理由主要基于被保險人的私法自治原則,以被保險人的利益最大化考量為標準,通過遺囑修改并沒有改變這一宗旨,只需在變更方式上加以嚴格約束即可。
反對派則認為遺囑不能對保險受益人進行指定,其原因在于主要基于以下幾點[7]:其一,保險金與遺產有截然不同的區別,其規制在不同的法律領域,不能進行混同。且被保險人的保險金使得受益人處于一種期待的地位,其本身并不擁有保險金的所有權,根據《保險法》,受益人享有保險金請求權,被保險人在投保人身保險時,特別是以死亡而給付保險金時,顯然保險金不是留給自己的。無論身前還是死后,被保險人無法享受領取保險金的權利,也不可能占有保險金。其二,在原因1的基礎上,即使被保險人與受益人相同的情況下,他們擁有的也不是所有權,而是一種請求權。值得一提的是,反對派唐瑋學者提出了區分原則,即對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需要看是否有人繼承的標準。唐瑋學者認為在投保單上未指定受益人的情況下,可以通過遺囑進行指定,其依據是保險法四十二條沒有受益人的情況下,遺囑繼承優于法定繼承的規則。但如果投保單上有既定的受益人,則被保險人不可通過遺囑的方式進行變更。
綜上所述,筆者比較贊同可以通過遺囑指定受益人的立法方式。首先,筆者認為這是被保險人通過遺囑變更受益人的方式可以充分體現被保險人的真實意愿,充分尊重了被保險人的意思自治。反對派學者認為保險金與遺產不能混為一談作為反駁,筆者不以為然,反對觀點在于把處分行為的客體僅僅限定在財產權利之中,與此同時,卻忽視了權利處分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其就是通過遺囑改變受益人,是對保險金的處分。只是通知的方式不同于保險合同受益人的直接修改,而是通過遺囑的方式。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此種方式、如何通知的內容、形式作一定的限制,而不是否定其大前提。其次,通過遺囑改變受益人也許是被保險人“危急”的保全做法,如案例中談到的,多數通過遺囑改變受益人情境下,都可能是被保險人已患重病,保險條件可能達到的情況下。在這種情境下,需要被保險人去保險公司進行受益人變更,根據保險公司的要求履行一定的程序和調查義務,未免太過苛責。很多人會選擇一個較簡單的方式,比如說遺囑(這畢竟是一個成本小、成效快的方式)來改變受益人,這符合對被保險人的利益的保護,也會使得讓保險金的歸屬更加明確。最后,從我國立法上來看,并沒有任何法律明文禁止不能通過遺囑進行受益人變更,《保險法》第四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可知保險法只對變更的形式需要“書面”通知即可,并沒有否定其效力。“法無明文禁止則可為”在該原則的推導下,應當承認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有效性。
那么,如何看待變更受益人這一法律行為,其屬于單方行為?還是需要通知或者必須通知保險人的雙方行為?通過遺囑進行變更的通知方式應為如何?需要公證遺囑嗎?
三、指定保險受益人的通知方式再商討——可以遺囑指定通知?
根據我國現行《保險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變更受益人應以書面形式通知保險人, 保險人應在保險單上批注。”但是,該條并未詳示書面通知的具體內容、法律效力以及保險人在保險單上批注行為的法律效力。筆者認為,要式行為應該只局限在通知保險人這一范疇上,后續可由保險公司進行批注。因通知與批注存在一定的時間,對保險人生效這一條件的達成只需通知即可。具體到遺囑中如何通知,筆者認為被保險人遺囑更改后應該立即對保險人進行通知,此通知可以是書面文件附上遺囑,讓保險公司最及時知道受益人的變更情況,以免錯誤的給付,而批注的時間法律也應該有一定的規定,不能使得保險人接到通知后不進行批注,怠于行使自己的權利而產生錯誤給付的抗辯理由。
綜上,變更受益人之行為屬于單方要式行為,只要被保險人作出變更受益人的意思表示,該變更行為就發生效力,不以書面通知和保單批注作為生效8條件。
不支持遺囑中指定保險受益人的學者正是混淆了受益人變更行為的法律性質,視書面通知和保單批注為必經環節,因而否定了遺囑變更受益人的適用性,這種錯誤的理解是不正確的。應該認為遺囑中可以指定保險受益人,一經指定即生效,但是需要作出一定的行為,即通知保險公司,應立即(在能力范圍之內)以遺囑加書面文件的形式通知保險人并進行批注,遺囑是否為公證遺囑在所不論。此行為的目的在于盡早讓保險人知道其給付的對象發生變化,以免發生錯誤的給付。當然,筆者認為在被保險人身故時,保險人有義務去對受益人的情況再進行核實,此處指的是形式核實而不是嚴格的審查。筆者建議應在人身保險合同中設立一個保險金給付等待期,其一在于讓真正受益人可以向保險人主張保險金請求權,其二在于保險人在未完成批注情況下也有足夠的時間去鑒別誰是真正合法有效的受益人。也就是說,賦予保險金等待期除斥期間的意義,即若真正受益人未在保險金等待期內對保險人進行主張,而保險人根據原有的保險合同進行給付時,真正受益人不能要求返還;同樣,若在保證金等待期內,真正受益人無論保險人是否錯誤給付,都可以向保險人行使自己的保險金請求權,此期間的設定可以促使相關權利人盡早行使自己的權利,使保險金的處于一個明確的歸屬狀態。
參考文獻:
[1]參考李春雨:我國保險法上受益人變更權研究,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5月。
[2]周馨路:保險金作為遺產的法律問題研究——由《保險法》第42條引發的思考,華東政法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4月。
[3]參見張慶俠:《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時死亡之保險金給付的多維思考》,載《企業經濟》2007 年第 8 期(總第 324 期)。
[4]引自湯曉梅:《我國人壽保險稅收制度法律問題探討》,西南政法大學 2008 年碩士學位論文,第 33 頁。
[5]參見張慶俠:《被保險人與受益人同時死亡之保險金給付的多維思考》,載《企業經濟》2007 年第 8 期(總第 324 期)。
[6]參考熊海帆:人身保險的受益人可以遺囑指定,保險研究爭鳴,2001年第8期;
李春雨:我國保險法上受益人變更權研究,吉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5月。
[7]參考陳會平:論遺囑變更受益人的法律效力,上海保險,2003年第8期;
唐瑋:受益人不能在遺囑中指定,保險研究法律,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