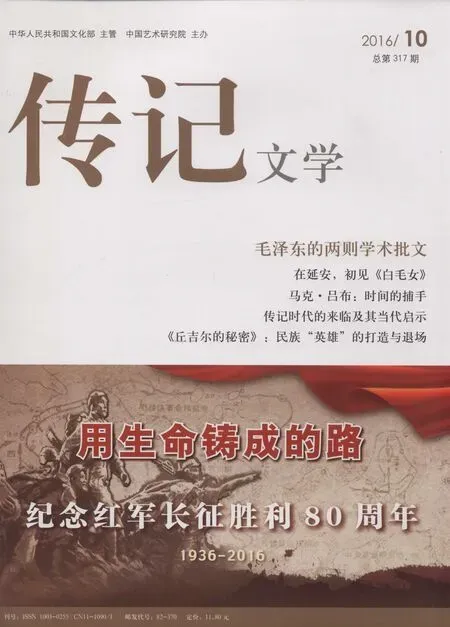崔維峻和關系紅軍命運的密電碼
文|田潤民
崔維峻和關系紅軍命運的密電碼
文|田潤民

上圖:四渡赤水雕塑(局部)
長征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由紅一方面軍組成的中央紅軍1934年10月從江西出發,歷經千難萬險,頭上有飛機轟炸,地上有圍追堵截的幾十萬敵軍,歷時整整一年,跨過11個省,于1935年10月到達陜北。
二萬五千里長征,誕生了多少將帥!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中,原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占絕大多數。十大元帥中,唯有陳毅留在南方堅持三年游擊戰而沒有參加長征,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其余7位元帥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均來自紅一方面軍。文化大革命中,八大軍區司令中5位來自紅四方面軍:陳錫聯、許世友、韓先初、陳再道、鄭維山。“九一三”事件后,一度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來擔任北京軍區和沈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也是紅四方面軍的。
因此,就產生了這樣一個說法:“一方面軍帥多,四方面軍將多。”
密電碼大顯神威,中央紅軍闖關奪隘
假如沒有楊虎城向紅軍提供的密電碼,長征中的紅一方面軍能否擺脫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紅四方面軍能否在川北站住腳,是個大大的問號。那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歷史就得重寫了。
眾所周知,紅軍長征中的赤水河、瀘定橋、烏江、臘子口是擺在中央紅軍面前的天險,不是滔滔江水,就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隘口,能否闖過去關系到紅軍的生死存亡。在這幾處關口上,有國民黨軍重兵把守,甚至蔣介石親自督戰,而紅軍竟然一次又一次地闖關奪隘,化險為夷,簡直像神話中的天兵天將一樣。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曾把這些勝利完全歸結于紅軍領導人個人的智慧,甚至用“神機妙算”這類帶有迷信色彩的語言加以渲染和夸大。其實,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紅軍領導人并沒有“神機妙算”的特異功能,他們是靠軍事情報作出正確的決策,其依據主要來自截獲和破譯敵軍的空中情報。而中央紅軍的空中情報則來自紅四方面軍的電臺。
對此,原紅四方面軍政治委員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1934年12月間開始的。”“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云南方面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臺沒有時間做偵察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形,決定行動,發布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等于為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紅四方面軍電訊局局長兼電臺臺長的宋侃夫及其部下肖全夫、陳福初、游正剛等當事人的回憶,印證了張國燾的說法。
而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對紅四方面軍電訊工作的高度評價也從側面證實了張國燾這段話。
據宋侃夫回憶,長征結束后,朱德總司令曾對紅四方面軍的電訊人員們說:“我們一方面軍離開中央蘇區,進入湘、滇、黔、川地區,以及四渡赤水時,對周圍敵情搞不清楚,是你們四方面軍電臺的同志們,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經常在深夜,把破譯敵人電報的情況,整理出來電告我們,這深刻體現了一、四方面軍之間的戰斗情誼,天下紅軍是一家嘛!”
1938年,毛主席在延安也對宋侃夫說:“你們四方面軍的技術偵察工作做得很好嘛,特別是我們長征到貴州,四渡赤水時,天天行軍很緊張,你們提供了許多重要情報,對我們幫助很大,要感謝你們呀!”
在這里,毛主席和朱總司令不約而同地強調紅四方面軍電報對中央紅軍長征中四渡赤水戰斗所起的作用,這和張國燾所說的“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云南方面行進時)”完全相符。四渡赤水,發生在1935年1月19日至4月7日,期間,蔣介石坐鎮貴陽,親自指揮他的嫡系中央軍和四川、貴州、云南三省的軍閥對中央紅軍進行前堵后追,企圖把紅軍消滅在川、黔、滇三省交界地帶。中央紅軍根據紅四方面軍所提供的空中情報,在敵軍的包圍圈中來回穿梭,避實就虛,忽東忽西,忽北忽南,不僅擺脫了圍追堵截,還找到敵軍薄弱環節予以狠狠打擊。1960年5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對毛主席在解放戰爭中所指揮的三大戰役倍加贊賞。在這位英國元帥看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殲滅了國民黨軍150多萬,是世界軍事史上的經典戰例,也應該是毛澤東個人軍事生涯中的亮點。孰料,毛主席聽后卻不以為然,他告訴蒙哥馬利,長征中的四渡赤水才是他軍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筆。
四渡赤水,紅四方面軍電臺所提供的空中情報給中央紅軍充當了耳目。那么,紅四方面軍為什么能夠破譯敵軍的空中情報?那是因為他們得到了一份蔣介石部隊所用的密電碼。
“密電碼”,六十歲以上的中國人聽起來是那么耳熟。一部樣板戲《紅燈記》的劇情就是圍繞著密電碼展開的,幾乎使全國人民都知道了它的重要性。日本憲兵隊隊長鳩山為了獲取共產黨的密電碼,殺了李玉和與李奶奶,為了保護密電碼,李玉和一家三代人付出了生命代價。可見,密電碼的價值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比生命還要重要。
那么,蔣介石部隊的密電碼又怎么落到了紅軍手里?這個事關紅軍命運的機密大事,相關黨史和軍史著作在細節說法上有差異。長征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1933: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漢中密約》一書中是這樣說的:
1933年初,蔣介石命令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配合川軍夾擊剛剛進入巴山的紅四方面軍。楊虎城不愿與紅軍作戰,密派少校參謀武志平出使紅軍求和。第38軍軍部秘書主任、中共地下黨員徐夢周提醒武志平:去年鄂豫皖“剿共”,西北軍將領吉鴻昌不愿與紅軍作戰,派密使去與紅軍聯絡。結果,紅軍拒絕與吉鴻昌聯合,還把來使殺了。此事說明,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張國燾對白區地下黨和白軍將領均不信任。暗示武志平要在“取信”二字上動些腦筋。
為促使求和成功,也為紅軍作些實實在在的貢獻,武志平利用作戰參謀之便,從軍部偷出了一份密電碼,外加一份軍用地圖,悄悄地走上了出使之路。
8天之后,武志平在四川通江縣兩河口村的一座平民屋里,將孫蔚如軍長代表楊虎城給紅四方面軍領導的密信,以及所帶禮物密電碼等,獻給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
傅鐘在《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一書中對此事作了這樣的記載:“武志平帶給紅四方面軍的寶貴禮物,是川、陜、甘三省的軍用地圖和西北軍用的密碼底本及其他聯絡信號。這些與軍隊存亡、作戰勝敗攸關的機密要件,是他冒著生命危險,穿過深山密林,闖過土匪、民團的封鎖阻攔才安全帶到的。他把這些禮物交給我,我當夜派騎兵把四川地圖送給了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徐向前同志,把密碼底本和其他材料送給了川陜軍委和紅四方面軍總部。”
這本書把紅四方面軍得到蔣介石軍隊密電碼歸功于武志平一人,而且說是武志平從三十八軍軍部“偷”出來的。
機關算盡蔣中正破解難題崔維峻
而蒙定軍在《懷念崔維峻同志》一文中則另有說法:一、不是偷來的,而是送的;二、涉及這份密電碼的不只武志平一人,還有一個更重要甚至關鍵人物——崔維峻,他為此犧牲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蒙定軍1931年和崔維峻一起打入三十八軍,在該部從事地下工作整整15年,曾擔任中共三十八軍工委書記,解放后任中共甘肅省省委統戰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他是這段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

崔維峻
蒙定軍在文章中寫道:“孫蔚如還送給紅軍一本蔣軍軍部以上專用密電本。但密電本角碼是經常變換的,變換權由蔣介石侍從室掌握。為了搞清角碼變換方法,維峻同志即同譯電室人員來往、交朋友,與該室負責人吉安成為要好的朋友,終于弄清了角碼變換方法和使用時間,同時也搞到了一些絕密的軍事秘密。”(《蒙定軍傳》第163頁,未來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對這份密電碼,蒙定軍講得顯然比《1933: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漢中密約》一書更詳細、更準確:一、這是孫蔚如送給紅軍的禮物,而不是武志平個人送的,更不是偷來的;二、這是蔣介石所統帥的部隊軍部以上所用的專用密碼本,可見其價值之高;三、正因為這個密碼本密級高,蔣介石采取了經常變換角碼的特殊措施以防止被竊取,而其變換權由蔣介石侍從室直接掌控。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不懂角碼變換方法,拿到密碼本也沒有用。然而,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的秘密,只要是人制造的秘密,人就能夠破解。蔣介石自以為由他的侍從室親自掌握這本密碼本的鎖鑰,結果是聰明反被聰明誤;四、崔維峻解決了這個難題,他直接找到譯電室負責人,弄清了角碼變換方法和時間,打開了破解這份神秘密碼的鎖鑰。
這份關乎紅軍命運的密電碼本讓一個神秘人物崔維峻浮出了水面。
崔維峻,陜西省旬邑縣城人,1910年生,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5月參加了著名的旬邑暴動。暴動失敗后,參與恢復旬邑縣黨組織,并擔任中共旬邑縣特別支部書記。1931年,由中共陜西省省委負責人崔廷儒派遣,和蒙定軍一起打入孫蔚如部在平涼的隴東綏靖司令部,先在該部主辦的《隴東日報》任副刊編輯,后任三十八軍參謀處書記(文書)。根據崔廷儒的指示,崔維峻、蒙定軍等在三十八軍秘密成立了黨支部,崔維峻任黨支部書記。1933年初,崔維峻和蒙定軍隨孫蔚如部到達陜南漢中,三十八軍內的黨支部和中共陜南特委接上了關系,并接受特委領導,其主要工作是搜集軍事情報。
崔維峻不僅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還是一個多才多藝的青年才子。他喜愛書法繪畫,且造詣很高,當年,他就是憑借自己的書畫才能,得到號稱楊虎城的左膀右臂——孫蔚如將軍的賞識,在孫將軍所部主辦的《隴東日報》當上了副刊編輯。他曾給戰友蒙定軍留了一幅條幅,可惜在戰爭年代遺失了,晚年的蒙定軍每每提及,遺憾不已。他還能吹洞簫,棋藝也不錯,在三十八軍軍部被譽為“棋琴書畫全才”,常給同事作畫、寫條幅,聯絡感情,結交朋友。這些業余愛好為他在這支國民黨部隊開展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很快受到參謀處長張之因的信任。張處長讓他主管關防、印信、機要、護照、差假證明信等事務,崔維峻實際上成了三十八軍參謀處掌握實權的人物。
從崔維峻在三十八軍擔任的職務和分管的業務來看,他比武志平獲得密電碼的條件要方便得多。假如說,武志平需要去偷的話,崔維峻根本用不著,可以大大方方名正言順地去要,因為這屬于他的工作范疇。
共產黨的地下情報工作,尤其是獲取軍事情報,有一套嚴密的組織分工。一般來說,不可能將獲取情報和傳送情報由一個人來承擔。實際上,武志平是孫蔚如的三十八軍和紅四方面軍之間的聯絡人和情報傳送者。蒙定軍就此寫道:“楊虎城授權孫蔚如軍長出面與紅軍談判停戰,遂于1933年5月派武志平(系杜斌丞先生介紹,在軍部任少校參謀)同志為代表,持孫的親筆信,歷盡艱險,輾轉到達川北,與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聯系。紅軍亦即派徐以新同志為代表同武志平同志到漢中。徐以新、武志平在同孫蔚如談判時,孫的高參王宗山也參加了。談判是在戒備森嚴、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經幾次商談,雙方意見基本一致。徐以新同志回到川北匯報以后,二次又到漢中,雙方再經談判即達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的協議,從而使紅軍(四方面軍)減輕了陜南方面的威脅,能以主力對付川軍和蔣(蔣介石)、胡(胡宗南)軍隊,同時建立了有名的‘漢中交通線’。先后一年多,這條交通線一直通暢。由漢中至川陜交界處,系孫的防區,駐有軍隊,孫軍與紅軍信使往來,傳送情報,輸送物資,掩護去川北人員,均持有三十八軍軍用護照。這條交通線,不僅打破了對川北的封鎖,孫部還給紅軍提供了大量的軍用物資(如醫藥、通訊器材等)以及川陜甘軍用地圖,蔣、胡軍的軍事活動情報。”(《蒙定軍傳》第163頁)
這段關于楊虎城的三十八軍和紅四方面軍議和的文字和《1933: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漢中密約》所述基本相同。蒙定軍在文中將武志平的身份交代得很清楚:他是和紅四方面軍接洽、談判的三十八軍代表。
關于崔維峻向紅四方面軍提供情報以及他和武志平的關系,蒙定軍作了這樣的描述:“胡宗南軍尾隨紅四方面軍,曾一度進駐漢中。孫蔚如軍到漢中,胡軍退出漢中城,仍與孫軍聯防。雙方時有沖突、摩擦,胡軍妄圖將孫部擠出陜南,推向川北‘剿共’戰場。胡部特務在漢中活動,造謠破壞、鳴槍、打手榴彈、拉兵事件不斷發生。孫部官員極為憤恨,搶了國民黨在漢中機場給胡軍空投的軍餉物資,矛盾有發展成火并之勢。陜南肅反委員會也在殘殺革命同志和進步愛國青年。維峻同志將上述情況向徐以新同志作了匯報,使紅軍了解了陜南的全面情況。”
他還特別強調:“維峻同志是通過武志平同志介紹與徐以新同志見面的。”
蒙定軍接著又寫道:“維峻同志到陜南,在(陜南)特委的領導下,把全部精力傾注在情報工作上,并向徐以新同志做過多次匯報。徐走后,他把譯電室了解的陜南駐軍和胡宗南軍、川軍的絕密軍事情報和軍事部署、兵力駐地、任官姓名、武器裝備、軍事要地、各縣城防工事、修筑碉壘的計劃和實施過程,即蔣軍的‘步步為營’‘戰時互相支持計劃’等,均制表繪圖,加以說明。還有軍令部制發的夜間特別口令(普通為兩個字,戰時特別為四個字),均通過武志平同志經由交通線遞給了紅軍。”
這段文字詳細介紹了崔維峻向紅四方面軍提供軍事情報情況,大到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部署,小到夜間口令,既有看不見的絕密情報,又有看得見的城防工事、碉堡等。同時還介紹了崔維峻和武志平之間的關系,使我們不難發現三十八軍和紅四方面軍之間存在一條情報傳送鏈:情報源——崔維峻,傳送人和聯系人——武志平,情報送達目標和接受人——紅四方面軍代表徐以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和駐外大使)。崔維峻和武志平,一個在臺前,一個在幕后,一個公開,一個處于半隱蔽狀態,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了一項影響中國革命走向的偉大使命。
除夕夜王陵基度良宵抓戰機徐向前破圍剿
本文一開始介紹了紅四方面軍掌握的蔣軍密電碼對紅一方面軍走完二萬五千里長征所起的作用。回過頭來讓我們再看看這份密電碼對紅四方面軍所立下的功勞。
紅四方面軍通過這份寶貴的密電碼本,不斷截獲川軍情報,掌握了反圍剿作戰中的主動權。1933年11月初,川軍總司令劉湘調集四川各路軍閥共計20多萬兵力,對紅四方面軍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六路圍攻”,揚言三個月內要把紅四方面軍趕出四川。這是紅四方面軍入川以來所面臨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圍剿,雙方激戰了好幾個月,依然處于相持階段。能否粉碎川軍的“六路圍攻”關系到紅四方面軍能否在川北站住腳,關系到川陜根據地能否保住。關鍵時刻,密電碼起作用了。農歷春節即將來臨,川軍第五路總指揮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親屬們,紛紛電催王陵基返回萬縣老家過年,并料理私人財產。王陵基未請示劉湘,擅自將第五路總指揮權交其參謀長代理,自己返回萬縣與家人團聚。這一秘密行動,上自劉湘下至師團部屬皆不知情,卻被紅四方面軍從王陵基的來往電訊中獲悉。決戰時刻,統帥離位,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抓住這個戰機,于1934年2月14日清晨襲擊了王陵基的右翼,摧毀了其頭道防線的駐守旅,擊斃旅長。很快,第二道防線潰亂。紅軍乘勝向前推進15公里,直抵王陵基的總部,王的參謀長倉皇率部撤退。直到這時,第五路的師長、旅長們才知道王陵基回家過年的消息,軍心頓時大亂。川軍總司令劉湘聞知,大為惱火,解除了王陵基的第五路總指揮職務,將其軟禁。此役為紅四方面軍反“六路圍攻”打開了一個大缺口,最終取得勝利。
古今中外的戰史中,凡勝仗,皆有情報的功勞。有的戰役,情報起了關鍵作用。“運籌于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靠什么來運籌?不掌握敵情,怎么來運籌?中國兵圣孫子早就說過:“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張國燾毀約失信義臥底英雄含恨罹難
1935年2月3日,陜南地區寧姜、南鄭、馮縣、褒城一帶突然槍聲大作。自從國民政府軍第三十八軍和紅四方面軍于1933年6月24日簽署了互不侵犯的“漢中密約”后,兩軍相安無事,這一地區成了友好往來的“紅色交通線”。這突然響起的密集槍聲一下子破壞了雙方的協議,這是紅四方面軍根據張國燾的命令,向三十八軍防區發動進攻。軍長孫蔚如大惑不解,趕緊命令武志平前去交涉:“雙方定有互不侵犯協議,為何兵戎相見?”然而,武志平一去不返,顯然,這一突發事件及其發展超出了中共地下黨的預料和控制。
戰事持續了兩個星期,孫蔚如部劉文伯、王毅武兩個旅遭受損失,蔣介石急調5個師的兵力增援,堵擊紅四方面軍的北上企圖。
就在孫蔚如被這場突如其來的戰事弄得焦頭爛額之時,披著三十八軍“高參”外衣的中統特務王宗山前來進言:“軍座,該是清理內部的時候了,不然的話,共軍里應外合,我們都得完蛋。”
“你這是什么意思?”
王宗山湊近孫蔚如身邊說:“我早就提醒過您,崔維峻、成子慎、孫作賓、徐夢周、蒙定軍這些人是混入我軍的共產黨,這些人早晚要鬧事。不如趁早把他們……”
孫蔚如很不耐煩地說:“你們中統就知道捕人殺人。”
“高參”繼續煽動說:“共產黨從來不講信用,白紙黑字簽的協議,說撕毀就撕毀了,我們不殺他們,他們就要殺我們。”
孫蔚如對共產黨有他自己的看法。大革命時期,他和陜西早期的共產黨人魏野疇、李子洲合作,反對北洋軍閥,成為好朋友。“四一二”事變后蔣介石開始“清黨”,他和楊虎城將軍堅持不殺共產黨,而是采取“禮送出境”政策,西北軍在皖北駐扎時,南漢宸、曹力如這批共產黨人就是他孫蔚如親自送走的。到漢中以后,他還是堅持:“發現共產黨不能殺,可以給路費送其出境。”眼下,他知道自己這支部隊里還有共產黨,武志平、張漢民就是,他和楊將軍心里清楚。共產黨是人才,人才寧可留著不用,也不能用的時候沒有。留著他們就是必要時和紅軍聯系,以便和蔣介石抗衡。老蔣想用我們西北軍“剿共”,鷸蚌相爭,他這個漁翁得利,我現在和紅軍和平相處,看你老蔣奈我如何?和紅四方面軍簽署互不侵犯友好條約,武志平這個共產黨立了功啊!
如今,紅四方面軍向他突然襲擊,事前武志平毫不知情,事發后派去聯系,直到現在一點兒消息也沒有。情況不明,怎么能亂殺人?孫蔚如這樣想著,實在理不出頭緒來。眼下,最頭疼的是如何應付戰局,他沒有來得及認真思考王宗山提出的問題。
孫蔚如的未置可否,或者說沒有明確的表態,讓這個中統特務鉆了空子。紅四方面軍撕毀協議給三十八軍內的反共分子殘害中共地下黨組織提供了借口。
對于三十八軍這支非嫡系地方部隊,共產黨在爭取,國民黨也在想盡一切辦法控制。中統特務王宗山當上了孫蔚如的“高參”,軍統特務宋樹藩當上了參議,周燕蓀擔任軍特別黨部書記長,這三個人同時擔任陜南肅反委員會主要負責人;三十八軍軍法處處長李階人、軍法官史伯橋是肅反委員會會員。肅反委員會專事偵緝、逮捕、慘殺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受國民黨陜西省黨部直接操縱,下設偵緝隊,隊長曹子登,隊員李維城、張恩光等,同時又是三十八軍軍警稽查處稽查隊的人,一套人馬,兩套班子,“軍、地”兩用,一個目標:對付共產黨。
紅四方面軍圍攻漢中城的槍炮聲越來越響。一天晚上,偵緝隊突然將崔維峻秘密逮捕。當晚,好友于景琪冒著危險前去看守所看望,崔維峻見到他,又驚又喜,他沒有想到在這里會見到自己的同志,趁看守不注意,崔維峻將隨身攜帶的保密箱鑰匙交給于景琪,并示意他趕快離開,打開箱子就知道該怎么辦。于景琪是崔維峻所培養的黨員發展對象,他打開崔維峻的保密箱一看,大吃一驚,里面裝的是三十八軍內的黨員和預備黨員名單,其中就有他于景琪的大名,還有崔維峻所搜集的軍事情報,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破壞碉壘計劃”,尚未來得及送出。這些材料要是落在偵緝隊手里,潛伏在三十八軍內的共產黨員將會被一網打盡,中統特務王宗山要的正是這些所謂共產黨“內應”名單和他們向紅軍提供情報的證據。于景琪趕緊將這些材料銷毀。第二天一大早,偵緝隊對崔維峻的辦公室和宿舍進行搜查,一無所獲。
軍法官史伯橋對崔維峻連續審訊了兩個晚上,動用了刑具,崔維峻嚴守黨的秘密,寧死不屈。
1935年2月一天深夜,敵人將崔維峻秘密殺害,臨刑前,他高呼“共產黨萬歲”,劊子手用毛巾堵住他的嘴,特務張恩光用匕首殘忍地將他刺死。黨的好同志崔維峻為了提供關乎紅軍生死存亡的密電碼和其他軍事情報,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犧牲時,年僅25歲。

本文作者田潤民與崔維峻的侄子崔林杰(左)
細節構成歷史細節改變歷史
在文化大革命動亂的1968年4月,筆者回老家陜西省旬邑縣探親。在縣城期間,無意中看到一份當地紅衛兵小報,上面有一篇批判習仲勛的文章,揭發習仲勛曾說過“旬邑救中央”這么一句話。“文革”中的揭發批判大多是斷章取義和無限上綱。
然而,1987年4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勛為《崔景岳》一書所寫的序言引起我的聯想。序言中寫道:“我在陜甘邊蘇區和中共關中特委工作時,曾和崔廷儒(崔景岳)同志有過多次接觸和聯系。當時,他作為陜西白區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常和我們通情況,商對策,以求內外密切配合,開展工作。”“1939年初夏,他去延安途徑特(地)委駐地馬家堡(旬邑),我們兩人在一個房間里住了五天,日夜暢敘。”
五天時間,日夜暢敘,可以想見這兩位老戰友說了多少話!究竟說了些什么,習仲勛沒有細談,但兩位革命者的話題肯定離不開旬邑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和人物。其中,崔維峻又肯定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他不僅是崔廷儒的戰友,還是同族、同學,從輩分上講,他是崔廷儒的叔父,從黨內職位上,崔廷儒又是崔維峻的上級領導。1931年,崔廷儒派崔維峻打入孫蔚如部,崔維峻在三十八軍所從事的軍事情報工作受崔廷儒直接領導。
那么,習仲勛聽了崔維峻的事跡后,會說些什么?他會不會說“維峻同志救了中央”?“文革”中紅衛兵小報上的“旬邑救中央”是不是根據這句話斷章取義或者演繹而來?
“楊虎城給紅軍提供密電碼”,這個說法聽起來太抽象。楊虎城本人不可能把密電碼直接送到紅軍手里。那么,誰去干,怎么干?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歷史是由許多細節構成的,細節又能改變歷史。
崔維峻,一個改變了歷史細節的革命烈士。
責任編輯/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