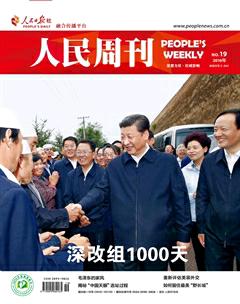遙想柳青:他絕不是只有土
喬葉
“一直以為柳青很土,這趟吳堡之行讓我知道,他固然是很土的,但他絕不是只有土。”
“5月初,我去了一趟陜北榆林的吳堡。這是柳青的故鄉。一路上聽了許多柳青的故事,百感交集……
一
“他頭上頂著一條麻袋,背上披著一條麻袋,抱著被窩卷兒,高興得滿臉笑容,走進一家小飯鋪里。他要了五分錢的一碗湯面,喝了兩碗面湯,吃了他媽給他烙的饃。他打著飽嗝,取開棉襖口袋上的鎖針用嘴唇夾住,掏出一個紅布小包來。他在飯桌上很仔細地打開紅布小包,又打開他妹子秀蘭寫過大字的一層紙,才取出那些七湊八湊起來的,用指頭捅雞屁股、錐鞋底子掙來的人民幣來,揀出最破的一張五分票,付了湯面錢。這五分票再裝下去,就要爛在他手里了……”
想到柳青,我腦子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曾經的中學課文《梁生寶買稻種》。多年之后,在《創業史》里讀到這些鄉味濃郁的細節,依然喜歡。相比而言,主旋律意識很明確的下一段文字似乎就有些突兀:“盡管飯鋪的堂倌和管賬先生一直嘲笑地盯他,他毫不局促地用不花錢的面湯,把風干的饃送進肚里去了。他更不因為人家笑他莊稼人帶錢的方式,顯得匆忙。相反,他在腦子里時刻警惕自己:出了門要拿穩,甭慌,免得差錯和丟失東西。辦不好事情,會失黨的威信哩。”
但是,莫名其妙的,又覺得很和諧。為什么呢?細細品來,便明白了:這兩段文字的底色一致,都是一種質樸淳厚的熱愛。無論是對于村鄰至親,還是對于政治身份。一直以為柳青很土,這趟吳堡之行讓我知道,他固然是很土的,但他絕不是只有土。《百年柳青——紀念柳青誕辰100周年文集》的前10頁是柳青先生的影像小輯。其中一張是少年柳青。后來,綏師因“赤色”濃烈被封。半年后,他又去上榆林六中。榆中的課程里有英文。他很快便能讀英文原著,成了英文學習會主席。許多英文名著,他背得滾瓜爛熟,幾十年后提起來還記憶猶新。
1937年,他21歲,已經擔任《西北文化日報》副刊編輯,同年開始學習俄文。1945年,他在米脂縣呂家崄工作的時候,聽說綏德縣一個人有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他去借書,頭天清晨出發,第二天天亮趕回,走了一百六十里。所以賈平凹說:“柳青骨子里是很現代的,他會外語,他閱讀量大,他身在農村,國家的事、文壇的事都清清楚楚。從《創業史》看,其結構、敘述方式、語言,受西方文學影響很大。”
他中年的那張照片應該是他流通最廣的標志性照片,照片上的他穿著對襟褂子,戴著圓圓的眼鏡,很像一個鄉紳——就我個人的審美,我覺得他更像一個村會計。還有一張照片,看不清他穿的什么衣服,仍然是圓圓的眼鏡,頭上多了一頂黑氈帽,這使得他有一種接近鄉村老人的慈祥。這時候的他,已經在長安縣的皇甫村住了多年。
二
《柳青紀念文集》厚厚兩卷,第一篇是陳忠實先生的文章《重讀創業史》。這是他在《創業史》發表5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陳忠實回憶說:“1982年的春天,我被我們西安市灞橋區派到渭河邊上去給農民分地,實行責任制。區上派的工作組到各個鄉鎮,開始給農民分地。我在我駐的那個公社先做了一個村子分牛分馬分地的試驗,總結經驗然后再推廣。我記得在渭河邊上第一個分牲畜的那個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都到一點左右了,我騎著自行車回駐地的時候,路過一個大池塘——蓮花池,剛從分牲畜的糾紛里冷靜下來,突然意識到,我在1982年春天在渭河邊傾心盡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上世紀50年代初在終南山下滈河邊上所做的工作構成了一個反動。完全是個反動……那個晚上從村子走回我駐地的時候,這個反動對我心理的撞擊至今難忘。生活發生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在我們文學界,多年以來涉及對《創業史》的評價,也是最致命的一個話題,就是農業合作社不存在了,《創業史》存在的意義如何……”
我忽然有點兒好奇:這個問題,柳青先生想過嗎?按照柳青的計劃,《創業史》第一部寫互助組階段,第二部寫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鞏固和發展,第三部寫合作化運動高潮,第四部寫全民整風和大躍進。但現實沒有也不可能按照他的預想來行進。1953年,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還是用十五年的時間來發展農業合作化,當時對蘇聯合作化的經驗和教訓深有研究的柳青欣慰地感慨說:“這是接受蘇聯合作化的經驗教訓,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制定出來的。”
據劉可風回憶,他極其關心政治,經常從自己的角度非常深入地思考分析國際和國內的政治形勢,甚至睡夢中都縈繞著政治問題。《柳青傳》里有一個細節:“他正在病床上熟睡,突然醒了,一骨碌坐起來,明眸中射出一道犀利的光說:‘我正在一個國際會議上和別人辯論呢,話還沒說完怎么就醒來了?”
兩年后的1955年7月,毛澤東發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這個速度是“小腳女人走路”。從此,形勢突變,高級社的成立大潮強勁席卷。柳青的寫作計劃也不斷進行著調整。1958年至1959年,柳青寫出了小說《狠透鐵》。書出版的時候,他在書名下方題寫了副標題:“1957年紀事。”他對關系親近的人說:“這篇小說是我對高級社一哄而起的控訴。”應該也就是在那時,他調整了《創業史》后續寫作計劃。晚年時候,有一次他和劉可風聊到《創業史》第四部的創作計劃,他說:“(第四部)主要內容是批判合作化運動怎樣走上了錯誤的路。我寫第四部要看當時的政治環境。如果還是現在這樣,我就說得隱蔽些。如果比現在放開些,我就說得明顯些……我說出來的話就是真話,不能說不讓說的真話,我就在小說里表現。”
“這些年,包括一些運動,來了就是一股風。不讓人分析,不管什么事都要‘一邊倒,所以,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不斷地‘翻餅子,下一個時代恐怕也會表現出來,我的《創業史》肯定會被否定。”能夠如此推斷自己的作品在未來的命運,這種理性近乎殘酷。與此同時,他也對自己的創作抱著低調而又頑強的信念。他曾和朋友李旭東談心,李旭東說:“我想,你所有作品的傾向很可能會被后人誤解。”他淡定地說:“不要緊,我四部寫完,人們就會知道我的全部看法了。”
1978年6月13日,他在北京病逝。他沒有寫完。
在影像小輯里,不期然間,我看到了李凖。那張照片一看就是擺拍的,是1960年夏天在北京出席第三次全國文代會,從左到右是:李凖、王汶石、柳青、杜鵬程。四個前輩里,同為河南人,我最熟悉的就是李凖,雖然我無緣見過他。想起他,我就想起紹興咸亨酒店里他的墨寶:“店小名氣大,老酒醉人多。”還想起李凖傳記《風中之樹》的作者、文學評論家孫蓀先生講述的一則軼事:1982年,李凖跟隨中國作協的作家代表團到國外訪問,他和團長一個房間。一天,他正在衛生間洗澡,忽然聽到團長喊他,連忙就從澡盆里跳了出來,慌亂間腳下濕滑就摔了一跤。他對孫蓀感嘆說:“團長又算什么呢?為什么不可以叫他等一等呢?我感到自己卑怯,我干嗎慌成那樣?”
1953年,李凖發表了小說《不能走那條路》,一舉成名。之后又有《老兵新傳》《小康人家》《李雙雙小傳》《龍馬精神》等,這些小說緊跟時代,緊跟政治,緊跟中心運動,如鮮花著錦。孫蓀如此評價李凖的上世紀50年代初到“文革”前的創作:“如果說時代潮流是風,他則是隨風搖曳的樹。有句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止,他這棵樹是寧愿隨風而動的……是毫無置疑地擁護并實踐文學從屬于、服務于現實政治甚至政策,自覺緊跟時代潮流,隨波逐流,進而推波助瀾的。”
記得中學時候寫作文,總有一項老師規定必須訓練的基本功,那就是摘抄名人名言,我們班的同學一定都會抄這一句:“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破折號后的名字,是柳青,他還有許多更經典的語錄,比如:“不要把我們的一切都說是正確的。實際上,我們一直都是在找尋正確的路。”
比如:“作家和作家之間最根本的差別往往不是文字技巧,而是在生活和思想上,同時也有意志的競賽。”
還有:“一切都是暫時的,只有人民是永恒的。”這最簡短的一句話里,我又看到了樹,風中之樹。對樹而言,所有的風都會過去。但是,樹扎根的土壤,永遠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