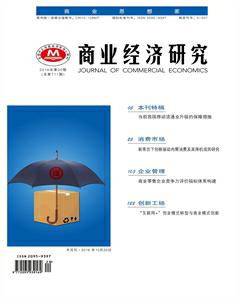垂直專業化、中間品進口對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作用機制分析
葉霖莉(集美大學誠毅學院 福建廈門 361000)
垂直專業化、中間品進口對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作用機制分析
葉霖莉
(集美大學誠毅學院福建廈門361000)
本文首先分析了垂直專業化、中間品進口影響產業價值鏈地位的內在機制,接著運用我國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從整體上、分行業、不同貿易形式和不同國家層面綜合實證檢驗了垂直專業化、中間進口品對我國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作用,并得出相關結論。
垂直專業化中間品進口價值鏈地位
過去幾十年,我國制造業在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體系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我國制造業主要承接的是低技術產品的生產和資本技術密集產品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在全球價值鏈中屬于從屬地位。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到底會對我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造成何種影響值得我們深入探討。此外,我國制造業中間品進口也在大幅增長,進口中間品存在學習效應,會促使企業提高生產率,還可使企業生產成本降低,提升企業產品利潤進而有助于企業出口產品技術含量的提升。那么我國制造業大量的中間品進口是否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提高產品技術含量,進而影響其國際價值鏈地位值得研究。
作用機制及基本假設
擁有雄厚的資本、高端先進的技術和豐富的生產經營管理經驗,使發達國家獲得了占領資本、技術密集的高附加值生產環節的先機。發展中國家只能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和豐裕的資源參與國際分工,承接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低附加值生產環節。在這種全球網絡下,發達國家的領導廠商與發展中國家生產廠商之間呈現的是一種“競合”關系。發達國家的下游企業為實現生產的順利進行,保證產品的質量,必須保證發展中國家的上游供應商提供的中間投入品是符合其質量和技術標準要求的。這樣,發達國家會對發展中國家企業提供相應的生產設備,進行技術指導或者人員培訓等。其次,發展中國家企業也會通過“干中學”效應吸收到發達國家技術擴散的成果。因此,參與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生產的初始階段,發展中國家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有所提高,其全球價值鏈地位進一步上升。但隨著垂直專業化分工的深入,發達國家為維護其高端價值鏈地位,可能會通過縱向控制及防止技術擴散條款等方式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進行“低端鎖定”,使發展中國家價值鏈地位的進一步升級受限。其垂直專業化水平與價值鏈地位之間可能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關系。據此,我們得出假設1。
假設1:我國制造業參與垂直專業化生產有助于其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但其垂直專業化水平與價值鏈地位會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關系。
全球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發展和深化導致了中間產品貿易規模的擴張,發展中國家在嵌入產品生產鏈的過程中,從國外進口了大量的中間投入品,這些進口中間產品會通過種類機制、質量機制和學習機制提高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產品的技術含量,進而影響其價值鏈地位。首先,進口中間產品種類增加,其與國內中間產品可能產生“互補”機制,不同種類中間產品集合產生“整體大于局部”的效應。中間產品種類越多,企業生產率越能得到提高,越有利于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其次,高質量的進口中間產品直接投入到生產過程,提高了最終產品的生產效率和質量。此外,技術含量較高的進口中間產品會刺激進口國對隱含在其中的技術知識進行學習、模仿甚至再創新,提高產品的生產技術,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了本國生產活動的技術含量,影響其產品的國際價值鏈地位。因此,我們得出假設2。
假設2:進口中間品對我國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提升具有促進作用。
計量模型及指標說明
(一)計量模型
根據上面的假設,本文設定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GVC變量代表制造業行業的全球價值鏈地位,i為行業,t為年份,VSS變量表示行業垂直專業化水平,VSS2為其平方項;IM為進口中間品,Xit為控制變量,含行業研發投入(RD)、人力資本水平(H)和行業平均規模(SC)。此外,受資源稟賦的限制,各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短期內很難改變,具持續性,因此將滯后效應納入回歸模型,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二)指標構建和數據說明
1.價值鏈地位(GVCit)。一國的價值鏈地位最后會體現在該國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上,因此采用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作為價值鏈分工地位的衡量指標。本文借鑒姚洋和張曄(2008)的方法進行測算,首先測算非貿易品部門的技術復雜度,得到投入產品表中所有部門的技術水平TSI,將行業j的復合技術含量定義為:


表1 整體回歸結果
其中,Vj為j部門復合技術含量,i為中間產品,j為最終產品,aij為每生產一單位j所需要的i中間投入品的投入。則行業j的國內技術含量VDj為:

其中,βi為第i種中間投入品中進口部分所占比重,用行業進口中間品價值/(行業總產值+行業進口中間品價值)表示。本文中價值鏈地位指標GVC采用測算后的VDj數據進行衡量。相關進出口數據來自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102個國家的數據。參照盛斌(2002)的方法,將Comtrade中SITC REV 3兩位數分類下的進出口數據按照我國投入產出表中的部門進行歸類,考慮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采用投入產出表中16個制造業行業,數據范圍為2000-2013年。行業間直接消耗系數來自投入產出表,目前我們只有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投入產出表,其余年份則采用替代的方式。中國進口總值數據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間產品數據來自Comtrade數據庫。
2.垂直專業化水平(VSS)。本文采用于津平、鄧娟(2014)的方法計算制造業行業垂直專業化水平。將出口分離為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分別測算各自的垂直專業化水平,再將加工貿易垂直專業化水平(VSSPi)和一般貿易垂直專業化水平(VSSDi)的進行加權平均,得到行業整體的垂直專業化水平,相關公式如下:

其中,MPi為i行業加工貿易進口額,XP為i行業加工貿易出口額。

其中,VSDi為i行業一般貿易出口中包含的進口價值,XDi為i行業一般貿易出口額。其中,Yi為行業總產值,(Yi-XPi)為i行業扣除加工貿易出口額后的產值,MIDi為i行業通過一般貿易方式獲得的進口中間品,分解為兩個部分:一是i行業一般貿易直接中間品進口(MIDi1),二是其他行業投入i行業生產而間接獲得的一般貿易進口中間品:即其中,cij為i行業生產中使用的j行業的價值,MDj為行業j一般貿易出口額,Yj為j行業總產值,為j行業一般貿易進口品價值在j行業生產總額中的比重。則一般貿易垂直專業化公式為:

表2 不同貿易形式、行業、來源地的回歸結果

計算中涉及到的加工貿易和一般貿易進出口數據根據國研網和《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整理得到,中間品進口數據見IM指標。計算時采用前文說明的16個制造業行業。
3.進口中間品(IM)。用制造業各行業進口中間產品數額來衡量。為得到相關數據,先參照盛斌(2002)的分類方法將BEC分類下對應的中間產品代碼轉換為SITC五位數代碼,再根據SITC分類,得到制造業各行業的SITC五位數代碼,通過Comtrade數據庫提供的SITC五位數代碼的中間產品進口額,加總得到各行業進口中間產品數額。4.控制變量(X)。研發投入(RD)采用行業內大中型企業內部科研經費支出來表示;人力資本水平(H)用科技活動人員占從業人員比重來表示;產業平均規模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來衡量。相關數據由歷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整理得到。
(三)計量方法
模型(2)解釋變量納入了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項GVCt-1,為克服動態面板
數據模型內生性問題,采用系統GMM法對模型(2)進行估計,GMM估計時模型工具變量采用被解釋變量及解釋變量的滯后一期,工具變量的有效性則用AR⑵檢驗法檢驗,用Hansen過度識別檢驗法檢驗模型設定的合理性。模型估計均用Stata11.0軟件計算完成。為考察結論的穩定性,下文將同時給出面板數據混合0LS方法估計結果和系統GMM估計結果。
實證檢驗結果及分析
(一)整體回歸結果
本文先綜合運用ADF-Fisher、PPFfisher、LLC和IPS四種單位根檢驗法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知各變量均為I(1)序列,但Kao ADF協整檢驗顯示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此種情況下進行的回歸,其結果是準確、可靠的。對模型(1)、(2)進行估計,結果見表1所示。表1 AR⑴、AR⑵值說明模型的殘差無序列相關,Hansen檢驗則接受工具變量有效性的零假設,說明模型設定是合理的,因此模型系統GMM動態估計結果是可靠的。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回歸結果,VSS變量的系數均顯著為正,而其平方項顯著為負,則表明了我國制造業的垂直專業化水平與其價值鏈地位升級之間呈現出倒“U”型關系,這與前文的假設1相符。從我國的實際來看,我國制造業憑借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參與到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中,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發達國家很多跨國公司的低技術生產環節和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都在我國完成,為了保證我國生產的產品符合其質量和技術標準,這些跨國公司勢必會對我國制造業進行了技術指導、員工培訓等活動,加上本國企業的“干中學效應”,參與垂直專業化生產初期確實促進了我國制造業產品技術含量的上升,對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提升起到促進作用。但發達國家希望中國只是其加工廠,會運用各種方式將我國企業“鎖定”在勞動和資源密集的低端價值鏈環節上,如美國對我國限制高新技術出口等,這樣將不利于我國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進一步升級。在此情況下,我國制造業垂直專業化水平對其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關系。
中間品進口對我國制造業價值鏈的升級發揮著正向影響。這與前文的假設2相符。近年來我國從國外進口的中間投入品質量有所提升,這些從國外進口的高質量中間投入品一方面直接通過投入產出效應提升企業勞動生產率,使企業生產函數外移,從而提高最終產品的技術含量;另一方面,高質量中間產品的進口會使我國制造業對隱含其中的知識進行學習、模仿直至再創新,提升我國企業的技術水平,使其出口產品技術含量提升,進而提高我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
表1從整體上考察了垂直專業化、進口中間品對價值鏈地位的影響,但忽視了幾個方面的因素:第一,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對價值鏈地位的影響機制不同,若研究垂直專業化與價值鏈地位關系時,對二者不加以區分,會產生偏差。第二,我國不同類型制造業參與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的程度及路徑是截然不同的,垂直專業化對價值鏈的影響可能存在行業異質性。第三,不同來源地的中間品的質量不同,對進口國的效應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接下來考察垂直專業化水平對價值鏈地位的影響是否存在貿易形式差異和行業差異,以及進口中間品對價值鏈的升級作用是否因來源國不同而有所差異。
(二)不同貿易形式、行業、來源地效果的檢驗
表2列(1)、(2)考察不同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對行業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分別為一般貿易形式和加工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分工水平。列(3)、(4)則考察制造業垂直專業化的價值鏈地位效應是否存在行業差異,引入行業要素密集度虛擬變量(DiVSS),行業為資本技術密集型Di取值1,為勞動密集型行業Di取0值。表2(5)、(6)列則考察不同來源地的進口中間品對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影響,來自發達國家(DECD國家)的中間進口品變量設為IM-DE,來自發展中國家(非DECD國家)的設為IM-FDE。為節省邊幅,文章列出主要變量回歸結果。由表2AR(1)、AR(2)及Hansen值可知不同形式下系統GMM估計結果是可靠的且對比兩種方法的估計結果顯示兩者并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回歸結果具穩健性。回歸結果顯示:
一是一般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對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要明顯大于加工貿易形式。一般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屬于主動承接的產品內分工形式,從事該貿易形式企業的資源整合及創新能力相對較高,這類企業能夠更好的吸收國際技術外溢,在垂直專業化分工中易獲得更多的收益,有利于價值鏈地位的提升。而加工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屬于“兩頭在外”的被動分工形式,我國參與加工貿易垂直專業化分工的企業,主要承接的是低技術、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而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環節都嚴重依賴于國外企業,這些企業在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過程中難以提升產品的國內技術含量,對其價值鏈地位的影響極為有限。
二是行業要素密集度變量(DiVSS)顯著為正,說明垂直專業化對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確實存在行業差異,參與垂直專業化對資本(技術)密集型制造業行業的價值鏈地位提升具顯著的作用,但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行業則無顯著的促進作用。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層次和分工業務的技術含量相對較低,且我國在這些行業與國外的技術差距較小,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對其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有限。而我國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垂直專業化分工水平較高,加工程度較深,使得這些行業能夠較好的承接發達國家轉移過來的生產環節,較大程度的發揮了進口技術溢出及產業關聯效應,有利于出口產品技術含量和產業價值鏈地位的提升。
三是來自發達國家的中間進口品對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來自發達國家的中間投入品的技術含量更高,我國企業在生產中大量采用這些質量高的中間投入品,一方面直接提高我國企業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在生產中通過學習、模仿可獲得更多隱含在進口中間產品中的技術知識,更有利于促進我國企業出口產品國內技術含量,提升制造業價值鏈地位。
結論和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第一,參與垂直專業化分工對我國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影響呈現顯著的倒“U ”型,一般貿易形式下的垂直專業化對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高于加工貿易形式,且這種提升作用在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較勞動密集型行業來得明顯。第二,進口中間品對外國制造業價值鏈地位攀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來自發達國家的進口中間投入品對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
基于以上結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我國要適應當前垂直專業化發展的趨勢,通過引進外商投資、承接外包、共同生產等方式積極融入國際生產分工體系中,利用技術溢出效應提高我國制造業產品的技術含量,在國際價值鏈中保有一席之地。同時,應警惕我國制造業被鎖定在價值鏈低附加值環節的趨向,采用財稅、金融優惠政策增加對企業研發資助力度,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推動制造業逐步向價值鏈核心環節延伸,改善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低端從屬地位。第二,一般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對制造業價值鏈地位的提升作用更為明顯,應進行貿易結構的調整,適當的降低加工貿易優惠政策,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更多地參與非加工貿易形式的垂直專業化分工從行業上看,垂直專業化對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價值鏈提升作用要高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因此,要著力提高勞動密集型行業在參與垂直專業化生產過程中的技術水平,通過科技利用與合作,提高其產品技術含量,縮小在垂直專業化分工過程中與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價值鏈地位的差距。第三,適度擴大中間產品的進口規模,優化進口結構。中間產品的進口對價值鏈地位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依靠自身的技術水平,我國制造業在短時間內很難實現技術突破實現生產環節的改進,從國外進口中間品引進先進技術顯得尤為重要。進口時應注意更多的進口高質量中間投入品,發達國家進口的中間產品技術含量更高,對價值鏈地位的促進作用更強,應加大來自發達國家中間產品的進口。
1.楚明欽,陳啟斐.中間品進口、技術進步與出口升級[J].國際貿易問題,2013(6)
2.劉磊.垂直專業化、中間產品進口與制造業國內技術含量[J].當代經濟科學,2013(5)
3.李強,鄭江淮.基于產品內分工的我國制造業價值鏈攀升:理論假設與實證分析[J].財貿經濟,2013(9)
4.邱斌,葉龍鳳,孫少勤.參與全球生產網絡對我國制造業價值鏈提升影響的實證研究——基于出口復雜度的分析[J].中國工業經濟,2012 (1)
5.馬紅旗,陳仲常.我國制造業垂直專業化生產與全球價值鏈升級的關系——基于全球價值鏈治理視角[J].南方經濟,2012(9)
6.盛斌.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于津平,鄧娟.垂直專業化、出口技術含量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3)
8.汪建新等.國際生產分割、中間投入品進口和出口產品質量[J].財經研究,2015(4)
9.姚洋,張曄.中國出口品國內技術含量升級的動態研究——來自全國及江蘇省、廣東省的證據[J].中國社會科學,2008(2)
10.趙增耀,沈能.垂直專業化分工對我國企業價值鏈影響的非線性效應[J],國際貿易問題,2014(5)
福建省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自貿區對福建省出口貿易品技術含量深化的影響研究(FJ2015C163)
F740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