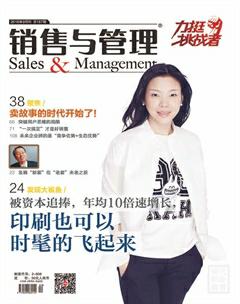80%的企業須重做戰略地圖
穆勝
在實踐中,即使放棄了有的關鍵戰略領域,但這也只是讓企業更聚焦于堵點,其他的關鍵戰略領域,由企業其他的管理系統來支撐,不用將其提到一個企業“最高的戰略級”來關注。但是,“放棄”仍然是高風險的。畢竟,我們的假設是企業有其他的管理系統來支撐那些關鍵戰略領域。但現實中,企業可能并不存在這些“其他的管理系統”,以至于堵點解決了,卻會因為其他戰略領域的問題而導致功虧一簣。另外,大家對于關鍵戰略的理解各異,關鍵戰略本身就不可能執行得很完美。
我們可以通過重做戰略地圖達到兩個目的:一方面讓企業建立更加平衡的管理系統,能夠關注到相對全面的關鍵戰略領域;另一方面讓高層統一思路,站在公司的高度明確每個關鍵戰略的深層意義。
高層任務描述
先提一個問題:高管們做的事情都是“戰略性”的嗎?并非如此。由于缺乏統一的戰略地圖,高管們往往各自為政,做著自以為重要卻不一定對企業重要的事情。事實上,他們也缺乏面對老板這個用戶的“用戶思維”。
這不怪他們,而要怪老板,如果企業的商業模式和戰略不能夠讓大部分高管都聽懂,顯然就是他的問題。我接觸高管時,他們會抱怨老板的思路不清,說得有理有據;但在接觸老板時,他們其實早就有謀篇布局,說得更有高度。其實,這就是個溝通問題,需要用高效的“對話武器”來解決。
不妨聽聽高管們會說什么,并這樣描述今年要做的三件大事:
*我今年要做……
*這件事要做到……(程度、目標)
*這件事對于公司的意義是……(最好連接到財務指標、客戶指標,但不強求)
這一步的意義有二:一是摸清“事”。了解高管們心中“實際的”重點工作是什么。老板的思路絕對是要有所突破的(相對一般趨勢),如果這種思路在有的方面居然沒有高管承接,并“放在心上”,那么企業的走勢基本不會與去年有太大區別。所以,走完這一步,專家教練心中應該有一幅基本的戰略地圖,接下來就是要填補那些沒有被承接的關鍵戰略領域或關鍵戰略;二是弄清“人”。這相當于高手對決時的“搭手”,很快就能摸清對方的“內力”。有的高管描述自己的重點工作根本就不在戰略主線上,那么,他一定就是局外人或者半個局外人。在組織討論時,專家教練既可以更有針對性地面對“主力”,又可以有針對性地激發“替補”主動承擔任務。平時大家都是高管,似乎“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但后面的戰略地圖一旦形成,所有人就會發現誰是“主力”,誰是“替補”。
某高管團隊描述完任務后,我居然發現80%的任務都壓到一個人頭上。可以想象,“一人干,多人看”的戰略執行又怎能落地?
常見的誤區是,高管們容易將目標當大事,例如:將管理費用降低30%。另外,他們還往往喜歡說大目標,但目標越大,事情就越虛。此時,專家教練一定要逼問:“您做的事情是什么?”只有說到具體點上,工作才會被他人所理解,才能放到戰略地圖里,成為系統中的一個部分,并得到相應的支持。
戰略地圖一:平衡積分卡
一定要有一幅高管們都認可的戰略地圖,否則在企業內部沒有統一的語種。但選擇什么樣的模板?這至關重要。好的戰略地圖模板能夠讓所有的資源更有效率地指向結果,反之則會把路帶偏。這里,有兩種常用的戰略地圖模板供參考。
第一是針對傳統業務,我推薦卡普蘭和諾頓基于平衡積分卡(BSC)開發的戰略地圖。這個工具首先確認了企業在財務層面的目標,而后倒推到用戶層面、內部流程層面和學習與成長層面,幾乎能夠囊括從核心競爭力理論到定位理論等主流的戰略學派觀點。
從財務層面上看,要確定企業究竟是要采用“生產率戰略”還是“增長戰略”。前者需要改善成本結構,擠出成本中的水分或提高資產利用率,將現有的資產盤活;后者要尋找“增長點”,增加收入機會(開發新產品、新市場、新伙伴)或提高客戶價值(現有客戶挖出更多盈利)。
從客戶層面上看,要確定企業的用戶和產品;從內部流程上看,要確定為支撐價值主張,需要什么樣的核心流程;從學習與成長角度看,要確定為支撐上述核心流程需要什么樣的無形資產。
當一幅戰略地圖被制定出來,所有的高管都會明確企業的戰略思路,也會明確自己的位置,老板的布局謀篇被用最簡單、直觀的方式進行了呈現。
戰略地圖二:宙斯模型
第二是針對新興互聯網業務,我推薦海爾首創的宙斯模型。這個模型的特色是,其并非從財務出發來進行戰略布局,而是首先關注用戶。因為,互聯網時代的特點是“用戶即財務”,用戶就是企業的財務數據,代表盈利空間,代表估值。極端的情況下,一些并不擁有實際資產的項目,僅僅依靠用戶數,也可以獲得市場的認可,羅輯思維、Papi醬等擁有用戶數的互聯網偶像能夠獲得投資,就是典型例證。
另外,沒有與用戶之間的交互,在平衡積分卡上定位出來的產品可能是錯誤的。
傳統的商業分析是以“產品”為核心的。產品是滿足用戶的單維需求,要將不同的產品放到一起分析,產業也是疆域的邊界。這種邏輯中,產業分析沿用S-C-P的框架,即行業結構(Structure)、企業行為(C o n d u c t)、經營績效(Performance)。確定行業結構是所有分析的基礎,包括行業里的供需情況、產品的差異性、市場集中度、進入壁壘等。
正如張瑞敏所言,沒有經過“用戶交互”的生產都應該被叫停,因為,那極有可能是庫存。探究一下這句話,如果僅僅分析產業結構,看到有空間就進入,看到沒空間就止步,肯定是錯誤的。因為,“空間”的存在既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用戶的心智有多重,關鍵是在某個層次上找到能夠觸動他們的“點”。找到了,即使原來有舊愛,產品也會變成新寵;沒有找到,即使產品各個方面表現得再好,也無法進入用戶心智。
從交互用戶上看,這一模型要求回答四個問題:我的用戶是誰?我能為用戶創造的價值是什么?我能分享什么價值?我的經營戰略和客戶戰略是否一致?這就是互聯網商業模式分析中驗證場景或用戶剛需的步驟。
從人力資源上看,互聯網項目成功的關鍵是人,而且是要有企業家精神的人——創客。確定有創客能夠做事了,這個項目才能啟動,之后就需要確保FU(職能模塊)、中平臺主、大平臺主能夠協同支持項目。
從預算零差上看,項目的目標應該在“零庫存、零簽字、零冗員”的“三零原則”下才能實施。
從閉環優化上看,是要確保每個階段里,項目的利益攸關者都能分享到“用戶付薪”,即分享到項目為用戶創造的機制。具體的方法包括設置基本酬、拐點酬、對賭酬等,好似一個嚴密的風投鎖定機制,確保風險共擔,收益共享。
簡單來說,完成了這幅戰略地圖后,企業就以用戶為起點,確認了有人做事,有錢投入,而且控制了過程風險,確保了即時分享,想成了強大的動力機制。
重找堵點與關鍵戰略
無論選擇哪條路徑,戰略地圖被制定出來以后,我們能夠根據這個基礎來尋找堵點,并制定關鍵戰略。在原來的模式中,我們通過使命—愿景—遠期目標—近期目標—關鍵戰略領域的分解步驟,得到的堵點可能不夠全面。原因很簡單,原來是“感性地”從遠期目標分解到近期目標再到關鍵戰略,更多的是依靠經驗而不是模型。
而一旦我們按照戰略地圖尋找堵點,基本上就不可能有遺漏。一般來說,在企業的戰略地圖中,會有幾條明顯的邏輯,穿越幾個維度指向最終的目標。這幾條邏輯中,一定有若干的“堵點”,否則就不會上升到戰略層面(戰略地圖),成為企業在戰略期內必須有所突破的關鍵。
例如:有的企業流程是正常的,但缺乏關鍵的人力資本來支撐,那么,人力資本的缺失就是“堵點”,關鍵戰略就是要“打造關鍵的人才隊伍”,我們為其制定“百川戰略”,要求百川匯流,“搶奪”行業內一切的優秀人才,甚至制定人盯人的挖獵任務。
當然,上述例子是以平衡積分卡為模板,屬于“學習與成長”和“內部流程”兩個內部維度上的堵點。有時,內部是沒有問題的,但外部找錯了方向,此時,就應該對“財務層面”和“客戶層面”進行相應調整。
例如,有的企業定錯了目標客戶群,執著于老用戶的深挖,但其實,這已經是一片紅海,而且老用戶的消費潛力已經被挖掘殆盡。此時,我們為其制定“新大陸戰略”,提出要轉化一批最大可能的新用戶,將產品勢能遷移到“新大陸”去,隨后,企業所有的流程和無形資產的資源都自然指向這個新的方向。
所以,最后一步是尋找邏輯鏈條上的堵點,并確定能夠突破這個堵點的關鍵戰略。平衡積分卡和宙斯模型這樣的專業工具會呈現出企業需要的戰略邏輯,總裁教練只需要引領企業的高管層檢視堵點即可。
在戰略地圖被確定以后,各個環節的操作方向都會呈現出來,這些操作一定要鎖定指標和目標,而指標和目標一定要背到高管身上,否則再好的戰略地圖也會被架空。在堵點和關鍵戰略確定之后,每個關鍵戰略都需要有高管來牽頭執行,假設今年企業有三大戰略,就相當于要打“三場硬仗”,高管需要“領仗”。
今天的競爭已經白熱化,互聯網改寫了商業底層邏輯。大概有80%的企業需要補上這一課。甚至一些優秀的企業也愿意“浪費”2—3天的時間重新做戰略地圖,為的是“好上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