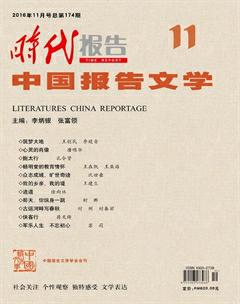尋找十三義士
孫翠翠
一、歲月深處的呼喚
深夜,坐落在群山之間的吉林省通化格外安靜,醫院里消毒水的氣味在靜謐的夜里顯得愈發濃烈。
徐金峰躺在白色的病床上,雙眼緊閉,一瓶液體正一滴一滴通過他的手臂流向全身,此刻他身體的各個部位都不聽使喚了,他的手、腳、眼睛、耳朵像憑空融化了一樣,感知不到它們的存在,他的大腦一片空白,拿捏不準自己是活著,還是死了,還是正徘徊在生與死的灰色地帶……
一片混沌中,隱約有腳步聲傳來,那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清晰,徐金峰努力地睜了睜眼睛,那是一個渾身是血的女子,鎖骨上穿著一根8號鐵絲……
徐金峰忍不住大叫,不知為何,他像啞了一樣,怎么也喊不出聲,他又連續叫了幾次,依然是啞的,女子慢慢向他踱來,身后是端著刺刀的日本兵……徐金峰努力地睜大眼睛,努力地揮動胳膊……
他感受到他的心臟怦怦地跳動,一股冷意順著手臂流進身體,他似乎聽到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耳邊喚他的名字,終于,他睜開了眼……
“老頭子,你醒了?”
徐金峰這才稍稍緩過神來,把目光移向懸在半空中的藥瓶,又慢慢移向四周。許久,他都難以入睡,他第一次那么清晰地看到了那個女子,他懷疑是手術的麻藥作用讓他產生了幻覺,可這感覺一直在幽暗的燈光下持續著,直到睡眠仁慈地將他占有。
天光再現時,徐金峰睜開了眼。他已經漸漸適應了醫院里消毒水的氣味,這讓他有種莫名的安全感,孩子們和老伴一直圍在他身邊照顧著,并告訴他,他僅僅是得了一場小病,做了一個很小的手術,但是徐金峰心里清楚,自己已經是癌癥晚期。
徐金峰從床頭拿起一本破爛的筆記本,黑色的封皮,內頁被寫得密密麻麻:范廣友(長春溝反日會長)、李興文(青溝子反日會長)、李文利(抗聯戰士李興文的岳父)、尹啟發(老母豬圈反日會長)、房老四(方慶好,農民自衛隊員)、梅老四(其弟梅老五是抗聯戰士)、金增順(抗聯六團小白龍連戰士)、宮德祥(抗聯戰士)、孫大姐(婦救會會長)。徐金峰花了8年時間,才找到十三義士中9個人的名字,他把它們仔仔細細寫在本子上,鐫刻在記憶深處。
徐金峰找到了93歲湯云成的回憶記錄。
那天,湯云成在哈泥河邊玩,突然,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一片嘈雜。一排破衣襤褸的人正緩慢往前移動,一根8號鐵絲穿透鎖骨,把他們串成一串。
鐵絲上的女子奄奄一息,一身青色粗布汗衫,補丁摞補丁,鎖骨周圍的血正一圈一圈向外擴散,頭上挽著的疙瘩鬢松松垮垮歪在一邊,擋住了半張臉。女子的雙腳已經邁不動了,全靠拖著一雙爛掉的千層底布鞋,往前挪動。
“趕走小日本,中國人民必勝!”聲音未落,日本兵飛起一腳,狠狠地踹在她的腰間,女子身體一晃,鎖骨處瞬間紅了大片。
“畜生做的小日本兒,你們都不得好死!”女子滿是血絲的眼里燃燒著熊熊大火。
日本兵氣急敗壞,刺刀柄像雨點一樣,向她的頭部砸去,血從她的嘴角、眼角、鼻孔流出來,五官似乎全都錯了位,她的雙腿徹底失去了知覺,整個人被掛在鐵絲上……
鐵絲上的人群由憤怒變成咆哮,他們用血淋淋的身體向日本兵撲去,雙手被綁在身后,他們就用腳、頭、牙齒與那白晃晃的刺刀搏斗……
“小日本兒,中國人壓不垮,打不倒,早晚會把你們送進地獄!”“起來跟他們干吧,父老鄉親們!把這些狗日的趕回老家……”怒罵聲、刺刀的刺殺聲、肉體在鐵絲上撕裂的聲音、身體倒地的聲音,混成一片。
日本兵一頓亂刺,順勢將他們一個個踹進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埋了。
“人心不死、國運不亡,中國人殺不盡、砍不光……”那些聲音,越來越遠,越來越小。
湯云成僵在高高的草叢里,眼淚不知流了多少。過了許久,他才拖著兩條軟塌塌的腿迷迷糊糊地走回家。很多天以后,他的雙腿依然沒有勁兒,連小便都沒有知覺。從此,他的夢里,永遠都是呼喊聲和那些閃著寒光的刺刀。他常常看到那根血肉模糊的粗鐵絲,那些人,就被活生生掛在鐵絲上,被刺刀挑開胸膛,被踹進坑里。那些交錯的叫罵聲,一直在湯云成心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湯云成躺在病床上,咽下生命里最后一口氣,他仍然分不清楚,這叫罵聲來自1936年農歷三月十五的郊外,還是來自他的心靈深處。
想起湯云成,徐金峰的眼睛濕了,最后一次見到湯云成,是在醫院里,徐金峰有很多很多不明白的問題,想問問他,可是他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只能艱難地在嘴角蹦出幾個字來:“得……讓……孩……子……們……知……道……”如今,湯云成已經走了,而那些聲音卻很奇異地在徐金峰的生命里回蕩,久久難以平息,一個個白天,一個個黑夜……
徐金峰終于解了心中的謎團,他長長地嘆了口氣,合上了筆記本。
凌晨時分,又有車子從他的房門前經過,伴著家屬低低的抽泣聲,徐金峰知道,又有人走了。躺在醫院里的生命,總是格外脆弱,一腳門里一腳門外,說不上哪一天,就邁向了另一個世界。或許,這一天,離自己也不會太遠。想到這,徐金峰的心里一沉,身子如同跌進深不見底的黑洞。
徐金峰時刻惦記著那沒找到的4個義士的名字,他計算著,化療已經有一些時日了,他應該離開這里啦!他試了試自己的身子,覺得還能走。于是,他做了一個決定——回光華鎮,繼續尋找。這是抗日聯軍在東北大地上的血淚史,更是中國人民抗日的烈火。作為一名老黨員,徐金峰不想也不能讓這些殉國義士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被人遺忘,最后連一個名字都沒在世間留下。
2012年,徐金峰在化療期間,再一次踏上征程。
二、昔日光華
在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上,像光華這樣的小鎮,小得不足掛齒,如果非要將它濃縮在中國的地圖上,可能連一個小黑點都找不到。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平凡的小鎮,在抗日戰爭時期,成為楊靖宇將軍所建立的“河里抗日根據地”重要組成部分。它曾是中共通化縣第一個黨支部的誕生地,也是解放戰爭“四保臨江”三次戰役的主戰場。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愛國志士、熱血民眾為了國家主權,為了民族利益,為了平等、自由和人的尊嚴,把鮮血和生命拋灑在這片土地上,譜寫成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壯歌。“光華”這個地名,就是因東北民主聯軍第四縱隊第十師師長杜光華在此處犧牲而得名。這個坐落于長白山支脈四方山以北、龍崗南麓的小鎮,將一條浩浩蕩蕩的哈泥河圍在腰間。“哈泥”滿語意為“哈爾民”,即祭神的刀。沒錯!波光粼粼的哈泥河,正如它的寓意“祭神的刀”一樣,以一種莊嚴、凜冽的精神氣質,世代影響、激勵著這座山區小鎮和小鎮的子民。
最初,“光華”地區并不叫光華,而叫廣生保,下轄11個村。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廣生保改名為訓養保。宣統二年(1910年)撤保制改為鄉制,原訓養保為惠柳鄉第二保。宣統三年(1911年)半截荒溝(今光華楊木橋)邱鴻賓捐土地十二畝為學田,建立了惠柳鄉立國民四校(今光華小學校址)。這是光華鎮的第一所學校。民國十二年(1923年)遵奉天省令,通化縣劃為八個區,光華為通化縣八區,也叫小荒溝。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將小鎮的平靜踏得七零八碎。人們不堪忍受侵略者的欺凌,紛紛起來反抗,沒有槍炮,小鎮的男人們拿起鐮刀、鋤頭等家什兒,用血肉之軀拼殺,通過參加大刀會、自衛軍,進行英勇抗日,保護自己的家園。
徐金峰的童年歲月,就在這些血、淚的時代背景下緩緩流過。他的奶奶、舅媽等親人都是當年那些慘案的親歷者,也曾經和其他百姓一起把家里唯一的糧食都送給抗日隊伍。關于當年十三義士就義的場景,徐金峰從記事起,就聽奶奶無數次講起過。“他們可都是大英雄啊,有給抗聯收集情報的,有專門送情報的,還有的組織大家為戰士們做鞋襪,還有的是反日會頭兒……可惜大家都沒記住這些人的名字,怕是以后,這些事、這些人都會被忘記了。”徐金峰幼年的小小心靈上,已經被那些紅色的故事占滿,他對奶奶、舅媽所經歷的年代,充滿了好奇。
徐金峰16歲參加工作,在公社賣釘子。少年的好奇心,就像一匹頑劣的小馬駒,被喂養得膘肥體壯,整天在他心里撒蹄狂奔。無論是木匠、鐵匠還是其他什么人,只要是來買釘子,除了要付錢之外,還要講上一兩段故事才行。
僅僅16歲的他,并不知道,這些聽起來散亂的故事,在他的心里自主排列,漸漸發酵,有一天成為不散的能量,成為一種堅定的信念,在他小小的心上,扎下“根”,燃成火。
2004年,徐金峰退休了。退休對于他來說,僅僅是從現有的崗位上退了下來,而在他的內心,作為一位共產黨員,責任和義務卻沒有退休,那是他一輩子的追求和堅守。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翻閱通化縣文史資料時發現,記載全縣各地革命歷史故事的材料中,關于光華鎮的記錄少之又少。光華鎮曾經發生了那么多的抗日故事,曾經有那么多人為保衛家園付出了生命,特別是十三義士為國捐軀的事跡,為什么在所有的歷史資料里,從來都未被記載?在東北抗聯史中,這也是一個重大的事件、一個悲壯的樂章。它是見證歷史、激發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情懷的生動教材,有充分的理由被后世所銘記。作為一名老黨員,他有責任將那些發生在當地的紅色故事還原,把紅色精神傳承和發揚下去。于是,徐金峰義無反顧地踏上了一條漫長的道路。而這條路,注定要從東北抗日聯軍開始。
東北抗日聯軍簡稱“抗聯”,雖然早已經載入抗戰史冊,但與抗聯有關的深層背景和相關故事,一直被埋沒在歲月的霧靄之中,若隱若現,朦朧不清。特別是那些抗日群眾和群眾組織,雖不屬抗聯戰斗序列,但見到抗聯沒有吃、穿、住,沒有給養保障,他們寧肯自己吃糠咽菜,忍饑挨餓,也要把糧食送給抗聯。是啊,想想東北抗聯的生存環境,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又怎能堅持斗爭14年呢?所以,從這個角度說,東北抗聯廣義上應該包含愛國的東北老百姓,他們是前線戰斗的后勤保障隊伍。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徐金峰一次又一次到靖宇陵園抄寫材料,企圖從這里找到相關線索。起初,徐金峰拿了一個小本子抄寫文字,因為工作量太大,他每天很早進去,很晚才出來,一天也抄不了多少。后來,他借了一個照相機,打算把材料都照下來,回家整理,可是這些寶貴材料都是用玻璃相框裱起來的,反光嚴重,用相機照出來的照片看不清。徐金峰的眼睛老花得越來越嚴重了。有的時候,趕上陰天下雨,屋子里很暗,徐金峰把眼睛緊貼玻璃柜也辨別不清楚。一個游客給他出了一個主意,買一臺望遠鏡。徐金峰一拍大腿:“我怎么沒想到?”有了望遠鏡,徐金峰更是一整天一整天站在資料柜前抄資料。
那段時間,徐金峰就像展覽室里一樁會移動的雕像。每個來參觀靖宇陵園的游人,不僅為當年的抗聯精神所動容,也為這個60多歲的老黨員而感動。
在靖宇陵園,徐金峰累歪了脖子,累花了眼睛,但他并不覺得苦,他收獲了一筆巨大的財富。這筆財富支撐他激情澎湃地走了十多年山路,讓他戰勝孤獨、疼痛、癌癥,更為他尋找十三義士劃定了范圍和方向。
三、婦救會會長
2004年,徐金峰搜集抗聯材料時,結識了83歲的魯守禮。據魯守禮回憶,日寇當年在通化地區大肆燒房、拆房、屠殺百姓。一時間,哈泥河、渾江、鴨綠江邊,到處都是被浸泡腫脹的裸尸。哈泥河變成了“吃人河”,渾江變成了“吃人江”。回憶起當年的慘象,魯守禮唱起了當年留下的歌:“河水流呵流,流著民族的血和仇,再不是江彎翠綠蕩漁舟,再不是浩渺煙波群山秀,血雨腥風瀟瀟下,無頭裸尸塞江流……”唱畢,魯守禮已然老淚縱橫。
1932年8、9月間,共產國際的執委第十二次全會決定,滿洲省委的總策略方針要有新的轉變,提出“開展游擊運動,在滿洲建立農民委員會,抵制政府的捐稅,沒收漢奸的財產,組織人民政權的選舉”等口號。通化地區掀起了參加人民革命軍的熱潮,群眾運動的“地火”,以中心縣委為核心,迅速向四外擴展。黨員、共青團員數量成倍增長,黨團員紛紛提出申請參軍,抗日義勇軍各支隊要求紅軍將他們改編為正規軍或游擊隊。少年連、兒童團發展迅猛。工人反日會、農民反日會、商工反日會以及婦女、青年反日救國會、反帝同盟會等團體會員組成了反日總會。
1933年夏,山洪沖毀光華鎮東升村古老的村莊。日偽統治者強迫老百姓修筑警備道(現公路)。一股強大的反日力量在人民群眾當中形成洶涌的暗流,仇恨在人們內心壓積、集結,等待著一引而發。1933年9月18日,東北3000萬民眾的武裝力量——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獨立師正式成立,并發布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獨立師成立宣言》,宣誓道:我們全體指揮員戰斗員誓與日本強盜及走狗“滿洲國”斗爭到底,實現收復東北失地,驅逐日本強盜出滿洲,推翻走狗“滿洲國”的統治,建立民眾政府的重大目標。光華人民盼來了自己的救星。
2005年,徐金峰通過多方打聽,找到慘案目擊者湯云成,湯云成回憶說,1934年春至1935年間,抗聯隊伍多次來到小荒溝(今光華鎮)秘密發動群眾成立“反日會”、“婦救會”、“農民自衛隊”等抗日組織。各抗日組織協助抗聯戰士在半截荒溝、大青溝、石場溝、馬鹿溝等深山老林里壓了地窨子儲存糧食、彈藥,建立了密室營地。因為年頭久遠,湯云成只想起了9個人,其中婦救會那個女義士的全名,他卻怎么也想不起來。
十三義士名字的準確和真實性至關重要,容不得半點含糊。2005年到2011年,徐金峰通過查資料、讀書、尋找知情老年人口述,逐一核實湯云成所提及的9個人。
2011年秋,他去東升村龍爪溝核實婦救會女子身份時,由于下坡車速過快,導致車子失衡,他下意識捏了一下車閘,車子戛然而止,他卻因為強大的慣性飛了出去。徐金峰趴在地上,半天都動不了,胳膊、手掌都麻了,鮮血從破裂的皮膚下滲了出來,他擼起褲腿時,膝蓋露著白色的骨頭。
徐金峰推著車子返回村子時,天色已晚,老人們都蹲在村口聊天,看到他一瘸一拐走來,趕緊攙扶著把他送進了衛生所。
處理傷口時,幾個老人你一嘴他一言,為徐金峰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李木匠說,當時小荒溝(今光華鎮)還被偽滿洲國統治,偽政府和日本鬼子為了斷絕抗聯的給養補充來源,實行集甲歸屯制,建起了集團部落,把各溝各岔分散的住戶,都集中在一個指定地點居住,不搬者就燒房子、殺人。居民點四周修有3米多高的大墻,并建有炮樓,所有可以出入的大門,都由偽軍或警察站崗,搜身檢查出入人員是否帶藥品、食品及衣物等給抗聯。住戶實行連坐(保)制,如有一戶通“匪”,十戶受牽連。
李木匠說,婦救會的會長姓孫,聽說后來被鬼子殺害了。她那時經常組織人把糧食、衣服、醫藥送到山上。當時抗聯隊伍上的人穿的都是翻花棉襖,爬冰臥雪鉆老林子,衣服都讓荊棘刮破了,露著胳膊肘子。孫大姐秘密組織鄉親們給部隊做棉衣,并把娘家一個半新棉袍扯了,又把弟弟家的被面、幔帳都毀了,全部做成棉襖。送棉衣上山時,孫大姐和他爹分頭行動,他爹在送棉衣的路上凍死了,被人發現的時候,還直立著靠在一棵樹旁,把棉衣緊緊地抱在懷里,寧可凍死也沒舍得穿上暖和暖和。
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徐金峰在心里已經認定了她的身份,但為了穩妥起見,他還是找到了另外幾個旁證,只可惜始終沒有人知道孫大姐的全名。
老人們說,這個孫大姐一家都是英雄,丈夫參軍一直沒有下落,老爹爹凍死在送棉衣的路上,孫大姐在哈泥河邊被殺害,而她唯一的弟弟,也是她家的最后一口人住在白家堡子,不幸的是,日本鬼子幾個月后就血洗了白家堡子,孫大姐的弟弟被扔進狼狗圈,被活活咬死。
四、白家堡慘案
說起白家堡子慘案,李木匠一輩子都沒忘記。每次講到這兒,他總是閉上眼,皺著眉,慢慢搖頭,好像通過這些面部變了形的表情,能稍稍緩解他心里的悲憤。
白家堡子,位于現在通化市興林鎮東南5公里的朝陽五隊。春天一到,白家堡子的溝溝岔岔里,大片大片罌粟花就開了。這是抗聯隊伍購買藥品、糧食、服裝、彈藥的經濟來源。想想它的用途,原本就妖嬈的罌粟,又多了幾分色彩。
1936年7月,罌粟快要收獲了,風吹過這些長滿罌粟的山溝溝時,夾帶了一股更加迷人的氣味。這氣味,不知道經過誰的嘴,傳到日本人的耳朵里。7月7日,伍田松下帶領日本守備隊和偽森林警察隊的兩個排,到南岔橫虎頭一帶毀壞即將收獲的罌粟。
抗聯部隊得到情報后,決定在白家堡子南雷家溝門打伏擊。
第二天上午10點,偽森林警察隊押著老百姓在前面走,伍田松下率日本守備隊走在最后。當日本守備隊全部進入伏擊圈王志明坎(今打鬼子坎)時,抗聯指揮員一聲令下,伏兵四起,戰士們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老百姓和偽警察聽后各自逃跑了。霎時間雨點般的子彈射向了日寇。不到15分鐘戰斗就結束了,11名日本兵全部被打死,伍田松下和一名翻譯官趁兩軍交戰之際,混入森林警察隊之中,連滾帶爬地逃回了本部。
吃了敗仗的小鬼子,咽不下這口氣。7月11日,他們調集通化、三源浦、山城鎮、朝陽鎮等地的日本守備隊約100多人,加上偽軍一個營的兵力,在日本守備隊大尉中山率領下,殺氣騰騰地向大荒溝撲來。日寇進入大荒溝后,先后派出特務和密探,都沒探聽到抗聯的下落,一連幾日都沒有消息,中山大尉十分惱火。
7月14日,日軍從白家堡子抓來青壯年30余人,以嫌疑犯的罪名押到警察署大院毒刑逼供。日本參事官齜著牙吼叫道:“你們說出抗聯的下落,皇軍大大的有賞。”一個青年厲聲說道:“我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們的!”日本參事官氣得面色青紫,猙獰地大叫“死啦死啦的!”隨后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他們把百姓綁在警察署門前的大樹上當作活靶子,進行刺殺練習;覺得不夠刺激,還把百姓扔到狼狗圈里,看著狼狗對他們進行撕咬,直到狼狗把人活活咬死。
1936年7月15日,天正下著濛濛細雨,日本守備隊及偽軍200多人,包圍了所謂“通匪區”白家堡子,把全體老百姓綁成一串押往大荒溝。叢家溝的孫大娘患傷寒病不能走,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在炕上。30多歲的刁大嫂,懷里抱著一個2歲孩子,手里還領著一個5歲的孩子,因為走得慢,日本兵上去就是一刺刀,隨著一聲慘叫,5歲的孩子被捅死了。刁大嫂哭喊道:“你們這些野獸,還我孩子”!她發瘋似地和敵人拼命,抓住一個鬼子的手,一口咬掉其兩根指頭,鬼子痛得直叫。這時另一個鬼子一把奪下刁大嫂懷中的孩子,摔在地上,對著刁大嫂的腹部猛刺數刀,刁大嫂的腸子淌了出來。兩個日本兵將刁大嫂和5歲的孩子一起扔到河里。摔在地上的嬰兒還在不停地哭,日本兵見狀,拎起他的兩條小腿也扔進了河里。
老百姓被抓進警察署大院的上午,村里的王大爺等3人,被日軍的翻譯說成是“通匪”,被吊死在大院東南的拴馬柱上。中午又有8個老百姓先后被刺死,隨后被拖到院里挖心,為鬼子祭靈。
陰雨濛濛,雷聲時斷時續,20多名持槍挎刀的日本兵,從大院綁出18名青年小伙子,又押到東山腳下,當鬼子要對他們下手時,小伙子們掙斷了綁繩,分頭逃跑,鬼子向他們開槍射擊……
第二批押到東山腳下的人更多,其中有8人各背一具剛剛被挖心祭靈的同胞尸體。日寇的4挺機槍一齊開火,老百姓就這樣一排排地倒下……
第三批被屠殺的人群中,有一位30多歲的山東大漢,他站在刑場上視死如歸,立而不跪。日本鬼子伍長松下,摸著兩撇八字胡,上下打量這條倔犟的漢子說:“你的不怕死?”山東大漢破口大罵:“日你個娘的,你們侵占了我們的國土,殺害我們老百姓,你們這些狼心狗肺……”,這時鬼子的刺刀刺向他的嘴,大漢一扭頭,刺刀從嘴角一直割裂到臉頰,只見大漢飛起一腳,把這個鬼子踢得連退好幾步,跌坐在地上,另一個鬼子兇惡地舉起戰刀劈向大漢,大漢倒下了,而大漢英勇不屈的民族氣節震懾了鬼子。
最后一批被屠殺的群眾,都是些老弱病殘和婦女兒童,鬼子邊走邊殺。有一位80多歲的老太太,走在人群的最后面,被鬼子一刀捅死;一位婦女懷里的孩子,嚇得哇哇直哭,被一個鬼子奪下,扯起孩子的兩條腿,向路旁的大樹摔去,孩子頓時腦漿四濺。黃昏時分,刑場上尸體遍地,血流成河。
李木匠講到這時,兩只胳膊直發抖,他習慣性地把夾在耳后的鉛筆握在手里,狠狠地拍著大腿,鉛筆尖扎在他的大腿上,折成了兩截,他卻渾然不知。
李木匠說,這些反日會的人都是好樣的,都是我們的大英雄。鬼子在血洗白家堡子之前,曾對這些人進行單獨提審,逼問他們抗日聯軍的下落。這些人明知道抗聯隊伍就在曲柳川、回頭溝、大甸子、四方山一帶,但他們沒有向敵人透露一個字,卻義正辭嚴地告訴敵人:抗日聯軍到處都是,無處不在,是你們小鬼子抓不盡、殺不絕的。婦女會的惠大嫂在就義前,把裝有大荒溝和白家堡子反日會成員名單的小鐵盒,交給她的小女兒,并叮囑她,一定要活著把它交給抗聯隊伍。鬼子掃射時,她用身體死死地護住女兒。
后來,徐金峰通過查史料得知,日寇這次血腥大屠殺,被害的無辜百姓共計400多人。郭漢臣、李忠昌,被捅了數刀僥幸活下來。惠大嫂的女兒叫惠連芳,當年僅有14歲,死里逃生后,歷盡千辛萬苦,把小鐵盒交給了抗聯隊伍,里面的名單沾滿了殉國者的血,而這個名單一旦落入敵人的手中,大荒溝街里也要被血洗。
鮮血和生命喚醒了人們的覺悟,生還者全部加入了抗聯的隊伍,整個通化地區加入抗聯隊伍的百姓更多了,他們要和小日本鬼子刀對刀、槍對槍地干。一首歌在渾江兩岸傳唱:“河水流啊流,流過我家大門口,往日歡樂變凄涼,骨肉分離血淚流!找不見大哥無頭尸,尋不到三哥無尸頭,家家與鬼子不共天,結下一海恨來、兩江仇。撲奔二哥殺鬼子,抗聯紅旗揚滿洲,白山黑水齊響應,打敗東洋惡鬼頭!清算日本侵略者,洗雪民族恥與仇!”
1965年7月15日,中共通化縣委、通化縣人民政府為紀念白家堡子死難同胞,永遠牢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行,在大荒溝(今興林鎮)的東山腳下建立一座“日偽統治時期死難同胞紀念碑”。
五、峰回路轉
2012年,徐金峰發現自己便血。為了不中斷尋找的腳步,他隱瞞了自己的病情。他聽說興林鎮98歲的姜生曾經是楊靖宇的警衛員,急匆匆去找他。可是徐金峰一連去了五次,姜生家都鎖著門。徐金峰實在沒有辦法,只好找到當地的朋友劉起。劉起說:“你都來5趟了?那這趟別白來,咱們跳進去看看。”徐金峰想想自己已經是快70歲的人了,曾經也是一鎮之長,貿然跳人家的圍墻不好,正猶豫呢,劉起已經翻墻入院,沖著他大喊:“進來吧,老爺子在家呢。”徐金峰一聽,顧不上年歲已高,顧不上沒痊愈的腿傷,跟著也跳了進去。
姜生年歲大了,耳朵也不好使,劉起和徐金峰想要問一句話,得沖著他大喊半天。說起當年抗聯的事,姜生竟一問三不知。他說那年他給楊靖宇當警衛員時,只有16歲,部隊最困難的時候,他就被解散回家了。
徐金峰失望極了。尋找十三義士的線索由此中斷。他的病情也不斷惡化,經診斷,他已經是膀胱癌晚期,醫生建議他馬上接受手術治療。此刻,徐金峰感覺到生命的天空里,黑如濃墨的彤云正壓頂而來。他只能利用最后的能量與時間賽跑。
術后,他立即加快了尋找的腳步。正當他在一堆材料里一籌莫展時,他在通化日報看到一條“八旬老人要為姥爺正名”的消息。報紙上說,大連市的劉書田的姥爺曾是小荒溝一帶的抗聯戰士,卻一直背負著土匪的身份。徐金峰輾轉與劉書田取得聯系,得知他的姥爺叫房德勝,但劉書田并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其姥爺的真實身份。徐金峰突然想起,2005年,曾聽一個老人提起過十三義士里有姓房的,但因為證據不足,徐金峰當時并沒敢采信。為了證實房德勝的真實身份,徐金峰先后3次去三岔河村和小龍爪溝尋訪。單憑老年人口述怕有差錯,徐金峰又分別到通化縣文史辦和通化市文史辦查找材料、請教專家。終于,在多人的努力下,核實了房德勝的身份,原來,房德勝為了隱藏自己的身份,一直叫方萬勝。方萬勝就是劉書田的姥爺房德勝。
徐金峰尋找十三義士的行動,感動了很多人。他經常會接到一些陌生來電,主動向他提供重要線索。其中有個老人叫李世文,他12歲時開始和父親李增芝一起給抗聯戰士送糧,掌握了不少當時的情況。令人驚喜的是,一見面他就說出了一個重要的名字——黃文舉,他是楊靖宇地下交通員老八號,當年他和八里哨、大荒溝、恨虎頭一帶情報站總負責人劉義配合密切,使哈泥河中、下游區域的敵情搜集、傳遞工作快速、準確,為抗聯打擊日寇提供了信息保障。李世文口述的這些材料,徐金峰在中共通化市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了查證。
黃文舉出身貧苦,他先是加入了農會和農民自衛隊,負責籌集糧食、鹽、咸菜、衣服、鞋、藥品等物資,他寧肯全家吃糠咽菜,大人孩子全身浮腫,也要把省下的糧食送給抗聯。為給抗聯送鹽,又怕被漢奸走狗發現,他先把鹽化成水,再把棉襖放在鹽水中浸泡后把襖面晾干,穿在身上送到抗聯密營。后來,他被選做秘密地下交通員,為抗聯傳送情報。黃文舉是當時可以直接見楊靖宇將軍的情報員之一,他進密營地界時,需要白天手拿一塊紅布(平時包錢用,常揣在懷里),夜間手拿點燃的3根香作暗號,經哨兵盤查后才能進入。
十三義士中還有一位,是與黃文舉接頭的重要人物,名叫李文秀,他是小荒溝一帶中心情報站的負責人。負責從過往行人口中獲取情報,也是周邊情報的交接點,有緊急情況和任務時,李文秀會親自傳遞。據通化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孫踐老人的多年研究和考證,李文秀是黃文舉的下線。當時,很多重要的情報都是由這3個人聯手送出來的。
小荒溝情報及時、準確,反日活動更加頻繁,抗聯隊伍時不時就會攻打守備隊,這讓日寇感到很撓頭。
1935年夏天的一個夜晚,小白龍率部又一次攻打了小荒溝日本守備隊,打傷日軍數人,致使日軍不敢貿然外出行動。1935深秋,他又襲擊東升警察分所,打死漢奸自衛團2人,活捉了警察宋殿奎。
敵人惱羞成怒,四處打探小白龍的下落,伺機進行“圍剿”,卻總是失敗。此時,小荒溝的情形,讓小日本覺得處處都有危險存在,他們甚至懷疑小荒溝已經“變紅”了。這時,小荒溝西集場子偽保長吳寶中等漢奸向日本人告密,稱小荒溝有不少秘密反日救國會、情報站等,還說小荒溝的百姓都在給抗聯隊伍送糧送衣,全部“通匪”。日本兵打算當晚就派兵偷襲小荒溝。這時,小荒溝情報站已經收到了這個重要情報。同時收到情報的還有當時偽通化縣縣長劉天成。劉天成雖然任職偽滿政府,但良心未泯。以他對日本人的了解,擔心日本人會血洗小荒溝。他馬上召集身邊可靠的警察開會,作了兩手準備。他先去勸福田小隊長,為小荒溝的百姓辯解一下,成功最好,如果勸不成,他就準備帶著福田到小荒溝親自看看情況。他召集4車警察跟著福田去小荒溝了解情況,這些警察只聽劉天成命令,如果小日本兒血洗小荒溝,這些警察就跟小日本撕破臉血拼一場;如果小荒溝沒有危險,這些警察就當是陪福田巡察了。
而此時,反日會也得到了消息,可是,這個時候轉移小荒溝的百姓已經來不及了,黃文舉、李文秀等人一方面把情報送往抗聯,另一方面組織十三義士及其他反日組織做好了戰斗準備。小日本兒來時,大家都正常勞動,假裝什么也不知道,如果小日本兒傷害老百姓,所有反日會的成員都準備拿起武器保家衛國,和小日本兒拼命。
這時,劉天成已經連夜見了福田小隊長,苦勸無果,于第二天一早陪著他來小荒溝看情況。他們站在最高處,發現小荒溝的農民依舊去田里種地,孩子們依舊到學校里上學,和平時并沒有兩樣。劉天成對福田說,自己對小荒溝一直很關注,確實沒什么問題。福田整整觀察了3天,并沒有看出異樣,便放棄了血洗計劃。就這樣,小荒溝避免了一場血雨腥風。
然而,只要日寇在,只要侵略者一天不被趕出中國,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就不會有一寸土地會得到真正的平靜。
六、為虎作倀
2013年,徐金峰從一份《南滿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發現,來自小荒溝、大荒溝等地方的抗日情緒讓日寇無比惶恐。他們一方面動用武力鎮壓,一方面通過收買漢奸、抓捕情報人員,迫害抗日者。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反日救國會、情報站不斷遭到破壞,一批批愛國人士被無情地殺害。
據王海成老人講,血洗白家堡子的慘案和漢奸有著直接關系。1936年端午節剛過,小荒溝(今光華鎮)西集場子偽保長吳寶和在單位門口碰到舊同事勾茂東,并邀請他到單位喝茶。吳寶和并不知道,此時的勾茂東已經是反日救國會的會長,在勾茂東眼里,吳寶和這些沒骨氣的漢奸早就該千刀萬剮。二人喝茶聊天,因為話不投機就面對面地干了起來。吳寶和說:“大荒溝和小荒溝一帶都是吃紅軍飯、喝共產水的,你去串親戚,要跟本保長說實話,不然我向脅坂司令官司舉報你。”吳寶和為了顯示他的能量,拿日本人嚇唬勾茂東。勾茂東哪吃這一套,火氣早就壓不住了,道:“誰不知道你姓吳的,鬧自衛軍時,你看人家王鳳閣勢力大,就做了他的情報員;后來王鳳閣抗日,你不跟著抗日,倒去舔日本人的洋屁股,把王鳳閣抗日隊伍上的人往日本人那里帶,你干這些缺德事,咋不怕出門碰到楊司令,攤上‘炸子兒呢?”說罷,勾茂東一甩袖子走了。他并沒想到,這一番話給自己惹下了殺身之禍。
當天,吳寶和就跑到日本人脅坂駐地山城鎮,告密楊靖宇的部隊就在大荒溝,隊上的人下來買糧,被他覺察到。他還說,大荒溝一帶已經沒有良民了,都“通匪”變紅了,那里家家戶戶給抗聯種大煙,就是為了賣了大煙給抗聯買糧食,支持他們抗日呢。脅坂一聽,來了精神,馬上讓吳寶和說說這些通匪的頭目都是誰。吳寶和早有準備,寫了一條長長的名單,這其中有反日救國會的人員,有抗聯的情報員,也有一些是吳寶中的異己、對頭。
很快,脅坂就調派了守備隊100名士兵,還命令300名偽軍協剿。7月5日,中川大尉遵令開始大搜捕,以“通紅軍”罪抓捕了勾茂東等人。
和勾茂東一起被抓的還有一名女交通員,打手們把她的衣服扯得凈光,把她的雙手綁在墻壁上的鐵環里,用繩子把她的腰身固定在兩個鐵鉤中間,然后問:“你要活還是要死?要活就趕快把和你聯系的同黨招出來,還有你們平時都在哪里接頭?”站在一旁的漢奸,馬上把燒得通紅的爐鉤子抽出來:“要想活命,就老實交代!”女交通員朝漢奸臉上啐了一口:“不要臉的東西!”漢奸將爐鉤子兇狠地壓到她的胸上,那雪白的皮膚頓時被燙得吱吱響,冒出一股黑煙。“臭娘們兒,不識相。快說,和你聯系的還有誰?”女交通員奄奄一息,說:“你還是人嗎?看看你的手吧,它沾的可都是你自己同胞的血。這些血,是要還的!”站在一旁的日本人指著掛在墻上的竹簽,一臉壞笑地說:“試試這個。”漢奸趕緊把竹簽取下來,用力插進女交通員的陰戶,并狠狠地轉動著。女交通員一聲慘叫,昏死過去。在這一次抓捕和拷問中,有人挺不過酷刑,昧著良心出賣了自己的戰友。
據王海成老人講,1936年,黃文舉以收山貨為名來到劉義家,讓他在農歷三月初十到窮棒子溝房老三家,與李文秀接頭取子彈,并送往恨虎頭抗聯密營。可是,他并不知道,房老三已被日寇收買,他指使王雙續(漢奸)給日本守備隊報信,并布下大網,準備抓人。劉義、李文秀剛接上頭,鬼子、警察一擁而上,把李文秀按倒在地。劉義見事不好,從地窨子的后窗逃跑了。李文秀被捕后,中心情報站遭到破壞。
據王新君老人講,家在大青溝的孫老大為了日本人給的一點賞錢,通過他的侄子,送信向日本人告密自衛隊和反日會的活動情況,日本守備隊開始抓人,情報員王忠和得知后,就把全家老小連夜轉移到小城鎮的六八擔。日本鬼子沒有抓到王忠和,卻把王存續當成王忠和抓去了。日本人對王存續施以“搟面條”的酷刑。兩個彪形大漢用大木杠子從王存續大腿往腳下搟,骨肉分離的那一刻,王存續沒有挺住,做了可恥的叛徒,隨后又有一批抗日愛國人士被捕。
漢奸,又是該死的漢奸!
1936年正月,由于漢奸、叛徒的出賣,十三位愛國義士先后被捕。日本鬼子對他們動用了極其殘暴的酷刑,企圖從他們身上得到重要的信息。鞭子抽、板子打、罰跪、罰站等老辦法并不能撬動他們的嘴,日寇把他們扒光吊在雪地里,先給他們灌一肚子冰水,再將冰水一遍一遍潑在他們身上。這些寧死也不“交代”的硬骨頭還被扔進狼狗圈,被狼狗撕咬。日本鬼子還對他們施行了其他酷刑,如裝入麻袋里摔、子母彈剜肋巴骨、開水澆后背、坐老虎凳、坐火爐、拴拇指上大掛打秋千、壓烙鐵、壓杠子壓碎腿脛骨、竹劍刺陰戶、指甲蓋里釘竹簽……鬼子的酷刑只能奪走生命,卻沒有動搖義士們的信念,十三義士嘗遍酷刑后,堅貞不屈,大罵日本鬼子的惡行。日本鬼子對他們軟硬兼施依然沒有作用,不得不謀劃著把氣息奄奄的他們全部活埋。
七、尾聲
2015年,徐金峰歷盡千辛萬苦,找到并核實了十二位愛國義士的名字和身份,但因年代久遠,還有一位義士的名字沒有找到,這時距離他們為國捐軀已經過去了整整79年。
79年過去了,哈泥河兩岸廣闊的農田鋪陳如畫。湍流的河水如一條白色哈達,將那些碧綠的農田間隔成均勻、規則的條塊。兩只野鶴在哈泥河里嬉戲,白茫茫的霧氣如同這79年的光陰一樣,把一個血淋淋的世界和另一個幸福平靜的小鎮隔離開來,或是以另一種狀態連接起來。
在當地政府的支持下,徐金峰把義士們的名字鐫刻在石碑上,并在哈泥河岸他們就義的地方,樹立起來。立紀念碑那天,86歲的老人劉書田帶著全家人從大連趕來祭拜。他的姥爺曾是頂天立地的抗聯志士。劉書田在紀念碑前放聲大哭。
此時,群巒垂首、萬物低泣,猛烈的山風,為民族解放戰爭流血的英雄奏響了悲壯的哀樂。白茫茫的霧氣隨著太陽的升起,正一點一點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