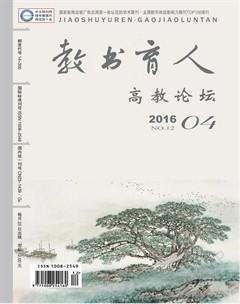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特征及啟示
任麗嬋
[摘 要] 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歷程是一個不斷改革高等教育,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所需人才的過程。基于日本高等教育發展史實,可以發現:政府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推動力量、多種角色的高等教育機構‘各司其職、不斷推進激活高校內部體系的改革、基于本土和院校內部的發展這四個凸顯的特征。并以此為鑒,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之路提出四點啟示。
[關鍵詞] 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特征;啟示
[中圖分類號] G53/5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8-2549(2016) 04-0032-03
近代日本高等教育自明治維新開始,并于戰后獲得快速發展。日本之所以能在20世紀60年代末一躍成為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高素質勞動人口的增加。到了80年代,日本在許多尖端技術領域超過美國,“經濟大國”的國際地位奠定之后,開始追尋增加“作為政治大國的份量”,并把教育改革視作與行政、財政改革同等重要的地位。包括新世紀的“新成長戰略方針”“人財立國”等國策在內,都體現了日本希望通過教育培養大批國際化日本人的目的。2007年,日本高等教育中全日制在校生的毛入學率達到54.6%,如果將非全日制大學生入學人數也算進去,大學入學率則達到77.6%。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發達,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培育了各種高層次管理和技術人才。可以說,日本能夠在國際舞臺中扮演“強國”的角色,與其高等教育的強大有著直接的關系。分析其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凸顯特征,將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歷程提出有益啟示。
一 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特征
1 國家意志始終是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無形指揮棒,政府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推動力量
日本國家、政府層面非常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始終將高等教育強國作為一種國家戰略。明治初期就制定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強國戰略。戰后,日本政府所倡導的經濟增長主義(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強調將教育計劃納入經濟計劃,促使日本高等教育規模在20世紀60年代獲得了快速擴充。到70年代后半期,日本將高等教育政策由“擴大數量”調整為“提高質量”。作為戰后一直是靠技術、靠教育立國的日本,進入80年代后開始推行“科技立國”戰略,掀起了新的技術革命,并將教育改革與行政、財政改革共同視為日本未來的三大改革。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推動力量來自政府。它總是以法律的形式“自上而下”地貫徹國家意志,在它背后有許多教育咨詢機構為其提供各項專業服務。例如,“臨時教育審議會”是20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專門對于教育各項改革方針開展咨詢的機構。該機構陸續發表的四次咨詢報告基本上揭示了日本未來教育發展的宏偉藍圖。日本政府則是本著“最大限度地尊重咨詢報告的精神,盡快將其付諸實施”的方針,隨后就頒布了“四六答申”、《私立學校振興助成法》等法規。1987年日本又成立了大學審議會,它和臨時教育審議會一起成為影響日本20世紀90年代以后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政府咨詢機構。大學審議會在成立后的10余年中向文部省提出了22份高等教育改革的咨詢報告。日本90年代修訂的《大學設置基準》《學位規則》等以及制定的《國立大學法人法》《研究生教育振興施政綱要》等,都是在此咨詢報告的基礎上進行的。
2 多種角色的高等教育機構“各司其職”,分別承擔精英、大眾人才的培養任務
日本與美國通過新成立“贈地學院”實現大眾化的方式不同,它是依賴于戰前就存在的“專門學校”實現其規模擴充的目標。日本戰前就形成了“二元二層”(二元指官、私立;二層指帝國大學、專門學校)的高等教育體制。帝國大學是日本政府所建立的、能夠真正適應國家需要的一種精英教育機構,它一直扮演著培養高級精英人才的角色。專門學校在日本同樣占有重要的地位,幾乎二戰前的所有大學都是以“專門學校”的形式建立,它為日本培養了大批適應時代所需的勞動力。戰后日本高等教育機構除原有的四年制大學、短期大學外,又建立了專門進行短期職業訓練的專修學校以及許多新型的科學技術大學、教育大學、圖書館情報大學、廣播電視大學等,適應了經濟社會的多樣化需求。日本高等教育發展路徑基本上是依靠帝國大學為其培養“向上”的高級人才,專門學校為其培養“向下”的各類人才的方式。
此外,日本高等教育規模在短期內迅速擴充還得益于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日本私立大學幾乎與國立大學并肩產生,而且只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其學校數量和在校生數就遠遠超過國立大學。1952年時,日本私立大學就已經有116所,占全部大學的53%,學生數為22.5萬人,占大學生總數的56%。到60年代,日本大學數量增加1倍而學生數增加3倍的原因也在于私立大學的發展。1979年時,四年制大學的入學新生中79%都上了私立大學。這些私立大學適應社會需要,為日本培養了大批工商法等各類企業職員。
3 激活高等教育體系的改革不斷推進,以扭轉大學變革的力量源于外部的局面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完全處于一種外力促進的“被動”狀態中。各高校開展的許多改革都是在政府的強力推動下進行的。70年代以后,大學開始主動參與改革,開展了更多傾向于來自大學內部的、圍繞大學課程、內部管理等微觀層面的一系列改革。此時大學的改革相比之前來講表現出很高的活躍性,包括各老牌大學在內都紛紛獨立研究生院、設立“綜合科學部”、并進行系列課程改革等。但這種內部改革的動力最終還是源于外部力量的刺激,并沒有從內部體制、機制上發生根本變化。日本各大學,尤其是官立大學,仍然保持著依靠文部省“保駕護航”的傳統。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文部省修訂了以《大學設置基準》為首的一系列法規。此次修改采取了粗線條式勾勒的方式,只就一些主要、重要問題作“大鋼化、簡要化”的規定,這也就給予大學相對自由的空間。進入新世紀,伴隨著要求增強大學教學研究活力和適應性的強烈呼聲,日本政府對國立大學進行了法人化改革,將其納入以“市場與競爭”為基礎的、新型的“開放體系”社會秩序中。這次改革與以往的歷次改革不同,它要改變包括私立大學、公立大學在內的整個大學體系,實現政府、市場、大學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這項改革不僅為日本公共財政減負,而且從體制上扭轉了大學長期的“惰性”,實現了組織機構的自律。
4 從模仿、依附到獨立、創新——基于本土和院校內部的發展是根本路徑
戰前日本模仿德國,形成了“國家主義”教育體制。此時帝國大學的辦學模式、課程設置、教學方法等都在積極學習西方。戰后,日本教育在美國占領軍指導下開展了一次全面改革,使戰前只培養少數精英人才的大學轉變為向廣大民眾開放的新制大學體系。到20世紀70年代末,伴隨經濟實力的提高以及規模擴充所產生的系列問題,日本開始探索獨立發展之路。尤其是在90年代以后,為了將日本大學打造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機構,日本出臺了一系列諸如21世紀“COE”計劃、國立大學法人化等強化質量發展的改革措施。縱觀近代日本高等教育改革過程,作為一個“后發外生型”國家,模仿、依附是存在的事實,但不斷尋求本土化和院校內部的改革、創新也是其發展的特點。單從高等教育機構上看:專門學校是最具日本特色的、也是僅存在于戰前的一種“日本式”高等教育機構;短期大學則是日本戰后初期對于一些不符合升格為大學的專門學校實施的一種“暫行措施”;70年代后建立的專修學校又是進行短期職業訓練的學校,等等。可見,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的根本途徑是基于本土策略的、尋求院校內部動力的改革。
二 對我國建設高等教育改革的啟示
如果說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是“趕超”式的,其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從10.3%提高到38.9%僅用了15年時間(1960~1975年)。那么,中國高等教育從“精英”向“大眾化”的跨越更是快得驚人,我們僅在幾年內就跨過了西方國家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走過的路。兩國高等教育規模發展的相似性,決定了吸取日本高等教育強國過程之“精華”為我所用有著積極的意義。
1 高等教育強國的實現至少在起步時需要經歷“自上而下”的路徑,需要依靠政府的強力推動
我國仍處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決定了我們只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甚至需要采取不均衡策略,將有限的資源放到最有益的項目上。尤其對于這樣一個有著“自上而下”傳統的國家,往往是政府牽頭的改革才能發揮資源的集中優勢。比照日本高等教育強國的進程,至少在改革之初需要這樣。另外,就我國高校目前的融資能力看,暫時也離不開政府的大力財政支持。因此,將“高等教育強國”作為一種國家戰略,通過政府的外力推行改革,對于我國當前高等教育的發展有著特殊重要的意義。它能夠充分體現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性價值,保障自上而下地貫徹一種“把高等教育做強”的理念,促進各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改革高等教育發展的具體行動。
2 提高高等教育政策出臺的適恰性,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是有效改革高等教育的保障
日本高等教育每一項改革的背后都有著某一重大政策或法律的支持。它們給日本高等教育發展創設了有效的外部環境。在我國推進高等教育改革的進程中,同樣離不開政策或法律的支持。尤其是對于一貫以來存在的某些偏見,比如對民辦院校的偏見等,更需要從政策、法律的視角給予“糾偏”。但實際情況是,政策、法律在發揮“糾偏”作用的同時往往也冒著“跑偏”的風險,因此,最大程度地防范政策出臺的非理性和法律制定的民主參與性,加強實踐環節的監督都顯得非常重要。日本在減少政策、法律風險方面的一個有效策略是開展各種專業機構的咨詢、審議、評價活動,而各咨詢會、審議會等也“不負眾望”地影響到了日本文部省的決策。結合我國實際,我們既可以鼓勵各種第三方部門開展政策咨詢、評估等活動,也可以考慮在政府部門內部設立專門進行高等教育發展的專業研究、咨詢、評估機構。
3 倡導“包容性發展”的理念,推進建設開放、多樣的高等教育體系
2007年亞洲發展銀行的經濟學家首次提出“包容性增長”概念,并將其作為經濟發展的新理念。其核心要義是消除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和所面臨的社會排斥,實現機會平等和公平參與,使所有群體均能為經濟發展做貢獻并合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在高等教育面臨著各種復雜形勢和重大歷史使命的背景下,將“包容性發展”(高等教育規模增長的有限性決定了只能談“發展”)作為指導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理念,無論從解決教育公平的視角還是從激活教育機制的視角,都將是一種新的思路。其實,日本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同樣是“多樣化”高等教育機構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國際化、開放化也一直在作為它的一個改革方向。包容性發展理念本身要求開展兼顧教育公平的、充分發揮資源優勢的變革,它的實踐落腳點也就體現在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建設開放多樣的高等教育體系上。
4 加快進行本土化改革和基于院校內部的變革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根本出路
我國高等教育經歷“大發展”的同時,也凸顯出了“各種矛盾和問題”。民眾把人才質量下降、就業形勢嚴峻等問題都直接歸咎于擴招。解決這些現實問題,唯有靠基于自身實際的獨立、創新之路。日本高等教育追尋質量提升的過程展現的是一幅充滿“荊棘”的圖景,尤其是最近開展的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更是一項不斷經歷“陣痛”的變革。其總體趨勢是:文部省對大學的控制逐漸由微觀控制變為宏觀調控;大學的發展逐漸由外部動力刺激下的變革轉變為源于內部動力的自主發展。可見,政府發揮作用的方式將隨著高等教育改革進程的推進越來越表現的宏觀、模糊,而高等教育變強的“期望”則越來越寄托在院校層面的改革上。在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步入大眾化發展階段,基于質量提升的改革將成為今后的發展方向,而加快進行本土化和院校內部的變革,努力盤活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也是一個重要的奮斗目標。
參考文獻
[1]胡建華.高等教育強國視野下的高校人才培養制度改革[J].高等教育研究,2009(10).
[2]史朝.現代日本高等教育發展機制研究[M].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
[3]蔡榮鑫.“包容性增長”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內涵[J].經濟學家,2009(1).
[4]胡建華.戰后日本大學史[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5]朱永新,王智新.當代日本高等教育(當代日本教育叢書)[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6]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M].陳武元,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
[7]黃福濤.外國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8]天野郁夫.日本國立大學的法人化:現狀與課題[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4).
[9]周遠清.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強音:建設高等教育強國[J].中國高等教育,2008(3).
[10]鄔大光.高等教育強國的內涵、本質與基本特征[J].中國高教研究,2010(1).
[11]Kazuyuki Kitamura. Policy issue in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34: 141–150, 1997. 1997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
[12]Shigeru Nakayama. Independence and choice: Western impacts on Japanese higher education[J]. Higher Education 18:31-48(1989).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