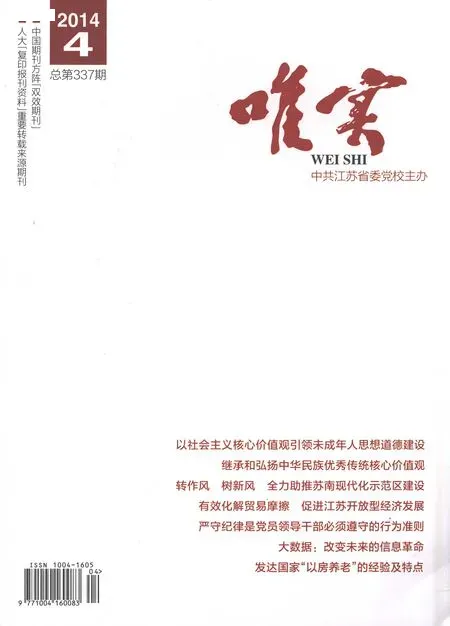“科研,為什么非要成功了才能報道?”
劉根生
1979年7月,漢字激光照排系統(tǒng)首張樣片出來時,王選激動地告訴記者,“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由于系統(tǒng)不可靠,軟件尚未完成,還不能實際使用,基本上沒有媒體愿意報道。只有《光明日報》記者“繞過各種困難”,報道了這項重大技術突破。這則報道被王選在玻璃臺板下放了十年,以激勵自己“一定要對得起這張報紙”。記者由此發(fā)問:“一個科研成果,為什么非要成功了才能報道?”
把“科研成果非要成功了才報道”絕對化,實屬“貌似求真”。科學研究是長途跋涉,“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積小勝為大勝”。把“成功”等同于“大獲全勝”,難免對“階段性成果”視而不見,也是“失真”。科學研究更是“壯麗探險”,隨時可能遭遇波折,不見“大獲全勝”不報道,無非是為了“絕對保險”。這種“負責”,實際上苛求科研,是容不得“階段性失敗”,也是以負責之名行推責之實。
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回想提取青蒿素過程時則說:課題組篩選了4萬多種抗瘧疾化合物和中草藥,歷經(jīng)190多次失敗后才終于打開成功之門。科研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失敗具有天然合理性,也自有其價值。在很多時候失敗是告訴你“此路不通”,當另覓新途。一次次總結經(jīng)驗,一次次吸取教訓,才有了一次次“階段性成果”,直到“大獲全勝”。及時報道科研“階段性成果”,才是以求真務實態(tài)度對待科研。“尚未完成”也好,“有缺陷”也好,都沒有關系,如實報道就是了。這對激勵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意義非凡。就算報道之后“階段性成果”又遇到了“階段性失敗”也沒關系,那就再靜觀其變好了。
在科研領域中有種現(xiàn)象,選題或項目如果成功率過高,往往說明過于循規(guī)蹈矩和前瞻性不夠,十有八九是“跟蹤模仿”,或低層次重復。這類科研當然也需要,但安于這種狀態(tài)就令人擔憂了,因為自主創(chuàng)新大廈歸根到底要靠顛覆性科技創(chuàng)新來支撐。然而,片面追求高成功率,幾乎已成當今科研領域通病。科技部有位負責人指出:在科技項目評審中,常常是“風險,一票否決”,結果便是“小兒科”成果太多。把“科研成果非要成功了才報道”絕對化,也是在片面追求高成功率。輿論具有導向作用,對科研成果非“大獲全勝”不報道,更強化了片面追求高成功率傾向,加劇了科研領域種種急功近利行為。
“漢字激光照排系統(tǒng)”報道波折已過去30多年了,把“科研成果非要成功了才報道”絕對化思維依舊存在。一個典型表現(xiàn)就是,把報道“階段性成果”當成惡意炒作。比如有媒體刊文批評石墨烯報道是炒作。其理由是,石墨烯的商用還需要優(yōu)化石墨烯結構以及石墨烯使用方法,以提升鋰電池性能。石墨烯是新型納米材料,因其導電導熱性能最強等優(yōu)勢被稱為“黑金”和“新材料之王”。因成功從石墨中分離出石墨烯,兩位科學家還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就因為石墨烯還有待優(yōu)化就把相關報道視為炒作,進而擔心“助推了科技界浮躁之風”,實在是“多慮了”。
“沉默的螺旋”是公共輿論研究中著名理論:在公開表達中,由于一方“保持沉默”,使得對方意見變得更加強勢。如此循環(huán)往復,便形成了“一方聲音越來越強大,一方聲音越來越微弱”的螺旋發(fā)展過程。在科研領域中,“沉默的螺旋”也成了種現(xiàn)象。一方面是科研作弊被不斷曝光,一方面是科研成果得不到充分報道,致使不少人對科技界信心大減。科研作弊當然要揭露和批評,但不能“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走出“科研成果非要成功了才報道”誤區(qū),多多客觀報道科研“正在進行時”,改變“沉默的螺旋”現(xiàn)象,提升科研公信力和提振科研信心,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迫切和重要了。
(作者單位:南京日報評論部)
責任編輯:張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