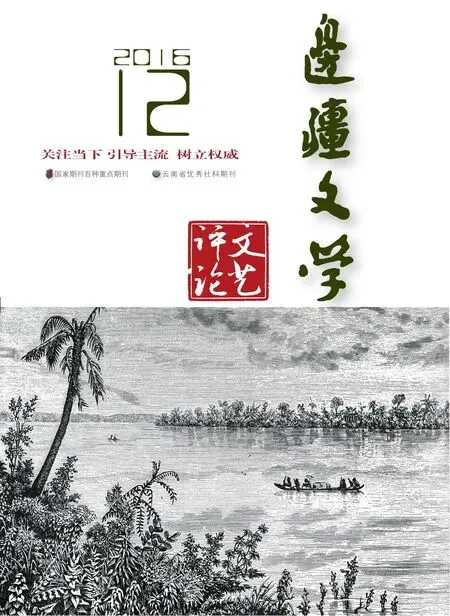素心相對如秋水
——評黃玲散文集《從故鄉啟程》
◎黃鳳玲
素心相對如秋水
——評黃玲散文集《從故鄉啟程》
◎黃鳳玲
散文是所有文學形式中最具包容性的文體。既可以鏈接歷史,緬懷和追思;也能夠指涉日常,會悟和備忘。甚至接納和伸展人們內心最為隱秘或最難放置和類別的情感,故而,散文當是心靈最親密的盟友。
新世紀以來有“一代之文學”之稱的“新媒體散文”,可謂是喧囂熱鬧的大眾寫作,其中被評論者稱為“調皮的”、“可愛的撒嬌”的“小女人散文”以女性作家群體寫作的姿態亮相。這是一些“當窗貼花紅”的梳妝派散文,她們的語言精巧、圓膩,洋溢著詩意的優雅和輕盈的喟嘆。一些女作家力圖規避“女性寫作”的焦點徽號,希翼穿越性別之門重歸傳統,回到生活和寫作的內部。
云南作家黃玲就是一位對生活和寫作有著深刻洞察力的作家。2015年12月出版的散文集《從故鄉啟程》,值得文壇再一次將目光投向新世紀的女性散文寫作。
一
在無數春秋中磨礪而日益通達的黃玲對于生活有清晰而堅定的認識:不要執著地試圖從生活中趕走悲劇,喜悅和苦難原本是生活的存在方式,生命的感悟不僅來自偶然的驚奇或嘆息,更來自尋常日子的平淡和平凡。故而,在貌似酷烈偉岸的歷史浪潮里,她并未竭力贊頌那些高居神龕的孤獨與喧鬧或者黑鐵般冰冷堅硬的規律,她始終關注的是那個熙熙攘攘甚至渾渾噩噩的凡塵世界。在她看來,那每一處歡笑,憂傷,狡黠或迷糊都是這塵土飛揚的俗世導向存在的一個隱秘通口。真正驚心動魄的生活,不是把自己的手腳釘在十字架上的悲壯,也非擂響震耳欲聾的羊皮鼓的決絕,而是行走在庸常日子不卑不亢的坦然接納和耐心等待。“平庸瑣碎的日子像一張網,鋪天蓋地,無處逃遁。生命存在有千百種方式,鶯飛草長、鳥語花香是存在,在塵世的奔波努力、精神的掙扎煎熬又何嘗不是更真實的存在。”[1]
黃玲的散文,也涉及大話語模式的理想構筑,有史學厚度和精神力度,但并未沾染上所謂“文化大散文”一般寫作者的虛空和偽飾習氣。在《大美云南》里,有“我們的祖先元謀人”,有云南歷史上可考的最早統治者“滇王”,有民國“云南王龍云”,作者在敘述中,既沒有一味墜入歷史事件的泥淖,用那些冰冷僵硬的數據和史料將閱讀者攻陷,也并非完全摒棄歷史的記憶,任由思想如柳絮般四處紛散。而是以歷史為經緯,在作者沉實簡潔的敘述中,閱讀者不斷地發現歷史煙塵中的偉大人性和精神光暈。
《云南王皮邏閣》一文,作者首先以一個類似戲
曲主人公“亮相”的方式開場“為首的是一個高鼻大眼、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他身披黑色披風,腰挎長劍,以好奇的目光打量著這座莊嚴華麗的帝王之都。他就是來自遙遠的西南地區南詔國的第四代王——皮邏閣。”接著輔之以史實和傳說,在對皮邏閣的文治武功的敬仰之余,也對英雄建功立業中難以遮蔽的殺戮和慘烈予以甄顯,讓閱讀者感受到歷史之火的炙熱和文學之血的感傷。
云南歷史深遠悠長,這片神奇的土地歷代上演著豐腴紛繁的文史掌故。黃玲的目光不僅凝視著那些偉岸、壯闊的身姿和功業,還以一腔深情和知識分子的敏感融入那些沉潛在民間的歷史碎片和生活的獨特段落,將人物的精神信息從凡俗市井中剝離,讓人心的溫度在晦暗的時間之沙中光亮。
同是云南歷史上的布衣名士,明代的蘭茂和清朝的孫髯翁都有頗具傳奇的經歷。如何撰寫他們各自鐫刻汗青的獨秀人生呢?這是對作家的深刻考驗。以學者內涵入主作家身份的黃玲,并沒有試圖去“糾正歷史”或“歷史正解”,表現出了有別于歷史學家的細致的詩情。《布衣奇才蘭茂》行云流水般講述蘭茂一生在醫藥、音韻、文學、教育方面的成就,文言跳脫,語氣輕捷松弛,對蘭茂這位民間傳說中被點化成仙的奇士的生平,可謂是面面俱到又點到為止,毫無贅文。
人們相對熟知的《大觀樓長聯》作者孫髯翁,作家將“聯圣”生活的窘迫與精神的孤傲在《一代名士孫髯翁》一文中鋪陳開來,以同為文化人的心性氣質感同身受,孫髯翁“睜了眼看世間”的清醒和“布衣終生心懷天下”的尊嚴,作家行文相對沉緩,節奏控制均衡,再現了“蛟臺老人”存在旅程和精神印記。更具宏闊、深沉的文化散文特質。
當然,如若以魯迅先生的“史識”觀要求,在獨具個人眼光和精神敏感的“歷史理解”方面,黃玲散文的自覺程度尚有提升空間,對于蘭茂和孫髯翁的評析還是多受制于公共層面的歷史結論。如此,不僅縮小了作者情感張弛的彈性,也使作品的精神指向性過于單一。
而《狀元和狀元府》躍出了歷史浩渺的樊窠,打破時空和事件的桎梏,以現時人的不斷重疊的視角去打量那些細碎的史料,用心底溢出的情愫去擦洗時光的陰翳,尋找到歷史本初的意義。在親歷者李喬的臉上,我們看到作家沉思的表情“但只要閉上眼睛,屏退世俗的喧嘩,便似乎可以讓思維穿越時空。”此刻此景,閱讀者與作家、親歷者、人物化身為一人,“所謂精神的傳承,其實就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教育和影響,它會一代代地繼續下去。”作家以“借景移情”的方式,將游弋于蒼茫流光里歷時性的人的心靈品質和精神追求聚集起來,讓閱讀者在文字中觸摸到了歷史遠處的余溫。開創了散文寫作中視角構筑一種新的發現方式。
二
在文學中,詩歌和散文,最能呈露作家的心境、才情,因為寫作者將自己的心緒、個性、人格,甚至生命直接凝練成了作品,可以說是言心合一,身靈皆融。在這樣的文字中,映射到閱讀者心里的,既有美的迷醉,情的動蕩,更有真的喜悅。應用在人生上,是物來順應,斟理酌情,不落偏見的悟會。當然,這樣的寫作對于作家確是一種真實的考驗。
作為一個對美有著異常感受力的作家,黃玲懂得,最好的事物并不來自美學理論家們喋喋不休的爭論和闡述——它不會隱藏——值得珍視的是人們普遍可以看見的美,它坦現在日光之下,無需證明和解釋。
在《故鄉在遠方》如江河般暢流的敘述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叫做米田塊的小小地方的似水流年,而是以“故鄉”為綢帶的舞者,于歷史敞亮奔流的物質和精神世界或沉郁或飛翚的呈現。在這個日趨匿名化、表面化和短暫化的城市社會關系中,故鄉成為承載黃玲精神密度最大的無形符號。在她由心而生,以情入筆的文化記憶和歷史想象的雙重復沓之下,人格印記的城市和鄉村傳遞著作家流動疏離又富足融合的生活跡象和文化模式。故鄉對于作家來說,是另一個我的存在。
筆者認為,作家的價值在于:一直向前走,并適時與讀者分享自己新近的印象。黃玲的行走是一生的,從故鄉米田塊啟程,鎮雄、昭通、玉溪、昆明、北京、首爾……“只有心知道,漂泊是為了更好地回望,遠行是為了思念的綿長。”[2]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說:“我發現弄文學的人向來是注重人生飛揚地一
面,而忽視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沒有這底子,飛揚也只能是浮沫。”[3]對此,黃玲的體驗是真切又富有新意的。
作家在不斷的行走中,對于人生世相始終保有一種獨到的新鮮觀感,進而以一種別致的形式將觀感表現出來。這樣,予讀者來說,便是由探趣而生欣喜的閱讀歷程了。正是因了這心意相通的密切關系,讓閱讀者不再莽撞輕佻地嬉戲消遣文字,而是將精神凝注于作品的幽深密道,細細品悟作家筆下最具生命力的“靈韻”。 總讓人想起易卜生的話:“我寫作不是給男女演員提供角色,我寫作是描繪人間肖像”。
黃玲不想讓偽裝和虛榮擱淺了讓心靈返鄉的訴求,那片生育她的土地是她的喜悅和痛苦,也是她信仰不熄的所在。在這個物質不斷擠壓心靈,游移成為現代生活常態的當下,無處安放的鄉愁也在故事的敘述中自然彌散開來。她率性而又節制的語言,包含著智慧的張力和生存的敏感,揭開經驗的暗處,舒展出一個抵達內心而又照亮存在的視野。
在《舷窗人影》中,黃玲并不打算穿著由崇高的詞語織就的朱羅衣,以一種形而上學論者的形象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作出一副漂亮美觀的象征姿態,化身佯裝掌控“真理”的哲學家。黃玲的家鄉風硬草枯,生活在這個土地上的人們勤儉辛勞。然而,嘈雜簡陋的日子并沒有消解她對歲月和希望的虔敬。她享受著一種平等地行走在人群之中的安靜,但也不懼怕以自己的名義發言:“只是歷史的碑石上只刻下高原漢子的雄姿和豪飲,女人則被擠壓成小小的符號和斑點,如明月旁邊的星星,永遠閃著微弱而沉默的光,襯托著廣袤的天空。”[4]
他們這一代人是有著“良心”信仰的自覺者,他們愿意俯身傾聽人們的話語,但并不戴著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的面具出現,因為她深諳萊蒙托夫詩歌中的那個世界:看一看你的周圍:人群在日常的路上歡快地走動/在他們那節日般的臉上憂慮的痕跡隱隱/卻沒有一丁點兒眼淚來大煞風景/但在他們當中未必有這么一個人/不曾被嚴厲的拷打折磨/在皺紋過早爬上臉上之前,不曾有被損,也沒犯過罪行。
在《人生屐痕》里,作家很清晰地懂得,個體要在人群中方能找到生存的意義和價值,伶仃一人,缺乏同情與互感,生命便無所發現和寄托,必然會頹頓枯滅。文章中,敘述者身處人群之中,心像安恬,精神平帖。她不哀嘆、不怨忿、不疏離,也不恐懼或對抗眾人,她在歡笑或者沉默,坦率純真,灑落雋逸。在從容清緩的敘述中,你會感覺空氣變得干凈,呼吸更加有力,胸腔充盈著源源不斷的真氣,這樣的文字是健康的,洋溢著陽光的暖意和月華的深邃。
三
我們身嬰世網,物質世界在不斷捆縛和擠壓我們的靈魂,流水線使城市僵化,機械無情至生活窒息。自我與他人之間,愈是隔雜疏離。在人們游離自然太久之后,便少有自在舒適之感,因為困頓和苦痛,時有嘆聲和哀吟。其實種種,皆是違離自然之心生出的文化病之故。中國古之自給農耕文化,易自足于圓融安然美觀,多忽略奮然向前的活動之美。鄉村代表著自然、孤獨和安定,它能給予那些奔赴城市,緊張、血氣、忍耐、掙扎的生命以養息精力的補救,記憶中的長林豐草將漸漸恢復他們的意志和氣魄,進而重返活動的城市。
讀《大美云之南》時的感覺最能療救此種文化病:從“我們的祖先元謀人”之首,閱讀者便開啟了云南浩如煙海的的塵封歷史之旅,出發在即,海上卻是重重密密的云氣,不免替船長暗暗憂心。但隨著風帆高揚,船上的游客時時發出驚呼,茫茫大海上的霧靄漸漸消散了,眼前越來越清晰,猛地發現,眼前聳立著一座島嶼,哦,不,是不斷閃現的島嶼,它就在那里,輪廓分明,穩固如山,讓人不由正襟危坐,心生敬意。待得胸中熱浪稍減,已是輕舟萬重山了。亂花漸欲迷人眼,空氣中若有若無的濁酒沁馨,耳邊隱隱傳來雪山戀人的情歌……
黃玲良好的道德感和倫理精神,帶著知識女性的柔情和祝福,世間的人,在她,都應是值得憐憫和同情的對象,所以,她并未將筆觸滯留在表面化的憂憤和感傷,于是她綿密從容的敘述里自然彰顯出一種張弛有節的優雅風度。
“莫名其妙地喜歡車站的氣氛,這是人生的一個中轉站,人們在這里暫時停留,然后各奔東西。……
‘在路上’是一個真正的詩人無法逃避的宿命。它意味著心靈永無居所,故鄉永遠在遠方。”[5]這樣的文字讓我們在黃玲的散文中常常能夠發現她對人類的普遍憂思,帶著知識分子與生俱來的堅韌和悲憫,在對生命和大地的敬畏與尊重里,書寫著一個文化學者的哲思追求,在她懇切與熱忱的個人化情愫的流淌過程中,堅執著一種超越性的精神氣質。
黃玲的散文中確有一種“人性的溫情”,不過,這樣的溫情并不是刻意過濾了生活的惡劣和人生的嚴酷的,她也并不把流逝的光景和孤僻的鄉野當作規避世俗的田園凈土,故而,即便是以個人經驗為中心的人事和生活,在她充盈著善意和溫情的敘述中,自有一種冷峻的沉思表情面對現實的困境展開精神的追問。“心靈的救贖無人能夠援手,只有依靠自身的掙扎前行。……當我們在樹林間穿行的夜晚,如果用心傾聽,一定能聽到被風雨摧殘、被刀劍損傷的傷口發出的呻吟。”[6]她時而將自我“準客體化”,將自我置于主體意識所觀照的對象之位,讓寂寞打開心靈深處的眼睛,赤裸的世界在和作家對話,平凡的生命放射出神秘的光:
“遠處有幾聲蟲鳴唧唧,絲絲涼意從草叢上掠過,月亮似一冰輪高懸藍空。升得高了便變得更加清明一些,環繞的云卻又讓它往朦朧的方向靠近一些。在異國他鄉,竟然會有這樣的奢侈,一個人獨享一個空寂的校園,獨擁一輪高懸的明月。天地間只有我和月相對,校園白日的喧嘩都隨風而去,剩下一片空空的靜。”[7]此中空無所有的心境最是難得,也最為廣大,最是真切。
四
在筆者看來,好的作家,即使外像冷烈清嘉,內里則應是絲綿著了胭脂般,易滲化開去的。黃玲便是這樣的作家:學者的克制和冷靜讓她保持著理性和思辨的頭腦,柔軟溫潤的心靈則讓她的文字不被市儈裹挾,潛藏的激情為閱讀者創造了一個充滿了骨血的抒情世界。
黃玲的散文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出發,自給自足又誠實內省,素顏布衣的文字空間時時隱隱閃現人性內在維度。婉約恬淡中自會建構生命的高度。當然,我們時而也會不經意中觸及到一顆因悲傷而沉思默想的靈魂,在《親情如水》系列文章中,作家纖巧如絲的情緒顯得特別敏感,仿佛一張精致古雅的瑤琴,輕柔悠緩的憐愛拂過弦梢,那么細膩誠摯又精妙絕倫,既樸實無華,又異常動人。
在這組文章中,黃玲不僅仰臉抒情感懷,更多的時候是俯首注視腳下的大地,用文字去撫摸故鄉的每一棵草,每一粒石子。沉著的情感像水一般緩緩滲入那片現實的土地。此刻的黃玲是最為坦然和自信的。因為她敢于面對真實的自己和厚實的親情,以及那些在時代的隙縫里艱難生存的掙扎痕跡。在這樣的散文中,黃玲表現出了作為小說家的優勢——散文中有人物。《外婆的村莊》的外婆,豁達仁慈,“喜歡穿一身陰丹藍長衫,包一塊青絲帕子”,“用一只磨得锃亮的銅水煙袋,咕咕咕地噴吐煙霧”;隱忍堅強的母親,“獨自一個人進城去醫院生孩子”,“用微薄的退職金在村里建了一棟草屋頂的房子”。最真切的“人物”便是“外婆的村莊”,這是一個彝族村莊,這里的人們“皮膚要黑一點,鼻子要高一些”,這里請畢摩“轉嘎”,這里彝人的姑娘“出嫁了也是自己的姑娘,過年是要叫兄弟牽著馬接回來過年的。”黃玲的敘述是樸素安穩的,沒有驚天泣地的故事,沒有浪漫感傷的情結,但那份深沉內斂的情感在作家貼心蘊藉的文字里,像晨霧中的蓮花,靜謐卻又動人心魄。
《舅舅·舅母》里,大舅舅“不多言,不多語”,但孝順善良,讓晚年的外婆“有了一份相對安穩的生活”,盡享天倫之樂;而對罹患“肺結核”奄奄一息的女兒竭心盡力的救助,以及對五個兒女公正與憐憫實難平衡的煎熬,凸顯出大舅舅父愛的博大與深沉,思之令人動容。還有整組文章中“母親”的形象,忙碌的母親,絮叨的母親,無奈的母親,衰弱的母親,倔強的母親,委屈的母親,達觀的母親……偉大卻不無悲劇意味的母親,來自那些人們習焉不察的生活細節,當我們凝神回望時,漸行漸遠的“母親”便仿佛迷蒙的煙雨翠湖,“它是一只眼睛,一只令我肝腸寸斷的眼睛,照著心靈的角落,讓我不得安寧”,空留悵惘和無聲的嘆息。這樣的散文身體是在場的,正因為身體的在場,它才能使作家心靈的律動成為真實,
進而支撐起散文內部一以貫之激情流動的河床和精神發現的天空。
好的散文,讓閱讀者放下書卷,仍然會有惦念的感覺。黃玲的散文,讓我心生惦念,而不想張揚。這不可言說之境,還是留給讀者自己去體味吧。
五
黃玲的散文語言沒有絲毫的乖戾氣,文章始末都保持著她所特有的那種透視力和平衡感,堅定明敏,帶著作家自己的溫度和氣息,宛若清冽的溪水般的珍貴品質,像極了一位技藝臻于化境的古琴高手,她的文字里高山流水,云卷云舒,早已是目送歸鴻,景近心遠了。
作為高校教授的黃玲恰如古時得科第之士人,生活無憂無迫,人事寬馳。故能于閑定生活中收拾精神,既不耽于道家空寂和放縱之弊,也不致似墨家因太過艱窘而計較功利,總是行走在人生篤實中和儒家正脈之道,沉實淡宕的藝術人生幾可達朱子所說的“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的敬靜之境了。如此安閑、平易的心態最適宜散文寫作。
《旅韓日記·摘錄》是類于閑筆式的散文,這類散文歡迎閱讀,可以品味,但卻并不適合闡釋的。然而,往往正是這類文章最得散文精髓。沒有擺出作文的故意姿態,也不在結構上用力過度。看似隨意,但卻并非信馬由韁,漫無邊際;長長短短,當行則行,當止則止。《韓國校園的吃》、《去教堂,看別人信教》、《一個人的中秋》、《參觀韓屋》,一掃所謂“為遠方寫作”的空洞和平庸之風,將目光收回,關心“糧食和蔬菜”的日常,從生活的細節中去關注個體經驗和精神發現,淡定的情理中不乏有深度的哲思。
散淡而不紛亂,自在而不蕪雜。這樣的文字既是作家敘事的話語表情,也是心靈風度的外化。讀來舒適自然,卻能讓閱讀者興味盎然。見修養,也見性情,這便是很好的散文。
寫作散文最為可貴的是心靈的真實和樸素,切忌矯飾裝腔。那些恢弘的感嘆和過度升華只會讓散文陷入空乏、酸腐的陷阱,從而喪失散文“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的本性。黃玲筆下的生活,并非張愛玲歡喜的“像鈞窯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么滯緩,帶著悠悠的模糊的幸福。是清楚明晰的,但也不是雪白十字布上的挑花,那么嬌靨醒目。倒像是趙延年先生的木刻畫,有一種昏濛的愉快和屋瓦上白霜樣的清爽。
我想,這本書如果以顏色來作比,那應該是藍色的吧,深深淺淺,明明暗暗的藍。明亮的藍像地中海般的晴朗和莊嚴;幽深的藍則似星空的夜,靜謐深邃。
【注釋】
[1]、[2]、[4]、[5]、[6]、[7],黃玲,《從故鄉啟程》,2015年12月版,云南人民出版社。
[3]來鳳儀,《張愛玲散文全編》,1992年6月第一版,浙江文藝出版社,112頁。
(作者系昭通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萬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