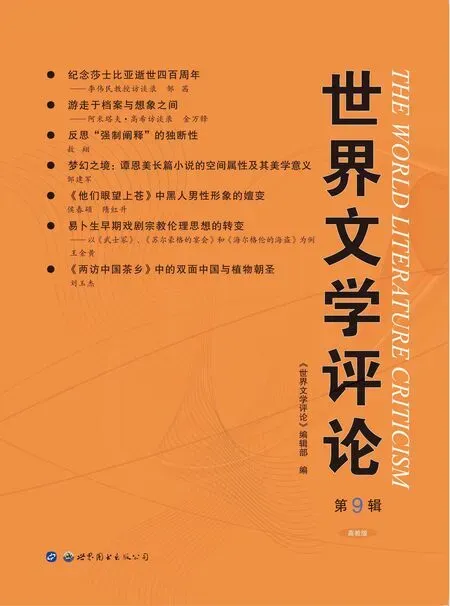地方與鄉土對于漢語詩歌的意義
——熊明修先生訪談錄
葉雨其
地方與鄉土對于漢語詩歌的意義
——熊明修先生訪談錄
葉雨其
葉雨其( 以下簡稱“葉”):每一個詩人都有不同的歷史,也有不同的創作環境,這對于其詩歌創作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不知你是在什么情況下開始詩歌創作的?
熊明修(湖北省麻城市作家協會主席,以下簡稱“熊”):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初中畢業后就在家務農。一邊讀書一邊干農活,在農村度過了很長一段日子。那時,只要有書我就看,什么書都讀,犁田打耙插秧什么農活都做。1972年冬,新洲倒水治理工程開工,生產隊以“抓鬮”的方式決定工地人員,我抓到了“8”,于是我們小隊連我8個農民,隨同三萬水利大軍上了倒水工地。工地上以團、營、連、排為建制,各自都分得了挖土筑堤的艱巨任務。當時因讀過初中上工地的農民很少,很快我被團部領導發現是個“人才”,馬上被抽調到團部搞宣傳。已入隆冬,北風呼嘯,天氣寒冷,人站在工地,只要一會不動,腳下就結冰。我的宣傳任務就是拿著土廣播在工地發現好人好事,現場編詞進行廣播表彰,鼓舞民工士氣,掀起你追我趕的施工高潮。每天至少要現編二三十段詞,而且要求,通俗易懂,還要有一些韻味。那時工地上,我走到哪里,民工的吆喝聲就在哪里,施工高潮迭起。1974年10月,碧綠河水庫示范工程開工,我又被抽到工程指揮部去搞宣傳。這次宣傳除了帶領一個流動宣傳組在工地做流動宣傳以外,還負責編印《碧綠河工地戰報》,主要側重詩歌創作,為工地創作了《工棚夜校》、《出擊》、《抬石工》等一大批詩歌作品。水庫竣工后,我作為一名電站工人留在水庫工作。1984年,我從碧綠河水庫調入縣水利局工作。在水利局工作期間,接受了成人大專中文專業的學習,加入了縣文化館群文創作這支隊伍,進入了正式的鄉土詩歌創作,分別有《棉花姑娘的剪影》、《配就配在豐收年》、《師徒話明天》等詩歌作品在“兩刊一報”上發表,即:省刊《布谷鳥》,縣刊《麻城文藝》,地級報《黃岡報》。當時能在這些報刊上發表作品的人不是很多,我很快就成為全省的重點業余作者。我是這樣寫《棉花姑娘的剪影》:
晨風吹落草葉上晶瑩的露珠
擺滿村沿的營養缽吐一片碧青
吱呀呀門半開,閃出健美的身影
象一群鳥兒飛出了青青的竹林。
和煦的晨光點亮黑色的眼睛
絢麗的朝霞染亮素潔的衣裙
姑娘們手捧棉苗,忙著栽種
她們把理想交給了每一抹初萌的綠茵。
整枝的剪子是剪春的燕子
薅草的鋤頭是繡花的銀針
挑糞的扁擔是織錦的金梭
翠綠的新毯呀,是獻給秋姑娘的禮品。
為了這每一片葉子,每一抹綠茵
她們的深情注滿每一串腳印
滴滴汗珠灑落在五彩繽紛的圖案上
呵,雪白的新棉該是汗水的結晶?
款款而來的金風攜來豐收的喜訊
一車車新棉,惹一路贊聲
問姑娘,喜交新棉有何愿望
——愿天下不再寒冷!
我的詩發自本然,寫的是鄉土。很快就引起了縣文化館館長和輔導干部的重視,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把我送去參加各種培訓班的學習。當我因工作任務繁雜,一度曾放棄寫作時,縣文化館那位館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的詩歌寫得這樣已經不容易了,如果你放棄了,那實在可惜。”也就是這句話,30多年來,我沒有一天與鄉土詩離開過,在鄉土中尋找創作的價值與意義是我的生命所在。
葉: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創作目的,有的為了愛情、有的為了故鄉,有的為了國家,有的為了民族,有的為了為自己生命價值的實現,有的為了自我表現,有的為了與他者進行交流。不知你開始創作詩歌的目的是什么?后來有無變化?
熊:與詩歌創作相系的時光,從二十冒頭轉瞬便是花甲之年了。用文學評論家林卓宇先生的話講:“每一個執筆者因為寫作而感到幸福。在漫長的過程中,生活在低處的肉體,已然獲得了一個行走在高處的靈魂。”我高興地祝福自己,也高興地祝福詩歌。因為寫詩而快樂,因為寫詩而幸福。也許這是我創作詩歌的主要目的之一。至于有無變化?詩是精神的支柱,詩是塵世的安慰。我以為,只要涵養、培育、發掘那顆生命的初心,并用詩的語言去擦亮它,就能平息自己的徘徊和焦慮,撫慰心靈的創傷,讓生活在曲折中得以繼續。我在與小說家趙金禾先生討論我的鄉土詩時,我對趙金禾老師說,古而有之的鄉土田園的詩歌情緒,一直掛在我的生命樹上。用“犁”寫詩,犁耙飄香,犁耙的光芒照耀鄉土,也照耀自己。做一個鄉土詩的守護者,永遠是我的夢想。“取材”于鄉土到“再造鄉土”也許是我的一些變化。借鑒鄉土,讓詩歌回歸家園。也許,這是我寫詩的目的之二。詩評家趙國泰早期在評介我的鄉土詩時,就講:“詩人對鄉土的關愛至深至切,蛙聲乃至春野,都一并成為詩人所歌吟的藝術圖騰或精神居所。”當我的大型文化組詩《苦人溝》公開發表后,文學評論家夏元明教授在第一時間作出了反映,他認為我過去寫鄉土,更多的是“取材”于鄉土,雖然也不乏“再創造”,但出發點還是“還原”。《苦人溝》則不同,“現實”在這里被充分意象化,成為構建詩人第二精神故鄉的原材料。詩人不再致力于還原于“材料”的真實,而是以“真實”的生活細節,進入一種更高層次的精神建構。
葉:麻城是三楚大地最重要的一個地方,不僅是黃麻起義的發生地,出現了許多有名的將軍,并且在歷史上還是“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的中轉站,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四川人,現在都稱自己是麻城人。前不久我也專門去到麻城訪問,有了一個很有意義的尋根之旅。我想問的是,你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麻城人,你認為麻城這一片熱土,在環境上與文化上具有什么特點和優勢,你在自己的詩歌里是如何表現的?
熊:麻城位于湖北東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別山中段南麓,處于武漢、鄭州、合肥三大城市合圍的中心位置。版圖3747平方公里,人口120萬。麻城的歷史悠久,七千多年前即已開發,春秋為楚地,名柏舉,因吳、楚在此大戰,后稱為柏舉之戰,而名重青史。秦屬南郡,漢為西陵。后趙石勒部下麻秋筑城始得名為麻城。這是一片被革命烈士鮮血浸潤的紅色土地。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八軍在這里誕生和發源。1927年11月,震驚全國的黃麻起義在這里爆發,此后二十多年,麻城的革命火種經久不息,革命紅旗高高飄揚,全境13.7萬余人犧牲于戰火,6萬多優秀兒女參加了紅軍,在腥風血雨的戰爭年代,鍛造出了王樹聲、許世友、王宏坤、陳再道等41位新中國第一批授銜的將軍和128位省部級高官。在這塊紅色土地上,大別山紅色旅游公路貫穿境內,山重水復的交通樞紐滿載人們對將軍故里、紅軍烈士之鄉的崇敬之情。“人間四月天,麻城看杜鵑”又成為這個城市一張新的名片。作為一個鄉土詩的寫作者,我自然敬重這片充滿血性的熱土,更敬重這片熱土上的厚重人文。僅從我最近出版的詩集《鄂東的風》和最近創作的大型鄉土文化組詩《鄂東,鄂東》中可以看出。意屬于情,心屬于身。我的親親故土因為鄂東的存在而存在,我的精神家園因為鄂東的追尋而追尋。我不敢說我的這些詩有什么清新奇崛,但我敢說,那種似無還有的人文氣息,那種讓人迷惑的鄉土韻味,在詩中國的歷史長河中,雋永悠長而難得一見,均可清晰地呼吸到那來自鄂東深處的芬芳。當詩人海子帶著“麥子”而去,詩人饒慶年長眠于“山雀子銜來的江南”的詩中,作為湖北的詩歌評論家、《當代作家》詩歌編輯的趙國泰先生深感痛惜,也為鄉土詩的后繼而十分焦慮。然而,當他讀到我的鄉土詩時,不禁欣然在同期的編后寫道:“當代鄉土詩,尤其是鄉土詩中的江南曲,是文學佳釀中的極品。然曾幾何時,個中名士或金盆洗手,或人已云逝,令人有繆斯道斷、美薪不繼之嘆。誰料想,自然實驗田拱出一抹新綠,無聲地驕人。我讀過熊明修的全部來稿,發現他一旦屬思鄉梓,涉筆故土,便珠走玉瀉,不擇地而出。這是另具一樣文化只眼的品鑒,是業經現代藝術整飭的天籟。”也就是同一個時期,我發表在《寫作》雜志上的鄉土詩《鄂東鄉村》也得到了武漢大學周文斌教授的認可。他說:“從《鄂東鄉村》這首小詩中,有心的讀者不難發現,作者是一個打心眼里熱愛鄂東鄉村的人。他渴望擁抱鄂東鄉村的一切,對鄂東鄉村的田園風光和牧歌生活奉獻出了自己的熱忱和祝福。在他由衷地發出一聲聲贊嘆和感喟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心境的滿足與悠游,而正是這種滿足和悠游的心境,才使得他筆下的鄉村生活從一種單調沉滯的苦澀變成一種超脫渾然的和諧。這種和諧,是不可能對生活淺嘗輒止就能獲得的,它有賴于作者敏銳的觀察力和深刻的生活體驗。”古往今來詩人興會神到的鄉村,一直是田園詩永不枯竭的題材,但只有那些將自己浸漬于其中的詩人,才能體味到鄉村的神韻,也才會呼吸到一陣陣親切可人的生活氣息……不謀而合的是,原《人民日報》大地副刊部主任、著名詩人石英老師以《淳樸的、機智的、優美的……》為題,為我的詩集《走向春天》作序時寫道:“如果以我早期讀到的熊明修與他的近作相比較,就不難發現他的詩歌創作正進入一個更加成熟期。隨著詩人視野的擴大和閱歷的增長,他的詩作的生活面和題材也在不斷拓展。對于一個成熟的作家和詩人說來,這也是必然的趨勢。但就目前來看,他的‘拿手活’似乎仍在他寫家鄉這片他鐘愛的圣土和家鄉人的風采上。給我的感覺是:他一動鄂東就來神兒,一動黃麻就出彩。他是擁有‘一招鮮’的優勢的。”也許,這正與著名詩人謝克強先生所言:“對土地深沉的歌唱,對當前鄉土重大生活改變的吟贊,對鄉親們思想感情的揭示和開展,所有這些構成了熊明修的鄉土詩,而這些鄉土詩里,自然有著濃郁的泥土氣息,飄散著泥土的芬芳,體現出人文的關懷。”
葉:一個詩人總是離不開自己的傳統,正如艾略特所曾經指出的那樣,如果傳統是一條河流,那每一位詩人作家都會時時處于河流之中。麻城在歷史上出現過許多重要的人物,當然原來的麻城比現在的范圍要廣得多,深厚的地方文化傳統是遠近聞名的。我想問的是,地方的文化傳統,包括地方傳說與民間歌謠,對你的創作產生的影響何在?
熊:傳統文化于我的詩歌創作而言,給予了無盡的滋養。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詩歌發生了劇烈的變革,各種思潮、流派的紛至沓來。詩歌主流的奇崛險怪和口語泛濫的多樣形態,真的讓我們這些耕耘在鄉土的寫作者一籌莫展,望而生畏。面對如此紛紜繁復的情況,我是明智的,清醒的,我了解并明白自己所面臨的魔幻世界。當然,我了解得更多、明白得更透的還是我腳下的泥土、胸中情愫。我甘愿受地方文化與民間歌謠對我的熏陶。那些生冷硬僻、莫名所以的高談不屬于我,那些口水遍地、傖俗無聊的絮叨也不屬于我。只有這泥土、這泥土所催發的情愫才是我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于是我就寫出了《犁耙飄香》、《太陽出山》、《鄂東的風》、《鄂東,詩草》等,一批批飄著田園清香的詩篇。多年來養成的閱讀和寫作的習慣,特別是我對鄉土詩歌的重傾態度,使我一直堅信好詩總是珍藏在民間。而民歌又是民間廣為積累的優秀產物,從民歌方向去讀,從民歌方向去寫,也許這正是地方文化傳統與民間歌謠對我的詩歌創作帶來的影響。很多讀者和詩評家說,我的部分詩類似于陶淵明。當然,這是指題材、領域上的。所不同的在于側身于田園的一種角度。著名戲劇作家熊文祥先生讀過我的詩后,他說我是一位典型的鄉土詩人,從詩集《犁耙飄香》中,讓人聞到了一股特別濃郁的泥土的芬芳,這是在同類詩人詩作中是不常見的。從作者的第二部詩集《太陽出山》比起《犁耙飄香》來看,其藝術思維和技巧駕馭,明顯地向前跨進了一步。許多詩句,都是苦心思慮的結果,無不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一直在書籍中旅行的黃岡師院中文系教授陳明剛先生在讀了我的詩集《太陽出山》后,給我寫了一封長達五千字的書信。他說:“我知道你生在鄉村,長在鄉村,鄉村是你的沃土;你在鄉村這片沃土中扎下了深根,樹長再高,枝葉再繁茂,你永遠離不開鄉村這片沃土;你永遠親近鄉村,血肉相連的親近;你永遠凝望著鄉村,雕塑般地凝望;你擁懷黃金有價而情無價的鄉村情感,這鄉村情感是有清純如畫的真誠和毫無雜質的圣潔。因而,你永遠歌吟鄉村,你‘殫思極慮’的詩筆永遠不停歇地抒寫著鄉村的山溪、蛙聲、水渠、河灘、陽雀、羊群、春秧、冬麥、柿子、棉花、桑林、老樹、河上柳、皂角夾……永不停歇地抒寫著鄉村的屋檐、小窗、竹笠、石凳、吊鍋、炊煙、老屋、草堆、山路、田埂、水塘、渡口、鳥窩、老井、草坪、籬笆、瓜架、木榨、水車、背簍、山歌……永遠不停歇地抒寫著鄉村人插秧、麥收、放牧、燒荒、出嫁、趕年、扎草把、田邊奶孩子……可以說,如此林林總總的鄉村自然景觀,人事風俗構成了你詩作的主要意象,這些意象是鮮明的,它既有寫真的現實情狀之細致‘反映’,更有寓意豐澹的抒情與象征。幾乎每一首詩中都有令人一詠三嘆的雋語佳句,她們的意象是那么美麗,色彩是那么明麗,風韻是那么清麗,境美,情美,語美,音美,讀來滿口生香。說真的,讀你的詩時,我聯想到了陶淵明的《歸田園居》、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王維的《鹿柴》、《山居秋暝》,聯想到了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春》等等。憑心而論,如果沒有歌吟田園與回歸自然的執著追求,又哪里有永居后人心中的陶淵明、孟浩然、王維之詩神形象呢?如果沒有傷心的‘雨巷’、沒有‘濃得化不開’的情愫,又哪里有后世人永遠懷戀與研讀的戴望舒與徐志摩呢?因而,我私下里想,如果沒有你的這‘的確多了的細膩的純情’,便沒有了《太陽出山》那感人的藝術魅力,便沒有真正的詩人熊明修……”我之所以引用陳明剛教授鼓勵我的大段書信,我只想說明傳統文化對我產生的影響和關懷。著名詩人向以鮮曾經說過:“讓珍貴的火種得以孕育并最終成就燎原之勢的母體,不是別的,正是我們偉大的文化傳統。文化傳統就像是一條永恒的河流,它不僅流淌在大地之上,也流淌在我們的血管之中。傳統從來就是活的,傳統從來就不會死去。”
葉:在這樣一個網絡發達、交通發達的時代,許多人都成為了“世界人”,不接受外來的資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一個中國詩人,具有深厚的中國背景,也可以寫出重要的作品,但外來的文學也不可不接受,不可能不受到影響。我想問的是,外國文學或文化,對于你的詩歌創作產生了何種影響?
熊:我對外國詩歌讀得不多,對西方詩歌各種流派的風格及表現手法等也是從各種詩刊上的評論文章中略知一二;如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艾略特的《荒原》,龐德的《在一個地鐵車站》等。我對他們詩歌中的病態頹廢的情調、意象疊加非邏輯性和肢解語言的非結構性的表現形式和手法不太認同。我認為詩歌就是生活,它來源于生活就應該植根于大眾,其生命歷程也走到了盡頭。當然,西方現代詩派詩歌中的好的表現形式和手法,我們是應接收的。泰戈爾是我最喜歡的詩人,他的《新月集》我最愛讀。我小時候愛讀,現在依然愛讀。《新月集》看起來像一個個零散的故事,但是串聯起來,便共同展現了泰戈爾一顆純真的童心。他用天真稚嫩的孩童語言,寫出了自己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強烈地表現出自己對美好生活的熱愛,對自然的熱愛,對家鄉的熱愛。同時,他那許多廣為流傳的詩句,就像一杯杯香茗,品上一口便久久縈繞在心頭。他的詩歌哲學和詩歌世界給了世人許多智慧,許多啟迪。我在創作《還鄉》這首小詩時,多少得到了一些啟發:“看見炊煙/說那是/長在鄉村肚臍眼上的/臍帶//看見老人的胡子/說那是/還鄉草//還鄉,還鄉/老人一生/在墳地里找親人/在酒杯里找故鄉。”燃放著熾熱的精神火花,照亮讀者的心,也是泰戈爾的詩作讓人銘記的一個突出點。
葉:近代以降,麻城這個地方出現了許多將軍,有的是國民黨的,有的是共產黨的,在歷史上還出現了諸多進士與舉人。這些歷史人物在對你的成長和創作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熊:回顧歷史,麻城這片紅色的土地,又是一片造就文學精英的沃土。據縣志記載,麻城歷代文人輩出,學者眾多。僅明代麻城出文武進士136人,全國少有。近數百年來,蜚聲全國著述甚多的就有劉諧、劉天和、劉侗、熊吉、梅之煥、熊調鼎、毛鈺龍、董天策等百余人。如劉諧著有《西湖律韻》;熊調鼎著有《經古文解釋》、《二十一史提綱》;劉天和著有《問水三集》、《幼科類萃》;梅之煥著有《中丞遺文》、《中丞遺詩》;劉侗著有《名物考》、《帝京景物略》;熊吉著有《柏舉文集》等等,其巨著三百余卷。更有趣的是,麻城人唐洪洲部督閻伯嶼,在滕王閣上宴請賓僚,引出王勃《滕王閣序》傳為千古絕作。還有杜牧、蘇軾、李贄、李世民等歷史名人墨客都曾在麻城生活過較長一段時間,在麻城留下了很多傳世之作,真可謂群英薈萃,雅士云集。身為熊吉的第十五代嫡孫,充盈著親切、崇敬的心情,我認真拜讀了《柏舉文集》,翻開書稿,我立即被這部“百科全書”深深吸引。前面說過,我干過各種農活,吃過多種苦頭,雖然沒有寫出詳盡的農耕記錄,但鄉村田園自然成了我成長的背景,它告訴了我的出處和來歷,我想創作詩歌的那種沖動來源于鄉愁,我認為最具生命力和震憾人心的是鄉土文學。能讓我的靈魂安靜下來,駐足下來的地方只有故鄉鄂東。最近,《長江叢刊》副主編、著名評論家劉川鄂在該刊刊首語中寫道:“地域性寫作一直是新時期以來中國作家以顯示個性的方式。莫言的高密(筆者添加)、閻連科的河南鄉村、賈平凹的商州、方方的武漢、林希的天津、野莽的烏江流域、聶鑫森的湘潭古城,展現了新穎的藝術視角和獨特的地域文化景觀,是新世紀成功的地域文學書寫。”我斗膽地補充一句,還有熊明修的鄂東鄉村。我并不是刻意要夸張自己,1984年我開始創作詩歌,先后在《人民日報》、《詩刊》、《當代》、《中國藝術報》、《文學報》、《星星》、《綠風》、《詩神》、《詩歌報》、《長江文藝》、《寫作》、《芳草》、《特區文學》、《南方日報》、《中國詩歌》、《詞刊》等省級以上一百余家公開刊物發表詩作兩千余首,其中寫鄂東題材的詩作達一千余首,并多次獲獎。已公開出版《犁耙飄香》、《太陽出山》、《走向春天》、《鄂東的風》等五部詩集。先后有張志民、白航、張同吾、石英、丁永淮、趙國泰、謝克強、劉醒龍、江岳、黃運全、劉川鄂、洪燭、夏元明、陳明剛、王浩洪、湯天勇、宋長江、陳炳健、何存中、袁敦文等作家、詩歌評論家,十分肯定我的鄉土詩歌創作的方向,主動寫我的詩評,絕大多數至今未曾謀面。武大主辦的《寫作》刊物,曾一度開辟專欄,連發6期刊載我的詩作,并加中文系教授老師的評點,作為范詩在校園推介。2012年,湖北省作協、湖北日報社聯合在《湖北日報》上開辟了《湖北作家寫作家》專欄,小說作家何存中先生以《飛翔在鄂東天空的布谷鳥》為題,記敘了我的鄉土詩的創作。“就像一只催春的布谷,熊明修飛在鄂東的天空,一直寫詩,一直歌唱。那是一塊紅色的土地,出將軍,出凡人,也熟莊稼。倒水河的水與大別山的太陽和月亮,輪回地照著他的親人,也照著他的村莊。熊明修如今到了耳順之年,套用偉人的一句話:一個人寫幾首詩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寫詩。在湖北、在全國有幾個人能一輩子寫詩歌呢?人生易老天難老,不老的是智者頭上的天空和胸中春日的情懷。”沒進過大學門的我,寫出的詩歌作品能夠走進校園,成為中學生和大學生的讀本,深感不安和慚愧。身上沒長翅膀,卻說我飛翔在鄂東的天空,我深感幸福和驕傲。文藝創作一個更為根本的規律,那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使我獲得一種無窮的精神力量。
葉:當代中國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詩人,有的人認為當代漢詩直追唐宋,當然有的人也認為詩發展到漢詩已經沒落了,寫詩的人多而讀詩的少,甚至有的人認為新詩不如舊詩,當代人所寫的舊詩讀者面更廣。你對當代中國的詩歌創作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什么樣的建議?
熊:對當代中國的詩歌,時下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聲音:一種聲音認為詩歌看似極其繁榮,活動眾多,但實際上已經遠離了讀者和時代;另一種聲音認為當下中國詩歌與現實緊密聯系,詩人與時代的關系密不可分。我個人認為,時代在前進,詩歌在發展,按照“雙百”方針的精神,中國詩歌總的趨勢比過去好,其形式多樣,其路子寬廣。但與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要求相差甚遠。“三大病象”的問題在詩歌創作中同樣存在:一是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二是抄襲模仿、千篇一律;三是像機械化生產、快餐化消費。其俗癥,也就是兩個字:浮躁。前年春節期間,在美旅居的作家趙金禾先生遠隔千山萬水,通過互聯網與我聊起中國詩歌和我的詩歌,讓我十分感動。他說:“我不寫詩,我讀詩,讓自己不失寶貴的詩情詩意和詩風。中國詩人們的行情我是略知一二的。他們走得很遠,遠得我看不見他們的首尾,即來處和去處。這似乎符合詩人們說的:詩是新鮮感覺,意象紛呈,是感覺與意象的復合體。這似乎是詩的定義。我說不。”他說:“定義可以有多種,多種可以并存,無須相互廝殺。我以為重要的,是要來自生命的因子。讀你(熊明修)的詩,我是放棄定義的。是用生命去觸摸的。我拿到了你的詩情的鑰匙,觸摸到你‘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的生命之核,那就是你的生命體驗,生命激情,生命表達。我找到了我的詩觀印證。”他說:“什么是文學作品的深刻?其中也包括詩歌,我們抵達的是,寫出生命的意味,寫出心靈的意味,寫出精神的意味。我贊同專家們對你(熊明修)詩作的那句詩意評論:從泥土拱出來的綠色詩行。我只是補充。你不能不承認你離開鄉村久矣,你的詩魂卻守在那里。”我也認為,詩歌離不開生活,生活里充滿詩情。生活永遠是我的老師。離開生活,詩評無從談起。離開生活,詩歌無從寫起。離開生活,詩人無從當起。離開生活寫詩的人,也許一時能得到奉承,但最終會遭到人們的唾棄。詩人無情,生活會更加無情。假、大、空不是生活,做文字游戲不是生活,故弄玄虛更不是生活。生活在哪里,詩歌就在哪里。有時候,我不禁暗自發問,你把詩歌編了一期又一期,有一首能讓人們記住的嗎?你把詩歌寫了一年又一年,有一首能與廣大讀者產生共鳴嗎?別怨讀者無情,首先是自己無義。回歸生活吧,詩歌在呼喚,讀者在呼喚,人們在呼喚。說實在話,中國是一個以農業社會為主的國家,是一個犁耙養活的民族。唐詩和宋詞無時不在訴說,鄉土田園詩有著廣闊的歷史風景和深厚的文化積淀,詩人展示自己對故鄉的思念、憂傷或摯愛,卻是令人感動,令人遐思,與人共鳴的。詩講意境,意境則由詩人的心境產生。一個有文化擔當、有使命感的詩人,絕不會只關在自己的小屋里淺吟低唱,他的目光總是在關注著民族的興衰,民生的疾苦,他會以閃爍著智慧光芒的文字,去提煉一個幽美的意境,去升華一個大家關注的話題,去開拓一片新詩的天地。“根在魂就在/魂在花就開”(熊明修《姐兒門前一棵槐》)。鄉土,是我生命的搖籃,除了足跡,還有終生隨行的影子。今后,不管是身體流浪還是精神放逐。它都將是我文化還鄉和衣錦還鄉的歸屬。我的生命注定珍貴,我的歸屬注定光華。
葉雨其,武漢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文學地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