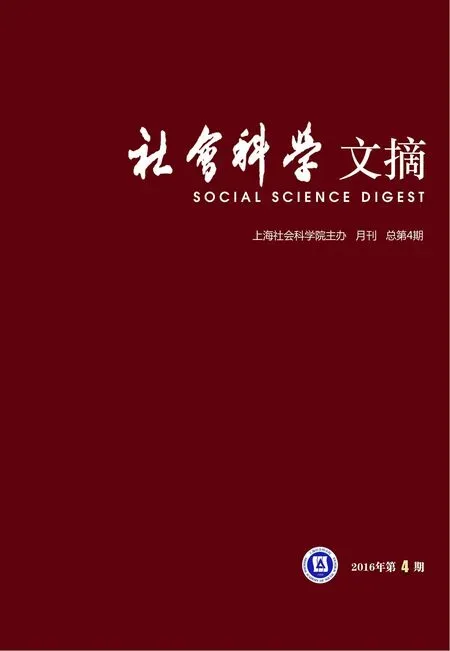對戰爭的倫理約束
文/何懷宏
對戰爭的倫理約束
文/何懷宏
我們慣用的對戰爭的道德評價一般多采用“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術語,即從戰爭的性質著眼,但我以為籠統地說“正義戰爭”或“非正義戰爭”有產生歧義的可能,即不易落到實處,不易具體和明確地評判、衡量與檢驗,甚至有可能為發動不當戰爭提供借口。為此,我嘗試先對戰爭倫理進行一些分類,直接和明確地提出一種“對戰爭的倫理約束”,這種約束貫穿于從開戰、作戰乃至到戰后的全過程,要求政治家和所有相關人不僅考慮參與戰爭的動機、意圖和信念;也考慮戰爭的行為、過程和手段;乃至考慮戰爭結束之后的相對直接和比較長遠的后果。在這一過程中,我也會討論為什么要特別強調對戰爭的倫理約束,以及這種倫理約束何以能夠成立。
戰爭倫理的分類
對戰爭的分類我們可以分成兩個方向來進行,一是形式的分類,借助于西方中世紀哲學家和法學家提出的分類框架,可以將戰爭倫理主要分成兩類:一類是戰爭權利的倫理,或者說開戰倫理;一類是戰爭行為的倫理,或者說作戰倫理。沃爾澤在他近年出版的《論戰爭》中提出,還可以再增加一個戰后倫理或者說戰爭責任的倫理。這是一個有用的涉及形式范疇的分類。
還有一種分類則是具有實質性觀點和立場的分類——將戰爭倫理或對戰爭的道德態度分成以下三種:一是現實主義;二是和平主義;三是正義戰爭論。有些學者或再加上一種:軍國主義。
我現在想嘗試一個新的分類,即將有關戰爭倫理的觀點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將“現實主義”直接稱之為“非道德主義”;第二類是將“和平主義”更貼切地稱之為“絕對和平主義”;第三類是將“正義戰爭論”改稱為“倫理約束論”。至于“軍國主義”,也可將其歸于一種“非道德主義”。
在流行的分類中,一般也是把“現實主義”視之為在戰爭中的非道德主義,即認為戰爭就是戰爭,戰爭與道德無關,戰爭中的任何暴行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甚至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發動戰爭也是可以的。“現實主義者”認為這就是人類的本性,就是權力的本性,戰爭的本性,政治權力必然要擴張自己,必然要爭個你死我活,面對殘酷的戰爭沒有道德存在的余地。
但是,我雖然認為這種觀點的確對現實的人性和權力相爭的一面有清醒的認識,但將之概括為“現實主義”卻不甚貼切。“現實主義”還有更廣闊的內涵。上述觀點適合于被稱之為“極端的現實主義”或者這個領域內的“非道德主義”。首先,許多被認為是、甚至就自稱是國際政治領域內的“現實主義者”的人,并不否認在權力和戰爭的領域內仍然有道德的存在,并不否認對戰爭仍然必需有倫理的約束。比如著名的現實主義者摩根索所提出的“政治現實主義六原則”中就有兩條涉及到道德,他說政治現實主義深知政治行動的道德意義,只是認為普遍道德原則不可能以其抽象的普遍公式應用于各國的行動,但又認為普遍道德原則必然滲透到具體時間地點的情況中。
同樣是著名的現實主義者、甚至是帶來了20世紀美國戰爭倫理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向的愛德華·卡爾也認為,說政治人只追求權力,就像說經濟人只追求利潤一樣,只能是一種虛假的論斷。政治行動的基礎必須是道德和權力的協調平衡。他認為,以為先追求權力,然后道德自會接踵而來,這只是一種幻想;而以為先堅持道德,然后權力自會接踵而來——這同樣是一種幻想。兩種幻想同樣是危險的。當然,這些現實主義者在權力與道德的關系中更為強調權力而非道德,但的確還不是一種完全否認道德意義的非道德主義者。
其次,我想無論持哪種觀點,我們都必須先有一種現實感,必須對人性和權力的本性有一種清醒的認識,這尤其是對絕對和平主義的一個必要調節。談到“和平主義”,也有一個容易導致誤解的問題就是,以為持其他戰爭觀點者不想追求和平。而一般被用來舉證為“和平主義”的觀點,其實常常是一種比較絕對的和平主義。比如托爾斯泰的和平主義,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抵抗,反對一切的戰爭,期望可以通過所有人一致的精神抵抗和感化能夠最后解決問題。但這看來是對人性估計過高,對現實過于樂觀了。像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反抗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面對的其實還是和平時期中相當講究規則和法治的對手,若面對戰爭中直接就要殺戮的暴虐的敵人,看來是很難奏效的。而持其他的直接肯定戰爭倫理觀的人們,比如“正義戰爭論”者或“倫理約束論”者,他們期望的目的也可以是說為了和平。甚至非道德主義者也不反對和平,只是希望一種能給他們帶來較大利益的和平。乃至一些軍國主義者,也還是會打著“和平”的旗幟作為幌子。
最后談到“正義戰爭論”或“倫理約束論”,這實際是“極端現實主義”和“絕對和平主義”之間的中道,即它有一定的現實感,不是一概反對暴力和戰爭;但也認為應當,也是能夠對戰爭加以必要的道德評價和倫理約束的。但我更傾向于使用“倫理約束論”而非“正義戰爭論”的概念來表述這一觀點,其理由主要是擔心“正義戰爭論”的說法容易造成誤解,甚至容易給戰爭開方便之門。茨維格曾經如此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說:“那是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是各國人民一味相信自己一方事業的正義性,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判斷一場戰爭是否正義也是不容易的,它還涉及到戰爭的目的和意圖,而真實目的和意圖總是容易被掩飾的。總之,對戰爭性質是否正義的判斷有可能會面臨相當復雜的情況,而主張對戰爭的倫理約束則是相當明確的。它涉及所有各方的所有行為而非意圖。它更像是一種普遍客觀的邊際約束,即附著于所有的行為,可用來判斷所有的行為。
此外,我這里還想引用18世紀一位瑞士法哲學家瓦特爾的觀點來說明一下我想用這一改稱來強調什么。他在1758年出版的《萬國法》中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因為所有的交戰國都認為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那么他們之間誰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為沒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調節戰爭的規則。這種規則,他稱之為“國家之間的志愿性法律”。
然而,戰爭的本性是要盡量擺脫約束的。但現實的戰爭都可能存在約束。對戰爭的約束主要有三種,一是來自雙方力量的不足,這種力量的不足會約束戰爭的擴大和發展;二是來自經常是作為戰爭決策者的政治家,如果這些政治家是有理性的,我們也可以說這種約束是來自理性;而第三種約束則可以說是來自道德,或者說來自戰爭決策者和參與者的道德良知、社會的道德輿論。的確,在戰爭中,這方面的約束看起來是相當微弱的,但這也正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
總之,僅僅“正義戰爭”的道德評價術語是不很明確的,不易落實的,而且容易產生歧義,甚至帶來危險。相比之下,將一種“倫理約束論”結合于我們前面談到的“開戰倫理”“作戰倫理”和“戰后倫理”的三個方面,則可以將問題細化和明確化:即首先要嚴格考察介入一場戰爭的理由,應該說這種理由除了保護生命之外幾乎不可辯護——由于考慮到戰爭的原始本性就是殺生,戰爭一定會帶來生命和財產的巨大損失,那么,除非它能夠直接保護和減少這種損失,那就幾乎沒有什么其他的理由一定要介入戰爭。其次,即便是為了止殺而不得不介入的戰爭,也還要考慮作戰倫理即手段的倫理,這方面應該是有明確的國際法可循的,比如不可屠殺平民,不可殺害俘虜,等等。最后,還應考慮戰爭之后的結果——如果它并不能夠帶來穩定的和平,反而使戰后的國家或地區繼續有各種暴力的肆虐,甚至造成比戰前還要嚴重的生命財產損失,那么,這樣的戰爭也是全然不可取的,而在戰爭之前或之初決策者就應該充分地考慮這種結果,承擔起自己的道德責任。
戰爭倫理何以能夠成立?
探討戰爭倫理的確還有一個困難的問題就是,戰爭倫理何以能夠成立,或者說,為什么戰爭應當接受某些基本的道德約束,其理由或根據何在?這是一個需要回答非道德主義的挑戰的問題。
我們在此從沃爾澤的論證開始。沃爾澤提出了一個“戰爭的道德現實”的概念,他認為即使在戰爭中,絕大多數人還是想合乎道德地或看起來合乎道德地行動。我們之所以如此因為“我們的爭論和判斷經過長時間的重復之后形成了一種現實,我想稱之為戰爭的道德現實——也即,道德語言所描述的或必須使用道德語言才能說出的全部經驗”。并且,他相信“我們對道德詞匯有十分普遍和穩定一致的理解,因而共同的判斷是可能的”。
但是,這種“十分普遍和穩定一致的理解”到底包含什么內容,沃爾澤謹慎地語焉不詳。他在后來的《論戰爭》一書中倒是談到:“為什么發動戰爭是錯誤的?我們都知道答案。因為戰爭要死人,而且常常死傷眾多。”也就是說,戰爭的惡就在于它的殺人,甚至是以殘忍的方式不分對象地殺任何人。而我們可以從中引申出來的一個正面的原則看來就是保存生命。
于是,如果說在“正義戰爭論”方面我們可以考慮比沃爾澤的觀點更謹慎地退后一步,在論證戰爭倫理的可成立性方面我們或許可以比沃爾澤更前進一步,即直接提出保存生命的原則作為給戰爭加以倫理約束的理由和根據。在這方面,我想先重新訴諸近代經典。
盡管格老修斯也主張正義戰爭的理論,但他是比較明確地將保存生命的原則視作是正義的基本標準的。他認為自然法是正當理性的命令,甚至上帝自己也不能對它加以任何改變。而按照自然法的規則,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為了保全我們的生命和身體完整,那么這戰爭就是正當的,而如此理解戰爭的話,正義的戰爭也就主要是一種保衛自己和同胞的生命的自衛戰爭。但是,他也指出,這一原則是要建立在公平的理念基礎上的,即不是單方面地強調一方的生命而是各方的生命,要區分攻擊與自衛。
我們在格老修斯的論證中,可以發現一種訴諸普遍性的論據。他推崇古希臘赫西俄德的一句話:凡是在許多國家中普遍流行的任何看法都必定有某種共同的基礎。這種普遍性或許可稱之為是一種訴諸經驗的普遍性。而康德的“可普遍化原理”則可以說是訴諸一種形式或邏輯的普遍性。即幾乎所有人都希望生而不是希望死,如果你不想自己無端被殺,那么,你也就不應該這樣殺死別人。如果允許非保護自己生命的殺人成為一條普遍法則,即人人都可隨意殺死并未威脅到自己生命的人,那么,最后就是人類毀滅,進而取消殺人本身。
關于生命原則的內容,我認為基本的保存生命的規范原則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是對生命的直接保障,即不殺害生命,不壓制生命,使生命有安全感;第二是滿足生命的需求,供養生命,使生命能夠維持下去。而從作為普遍價值的生命原則來說,第一層含義是人的生命本身是寶貴的。所謂“本身是寶貴的”,就是說,它不是作為手段和工具的寶貴,而是作為“自在自為的目的”的珍貴。這就引申出它的第二層含義,既然生命是本身寶貴,那么任何一個享有生命的人,任何一個活著的人,所有的人,他們的生命都是同等寶貴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應當受到尊重和珍視的。第三層含義就是,保存生命、尊重生命這樣一個原則,在次序上是最優先的,優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則。
應用到作為政治單位,主要是國家之間的戰爭上來,則可以說,生命原則主要是強調其第一方面即對生命的直接保障,即不殺害無辜者的生命。在訴諸戰爭的時候首先要考慮這是否是為了保全生命的目的,并的確能達到減少生命損失的結果;在戰爭進行的時候則考慮區分對象,包括不以極端殘忍和侮辱的方式殺害哪怕是對方的軍事人員。至于第二方面即保障生命的基本物質需求方面,則主要是一國政府對本國公民的責任,但是,在戰爭中也要考慮通過對一個城市或地區的長期圍困和封鎖使對方居民大量死亡是否符合倫理的問題。就像羅爾斯所言,在正義原則中直接地提出保障基本權利勝過試圖間接地達到這一效果。
戰爭與倫理都是古老的現象,但廣義的戰爭無疑比倫理還要古老。因為它還可以追溯到動物界,而倫理只是隨著人類的意識、理性產生才出現,是特屬于人的現象。在這一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戰爭倫理是人性對動物性的一種約束,道德理性對原始攻擊沖動的一種約束。戰爭的原始本性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搏斗和相殺,而且是一種大規模的、成建制的群體搏斗和相殺,至于它光榮或偉大與否,乃至正義與否,則是第二位的屬性。戰爭不僅難以在人類生活中絕跡,甚至有時造成好的結果,但它歸根結底并不是人類的光榮。
問題還在于,戰爭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或者說,某種合力會使本來沒有戰爭意愿的人們和國家卻卷入了戰爭,甚至是狂熱地投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一個范例。它是一場本來所有方都不想真正打的戰爭,最后卻打得無比慘烈和持久。所以,對戰爭的性質和邏輯應該有一種自覺意識,對戰爭的倫理約束更應該有一種自覺意識,這樣才能比較好地防患于未然。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國家再大再強,也不能好戰,好戰必有災殃,甚至國家危亡。同時,忘戰也是不可以的,這不僅指一個國家要強固與本國相稱的國防,還應該指同時還要討論和研究戰爭及戰爭倫理,以保證只涉入正義的或者說自衛的戰爭,且在卷入戰爭之后也總是正當地進行戰爭,并隨時爭取和平的機會,擔負好戰爭的“善后”。而在聚集反戰和正義戰爭的力量方面,學者和知識分子還有一種特別的責任。即他們不僅應該深入地研究戰爭倫理,而且應該努力去影響社會的輿論。
茨維格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深刻教訓就是,戰前各國的巨大經濟和科技成就普遍地使人們陷入盲目的樂觀,人們也不了解戰爭究竟意味著什么,在他們看來,戰爭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奇遇。這樣,由于沒有什么思想準備和防范,當大戰突然降臨的時候,無論在德國,還是在法國、意大利、俄國、比利時,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就都順從地為“戰爭宣傳”服務,而不是與之斗爭。敵對雙方的所有國家的群眾幾乎都一度陷入亢奮的狀態,于是,大戰的車輪就開始毫不留情地碾過無數生命的血肉之軀了。
所以,為了保存生命,預防戰爭,在和平的時期就應該保有對戰爭、尤其是約束戰爭的倫理的深入研究和廣泛傳播。就像政治權力必須約束和馴化一樣,對戰爭這一暴烈的權力更應該時刻保持警惕,仔細研究和實踐如何約束和馴化戰爭,尤其是約束那種將對人類生命造成最大危險的戰爭形式——總體戰的戰爭形式。
【作者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摘自《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