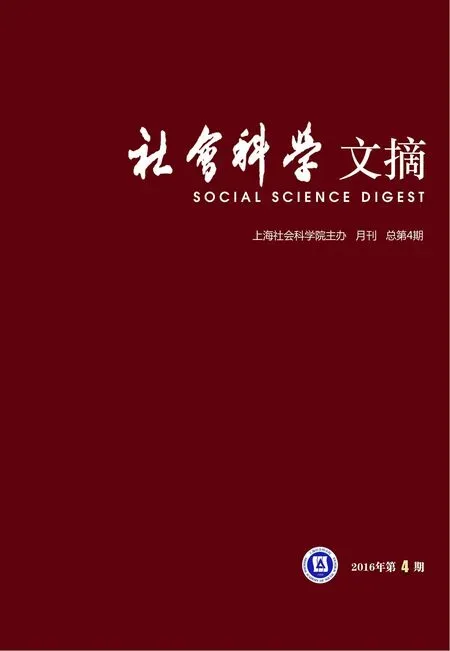革命與“革命敘事”
文/馬勇
革命與“革命敘事”
文/馬勇
在古代中國,“革命”似乎并不是一個“好詞”。《周易》所謂“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總覺得有強辯意思在。
直至孫中山出,“革命”漸成為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新詞。這是孫中山的偉大貢獻,也是后來國民黨史觀建構的基礎。由此檢視國民黨主導編寫的近代史,革命,包括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都與正統史學漸行漸遠,清政府、滿洲貴族承擔了中國落后的原罪,孫中山、革命黨成為救世主,晚清敘事逐漸脫離正統史觀、王朝史觀,敘述主線不再以統治者活動為主,革命者、造反者成為新歷史敘事中的主角。
“革命敘事”之主旨
“革命敘事”與20世紀全球范圍民族主義運動相吻合,因而迅即獲得知識界認同,并將朦朧中的“革命敘事”體系化,填充豐富內容,至民族主義革命高潮,一個全新的近代中國歷史敘事大致成型:
由1840年英人以炮火擊破中國的門戶,強行輸入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中經英法聯軍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聯軍之役、日俄之戰、日德之戰,一直到1925年“五卅運動”以來,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沙面、漢口、九江等處,對于中國民眾的屠殺,是一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族史。
這是李大釗1926年一篇文章的描述。他認為,這一條浩浩蕩蕩的民族革命運動史的洪流,時而顯現,時而潛伏,時而迂回旋繞,蓄勢不前,時而急轉直下,一瀉千里。它的趨勢是非流注于勝利的歸宿而不止。簡明地說,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只在壓迫中國民眾的帝國主義完全消滅的時候,才有光榮的勝利的終結。
李大釗并不是專業歷史研究者,他的看法只是一種天才般的猜測。近代中國的主題,就是怎樣接納不期而遇的“西方”,進而就是中國能否向西方學習,步入全球一致的發展軌道。回望19世紀全球史,整個東方實際上都面臨著相似的問題。作為先發的西方國家,他們來到東方固然不是傳教士自詡的那樣拯救人類,傳播福音,而資本的輸出、市場的開拓,才是那個時代的主題。但是,因而將這些活動一概歸為帝國主義,李大釗的朋友胡適就很不贊成。胡適竭力反對革命的路,反對革命史觀、“革命敘事”,主張以漸進的改良推動中國轉型。
漸進改良或許也是一條可以選擇的路,這是嚴復、康有為、章太炎以來知識人最期待的路。但20世紀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無法讓中國循序漸進。期待往往落空,期待改良,卻引來了革命,革命成為20世紀中國的主旋律。這是歷史事實。
接續李大釗思考近代中國歷史敘事的有華崗。華崗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同時兼具知識人情懷。華崗的一系列作品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建構近代中國“革命敘事”的典范之作,回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所走過的道路,一方面強調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另一方面承認帝國主義的進入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既為中國造就了一個全新的民族資產階級,也為中國革命準備了無產階級。
基于這樣的理路,華崗那一代傾向“革命”的史學家,大致接受了共產國際、斯大林、布哈林對中國革命的分析,以為伴隨著西方勢力東來,中國由封建社會漸漸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何干之、李達、瞿秋白、張聞天、呂振羽等,都有比較細致的論述。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話語環境中,近代中國幾乎所有事件、人物,都有了很不一樣的含義。比如,1898年發生的變法與政變,原本只是中國資產階級要求權利分享的和平變革、改良主義,與革命毫無關系,但在“革命敘事”者筆下,戊戌變法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改革領導者沒有群眾基礎,沒有革命意識,只是幻想、祈求點滴改良,因而注定失敗。
“革命敘事”之定型
20世紀30年代,“革命敘事”還屬草創階段。各方面知識人對這個敘事充滿懷疑,胡適說:“革命論的文字,也曾看過不少,但終覺其太缺乏歷史事實的根據。”梁漱溟不認同胡適對“革命敘事”的責難,但對胡適“反對今之所為革命,完全同意”。他也認為“革命敘事”過于“輕率淺薄”,“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說的濫調”,并不足以解釋近代以來的中國問題。
“反對就是興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草創期的“革命敘事”能贏得學界大佬反對,而且還有那么多的認同者、追隨者,足以顯示“革命敘事”的生命力,意味著具有修正、完善,逐漸定型的前景。
使“革命敘事”最終定型并一直深刻影響到今天的,有很多因素很多人,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的理論思考是一個方面,延安、重慶知識界的討論也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是范文瀾、胡繩,他們兩人將這個模式漸次用于近代史實證研究、具體表述上,用事實證明了“革命敘事”的效用。
范文瀾為章太炎再傳弟子,具有非同尋常的學術基礎,1940年初抵延安,正值整風運動,重新認識中國歷史和中國革命。因此契機,毛澤東建議范文瀾編寫一本適合一般干部閱讀的中國歷史讀本。
毛澤東的建議為范文瀾提供了一個巨大的用武之地。1941年,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出版第一卷,他計劃用三卷篇幅重寫遠古至當代中國歷史。按照計劃,第三卷為鴉片戰爭至義和團時期的歷史,后將第三卷單獨出版,定名為《中國近代史》。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充分吸收了學術界研究成果,尤其是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但其主要觀點,與蔣廷黻存在巨大差異。
與蔣廷黻的看法很不一樣,范文瀾認為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飽受侵略的苦難,中國由此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境地。痛定思痛,回顧往事,范文瀾以為鴉片戰爭就是英國資本主義強國殖民擴張的產物,英國殖民者利用資本主義先進技術,駕駛著新式運輸工具,帶著可怕的殺人武器,還有那精美且廉價的紡織品,前往遠東開辟市場。他們不允許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中國閉關自守,不允許中國孤立于資本主義世界之外。
范文瀾贊揚林則徐的抵抗,推許林則徐是“中國封建文化優良部分的代表者”,是清代晚期維新運動思想先驅,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這個評價與蔣廷黻的看法正好相反。蔣廷黻說林則徐不肯犧牲個人清譽與時人奮斗,是一個在道德上有虧欠的“偽善者”。而范文瀾認為林則徐相信民心可用,因而愿意抵抗,愿意將英國勢力拒之門外。
對于蔣廷黻稱許的穆彰阿、琦善等外交家,范文瀾始終不愿認同,以為這些人的妥協就是投降,就是賣國,就是與外國勾結。在范文瀾看來,假如不是穆彰阿、琦善等人妥協主義影響,中國就不會在鴉片戰爭中失敗。所以,范文瀾一直以為穆彰阿、琦善、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等投降派阻礙了中國的進步。
與范文瀾稍有不同,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所要著重說明的,“是帝國主義怎樣在中國尋找和制造他們的政治工具,他們從中國的反動統治者與中國人民中遇到了怎樣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義者對于帝國主義者的幻想曾怎樣地損害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等”。
胡繩認為:“為了說明只有徹底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下解放出來,只有徹底地打倒作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的中國反動階級,中國才能有真正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經濟的發展,為了警惕帝國主義會用這樣那樣的方法來破壞中國人民的革命,為了指出中國的民族獨立只有依靠無產階級的領導而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的領導來實現,作者當然不需要在寫作時絲毫離開歷史事實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歷史事實中的本質的、規律性的東西,越是能說明問題。”這是作者的自信,也是那個時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最普遍的看法。
范文瀾、胡繩的研究,將“革命敘事”定型化、經典化,必須承認在1949年之后,“革命敘事”取得了壓倒一切敘事模式的絕對優勢。這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后果——那就是一個多元的歷史理解漸行漸遠。
其實,從大歷史敘事說,革命與改良相對而存在,都是人類歷史上不絕如縷的事件。但社會進步主要憑借改良,也就是中國老話說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人們通過適度保守、適度變革,推動社會進步。但有些時候,革命又不得不發生,沒有革命的推動,舊勢力不愿自動退出,舊體制無法改良。革命,是一種非常手段,又是社會進步過程中不得已的手段。因而,革命與改良在歷史上往往交替發生。一個理想狀態,大約像馮友蘭曾經期待的那樣,大致維持革命與改良的適度緊張與平衡,而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中國就是舊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現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舊邦的同一性和個性,而又同時促進實現新命。我有時強調這一面,有時強調另一面。右翼人士贊揚我保持舊邦同一性和個性的努力,而譴責我促進實現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賞我促進新命的努力,而譴責我保持舊邦同一性和個性的努力。我理解他們的道理,既接受贊揚,也接受譴責。”(《馮友蘭學術論著自選集》)
“革命敘事”是一個偉大創造,居功甚偉。但一定要謹記“革命敘事”與“現代化敘事”,以及其他一切敘事模式一樣,都是為了“說話方便”,并不代表歷史本身,更不是一切歷史。一個多元開放的歷史敘事,依然需要學界同仁不懈努力。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摘自《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