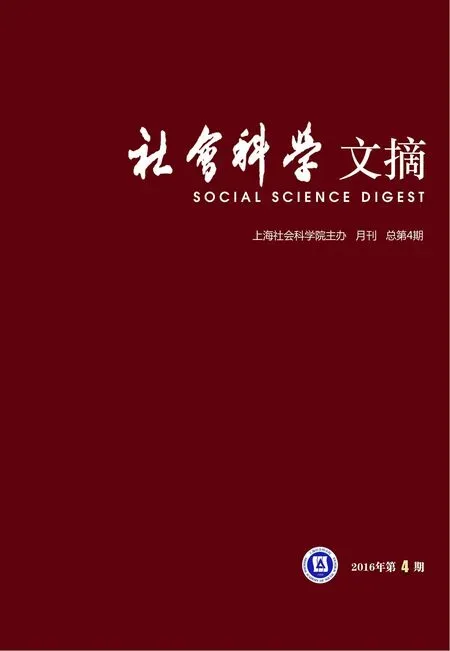危機與危機利用:日本侵臺事件與李鴻章和淮軍的轉型
文/王瑞成
危機與危機利用:日本侵臺事件與李鴻章和淮軍的轉型
文/王瑞成
1874年日本侵臺事件引發的危機,與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等重大事件相比,只能算第二層級的沖突事件,因而,在中國近代史的表述中影響力有限。相關研究也是以事件史方式來呈現危機及危機應對的過程,以及這一事件的結果及其影響,并做出評價。但我們在全面了解相關史料之后,會發現存在兩套史料,一為清廷與疆吏圍繞危機應對的往來公文,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有比較完整的收錄;一為李鴻章和朋僚之間的信函往來,反映并非事件主要當事人的李鴻章在其中活躍的身影,這在新版《李鴻章全集》中有比較全面的體現。兩套史料呈現出圍繞事件臺前和幕后兩類史實,一是中外沖突事件及其應對,另一類是李鴻章為中心的政治勢力利用危機實現淮軍和海防體制轉型的活動。
日本侵臺事件臺前幕后:李鴻章的雙重角色
我們從官方文件中可以重建日軍侵臺事件帶來的危機和應對全過程。這一危機應對是依據正式體制的常規應對方式和應急舉措來進行的。常規體制下的應對是皇帝和軍機處,總理衙門,福建和沿海督撫及下屬官員和軍隊組織系統的動員和布置。但王朝還有常規體制之外應急機制,即欽差大臣。通過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建立起以欽差大臣為中心的應急機制,承擔主要責任。
常規體制性應對首先是按屬地原則,即事件發生地官員具有守土之責,應當承擔主要責任。因而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和福州將軍是直接當事人。而海警特點是一處有警,處處設防,因而,沿海督撫也是事件應對相關方。這一常規應對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體制的例行公事。如各地包括福建的布防都是臨時敷衍,表面文章。因而,欽差大臣沈葆楨才是危機應對的關鍵角色,應急機制才是主要的應對機制。在交涉方面起主要作用的總理衙門,也是王朝舊體制之外建立的應對外部沖擊的新機制。可見晚清面對外部沖擊,舊的常規官僚體制已經失效,只能依賴應急應變機制來應對外部沖擊帶來的危機。這一危機應對體系中最關鍵的是皇帝和軍機處主導的中樞,總理衙門和欽差大臣。總理衙門和欽差大臣分別負責交涉和防務,中樞雖然主要是采取總理衙門和欽差大臣的意見,在決策方面已經不具主導性,但可以起協調和整合作用。最終似乎是依靠這一危機應對機制化解了這場危機。
從官方正式文件反映的內容看,李鴻章在這次危機應對過程中只出現三次,一是報告日本侵臺消息,二是針對沈葆楨調北洋三千洋槍隊、南洋兩千洋槍隊的請求,李鴻章上奏提出異議,改派淮軍唐定奎部赴臺。三是朝廷要李鴻章利用輪船招商局加快公文傳遞速度。而在中樞要求沿海一體籌防之后,李鴻章甚至沒有回應。如果按照危機應對和事件史來看,李鴻章似乎無足輕重,起碼不是事件主角。但這只是臺前一面。李鴻章留下的大量信函告訴我們,這一階段李鴻章異常活躍,在很大程度上驅動事件朝著自己設定的方向轉換。其重點不在危機應對,而是危機利用。
1874年日本侵臺這一事件發生前,李鴻章已經因天津教案引發的危機,被朝廷緊急調任直隸總督,并成功將淮軍一部帶往天津,變為海防力量。但事后淮軍主力仍面臨裁撤壓力,海防體系也空虛無力。李鴻章充分利用日軍侵臺造成的危機局面,將閑居徐州的淮軍精銳調往臺灣海防前線,將參與西北平叛的另一支淮軍精銳力量撤回沿海布防,成功實現淮軍從國內平叛前線到海防一線的全面轉移。同時,利用危機,制造輿論,推動以李鴻章為核心的海防體制的形成。這是李鴻章和淮軍從內部平叛之戰時體制向應對西方的海防體制轉型的關鍵一步。
日軍侵臺危機爆發和善后這一時段,李鴻章密集聯絡協調的“朋僚”達20余人。按實現其意圖來梳理,可以區分三條線索。圍繞淮軍重新安排,主要涉及接受淮軍調遣的欽差大臣沈葆楨和閩浙總督,與駐徐州淮軍和駐陜淮軍調遣相關的兩江總督、江蘇巡撫、陜西巡撫、淮軍將領等,促成淮軍調遣的總理衙門,批準淮軍調遣的皇帝。圍繞對日交涉控制局面,則居間協調總理衙門、沈葆楨、日方和其他西方駐華使節,調動或安撫沿海相關督撫大員。圍繞推動自強海防建設,則聯絡沿海督撫和相關官員,推動總理衙門,上書朝廷。按親疏遠近,可以區分為李翰章、沈葆楨、丁日昌為主的核心內圈,張樹聲等淮系政治勢力為主的基本力量,兩江總督李宗羲和四川總督吳棠等關系密切的政治盟友,作為奧援的總理衙門,作為政治工具利用的中樞和外人。可見李鴻章形成的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新的權力運作網絡體系,在這次危機利用過程中被充分動員和強化。這一系統主要是通過朋僚之間私人信函、給總理衙門的咨文和上奏朝廷的奏折來維系運轉。這實際上是官僚體制之外非正式的“公文”流轉系統。李鴻章正是憑借這一系統來利用危機,實現自身戰略目標和推動海防體系形成。
李鴻章緣何利用危機實現轉型?
李鴻章之所以要利用危機,是因為淮軍和其自身有轉型的迫切需要,也是晚清王朝面對外部沖擊,需要建立相對應的正式國防體系。前者在中外沖突產生時,才顯示出其存在的價值和重要性,具有走出困境,實現轉型的可能性;后者則是在中外沖突產生危機時凸顯出來,事后又為因循守舊的慣性所遺忘,因而,需要抓住危機產生的震動,推動變革。
李鴻章之所以能利用危機,有多重因素。一方面是李鴻章手中握有淮軍這一重要政治籌碼,雖然一度陷入裁撤困境,但李鴻章不愿輕易放手。淮軍及淮系軍政勢力是當時政治權力關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晚清前期政局。另一方面,李鴻章自身身兼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當然也是有利條件。李鴻章在上海和江蘇巡撫任上與洋人打交道積累的經驗,以及成功了結天津教案的經歷,獲得懂洋務的聲望。而李鴻章本人也對處理中外交涉充滿自信,積極有為,且確實具有超出當時一般官僚的政治敏銳性和國際視野,能夠敏銳覺察到危機之中存在的機會,實現控制危機,把握機會。在海防大討論期間,李鴻章給其兄李翰章的信中,其自信和抱負展露無遺。可見海防大討論交卷之前,日軍侵臺事件中的兩個核心人物李鴻章和沈葆楨,已經成為眾望所歸的洋務領袖。
除了李鴻章本身具有的政治意愿和操控能力之外,危機利用還要有利的內外環境和條件。危機利用的成功關鍵在于掌控危機,不至于失控。這就需要危機強度不能太大,在幕后可以操控的范圍內;但是沖擊太弱,則沒有利用價值。日軍侵臺就是一種具有刺激性但又可控的危機。而甲午戰爭則是兩個國家之間殊死一戰,幾乎沒有政治操作的空間。這是就中外沖突而言。同時,內部綠營的廢弛、海防的空虛以及1865和1874年王朝中樞慈禧太后與恭親王之間二次政爭,慈禧太后雖制服恭親王,但其自身對處理國家事務又力不從心,形成了巨大權力真空,需要借助李鴻章這樣的實力派人物來填補,這一國內局勢的發展也給李鴻章以可乘之機。
危機與危機利用:晚清歷史敘事的重要歷史構造
本文所謂危機利用是在晚清特殊背景下發生的。危機是在中外之間發生,危機利用是在內部政治和權力系統中進行,王朝內部權力系統中下放的權力轉向應對外部沖擊的海防體制,權力下移蘊藏于權力外移之中,形成權力下移和權力外移結合的特殊現象,這需要從內部視角和外部視角相結合的角度來觀察。日軍侵臺事件若結合內部視角重新審視,我們會發現這一事件存在于雙重語境之中。一方面是中外關系語境下的中外沖突事件,另一方面這一時段中國內部正經歷從太平天國戰爭引發的戰時體制向平時體制的過渡。圍繞李鴻章的大量史料,讓我們能將這一中外沖突事件置于內部權力結構和體制變化語境中,以李鴻章和淮系政治勢力為視點,看李鴻章如何化危為機,形成新的權力結構、海防格局和以李鴻章為中心的洋務自強新政體制的形成。
事件應對和危機利用構成的復合結構是晚清歷史敘事和研究需要特別注意的歷史構造。費正清等學者總結出“沖擊與回應”,如果只是強調西方沖擊,中國回應,則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觀的誤區。其實面對西方沖擊,中國一方并非只是被動、直接回應。中國內部還有不同的歷史主體,有各自訴求。因而,外部沖擊造成的結果是復雜的,有可能不是回應,而是利用。利用外部沖擊來實現自身目標和訴求。本文揭示的事件背后的危機利用就是這一歷史復雜構造。沖擊與回應是外部視角,還需要危機利用的內部視角。就本文而言,危機應對是以王朝為中心的視點,危機利用則是以李鴻章為中心的視點。兩者結合構成比較完整的歷史。
危機和危機利用在晚清并非個別現象。危機利用與權力外移是晚清權力關系變動和體制變化的重要路徑。1870年天津教案、1874年日本侵臺和1875年馬嘉理事件這三個連續發生的中外沖突和危機,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雖然只是低烈度沖突,但借助這三次危機,李鴻章從內部平叛一線,入主北洋,將淮軍帶入海防體系,建立起以李鴻章為主的海防體制,并將外交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集國防外交大權于一身,完成了晚清前期最重要的權勢轉移和體制建構。
(作者系寧波大學歷史系教授;摘自《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