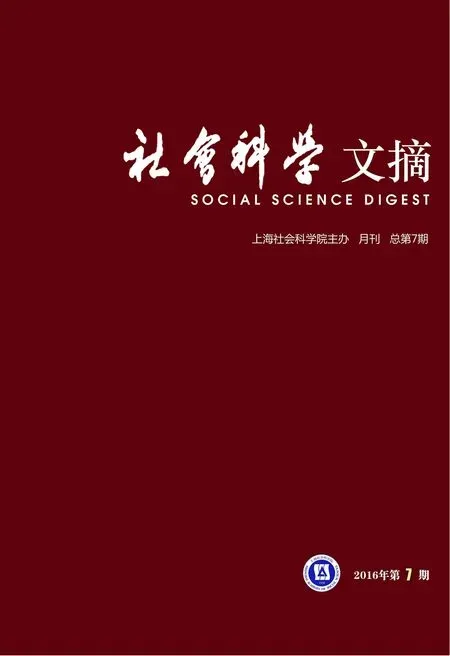現代實踐觀念的起源與現代性困境
文/王南湜
現代實踐觀念的起源與現代性困境
文/王南湜
人們常用“現代性困境”或“現代性危機”來表征現代實踐方式所陷入的悖謬境況,并對這種現代實踐方式及與之相應的觀念表現形式進行批判。此即所謂現代性批判。但當人們在這樣做的時候,卻往往只是直接抓住現代性觀念的現成表現形式進行批判,而忽視了對使得現代實踐方式獲得其合理性表征,即在觀念上獲得支撐、引領和確證的現代實踐觀念及其起源的考察。由于實踐觀念乃是相應的實踐方式的最為直接和根本的合理性支撐,且事物的起源乃是其本質的最直接顯現,因而這種忽視了現代實踐觀念及其起源的現代性批判就往往流于表淺層面,而不能抓住其本質。因此,欲改變現代實踐方式以緩解現代性困境,便須改變現代實踐觀念;而欲改變現代實踐觀念,則又須了解現代實踐觀念的源起,它與古代實踐觀念之根本差別,并從這種差別中發現現代實踐觀念的缺陷及其合宜的處置之道。本文將試圖表明,實踐觀念從古至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變化的根由在于,在古代本為最低級之人類活動的制作因近于上帝創世之活動而成為神圣性的,其后果便是制作替代了生活世界,遮蔽了生活世界,這使得現代實踐觀念與亞里士多德作為習俗性的倫理生活的實踐觀念大相徑庭。故合宜的處置之道便在于,在某種意義上通過康德而回歸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古代實踐觀念,而這一點正是馬克思《資本論》時期的思想所揭示出來又被人們所忽視了的。
現代實踐觀念與古代實踐觀念的反差
在對于現代性困境的諸多考察中,海德格爾關于“技術的追問”,顯然更為切中問題。海德格爾不同于他人的深刻地方在于將現代技術之本質視為“是與現代形而上學之本質相同一的”,而科學,這一“現代的根本現象之一”,亦是在深層上由技術所規定的。這就將技術這一現代人類實踐的主導方式提升到了形而上學的高度,且視作現代社會最為根本的規定性。
與古代社會相比,在現代社會中技術的地位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呢?這需要回到亞里士多德那里。我們現時稱作“實踐”的生產活動或技術,就是亞里士多德稱為“制作”的人類活動。他認為,在目的內在于活動自身的作為道德、政治的實踐活動以及作為沉思的理論活動中,以永恒的東西為對象的理論具有最高地位,而在以可變東西為對象的活動中,實踐由于是一種具有內在目的的活動而高于外在目的活動的制作。于是,制作成了最為低下的活動方式。顯然,亞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技術或制作在人類活動中的地位,與現代社會所理解的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現代哲學是否普遍蘊含著一種全新的實踐觀念
海德格爾對于技術的追問,道出了何以技術在現代社會成為了“最為根本的規定性”, 并使得技術成為了現代實踐觀念最為根本性的規定,從而也就成為了現代哲學所普遍持有的觀念。
在海德格爾看來,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貫通并統治著現代生活。但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是一種促逼,它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儲藏的能量。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現代技術的本質顯示于我們稱之為“座架”的東西中,作為命運,“座架”指引著那種具有訂造方式的解蔽。這種訂造占統治地位之處,便驅除任何另一種解蔽的可能性。
這樣一來,為技術的對自然的“訂造”本質所決定的現代科學的本質,便被追溯到現代物理學出現之初的伽利略、笛卡爾和牛頓等人那里。現代自然科學的根本特征是數學化。伽利略曾言,自然這部大書是用數學的語言寫成的。但數學并非只是簡單的科學工具,而是現代科學之本質性的東西。
如果我們承認對于世界的“籌劃”“訂造”是現代技術、現代科學和現代哲學之基底的話,那么,海德格爾將現代性困境歸結于現代技術之特質,或者說,從現代技術之特質去探討現代形而上學之本質,進而探討現代社會之本質,也就是全然合乎情理之事。
現代實踐觀念的基督教神學根源
那么,從古代到現代,人類思想何以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笛卡爾作為現代哲學之奠基者,其思想的革命性轉變到底是如何發生的?如若不搞清楚這一問題的話,人們對于海德格爾所描述的現代思想革命,會感到即便那是十分真實的,也是過于突兀而難以理解的。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追溯這一進程的源頭。這就把我們帶回現代哲學發展之前夜的中世紀基督教神學那里。
中世紀基督教哲學是希伯來神話與希臘哲學相遇的產物。在希臘化地區傳播中,基督教借用了希臘哲學。但希伯來神話與希臘哲學是極為不同的兩種理論框架,因而這種結合之中便不可避免地充斥著種種張力。其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便是惡的起源問題。基督教哲學不能像希臘哲學那樣解釋惡的起源問題。既然這個世界是上帝創造的,且上帝是全善的,那么他怎么有意愿創造一個會包含惡的世界呢?當然可以像希臘哲學那樣,限制上帝的全能(現代也有這種有限上帝說,如奧斯維辛之后神學中與人類一起受難的上帝),但這樣一來,受限的上帝如何可信?因此,必須另覓出路。在哲學上,這開始于奧古斯丁的創新。與希臘哲學的理性主義不同,后期奧古斯丁在反對伯拉鳩主義的論戰中,盡管將源于上帝恩典的拯救提到了最高處,而仍認為世間的惡則是由于人的自由意志所造成的。這樣一來,與希臘哲學不同,道德上的惡與存在上的缺陷區別開來了,但其起源卻也轉移到了意志內部,即源于上帝的本質意志與人的意愿的張力。奧古斯丁是意在調和啟示與理性,只是他要將理性置于啟示之下,將上帝的自由意志置于首位。而中世紀另一位重要神學家阿奎那則在某種意義上傾向于將理性置于首位。這便是中世紀基督教哲學中奧古斯丁主義與亞里士多德-托馬斯主義的斗爭。在反對亞里士多德-托馬斯主義的實在論當中,奧古斯丁主義后來發展出了以奧卡姆為代表的唯名論。這一斗爭最終導致了1277年主要是針對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大譴責,其結果是唯名論思想的勝利。
唯名論把實在論顛倒了過來,認為“受造物是完全特殊的,所以不是目的論的。于是乎,神無法被人的理性所理解,而只能通過《圣經》的啟示或神秘體驗來理解。因此,人并沒有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目的。這樣一來,反對經院哲學的唯名論革命摧毀了中世紀世界的每一個方面。它終結了那種從基督教教父開始的把理性與啟示結合在一起的巨大努力”。
這也就意味著唯名論之唯意志論導致了近現代主體性哲學的興起。“現代性的起源之一在于一種特別重視上帝無限性的上帝觀。這種理解開啟了一個深淵:由于一切明確內容都被認為與上帝不相容,上帝漸漸被視為‘無名的不羈’。但一個變得如此不明確的上帝有徹底消失的危險。上帝成了一種空洞的超越性,無法為人類提供量度。對這一上帝的體驗與對一種自由的體驗無法區分,這種自由不承認任何量度,必將淪為一種縱容。”但同時,“這一發展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是內轉。個人被拋回到他自身。內轉為個人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即使它促使個人將其個體性遺棄在其內在的深淵中。在中世紀的靈性中,我們看到了現代主體主義的一個根源。”或者說,“人在自身之中發現了無限,這種無限與上帝的無限融合在一起——不是受造物所構想的上帝,而是受造物自身之中的上帝。”于是,“人在這里被賦予了兩重存在。人被描述為已經脫離了他的無限起源或無限自由,而落入了時間、空間和有限之中。但這種落入并不意味著我們的起源已被完全掩蓋,它被體驗為一種召喚我們內轉的東西,使我們超越于有限的存在。人就本性而言是受無限感召的有限造物。這一本性表明,我們可以在人那里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認知模式:一種屬于作為受造物的我們,另一種則屬于超越了受造物而達于無限的我們。”
現在思想所面臨的問題是,與亞里士多德主義傳統的經院哲學可借助體現著上帝理性的自然不同,唯名論之意志主義的勝利既然意味著上帝被視為不受任何理性規則限制的自由意志,且對人而言,處于無限的超越性的條件下,那么,處于有限的此岸的人,便只能從人自身出發去尋求這種確定性。于是,進一步的問題便是人自身有什么依據可達于確定性。這就將我們帶到了現代性的門口。
現代性哲學的興起及其困境
在意志主義的前提下,人自身要想獲得確定性,從邏輯上說,有三種可能的方式:通過神的直接授予、通過對神創造的自然的認識、通過對神的創造活動的模仿。但這三種方式之間并不是互相隔絕的,而是在某種程度上關聯著的。其中最為根本的共同點是要找到人與神的某種同一性以作為基點,但各自所找到的出發點則有所不同。
通過神的直接授予而獲得確定性,這便是以路德為代表的新教神學通過信仰而獲得確定性的方式。這種方式的所面臨的問題是,人如何能夠確定他從上帝那里獲得了據以進行判斷的權威?如果借助于每個人的良心,且各個人所得到的啟示各不相同,則又當如何?
試圖超越路德的帶有某種神秘意味的啟示方式而從人的理性進路探討確定性的,當首推笛卡爾。但這會導致他那著名的思維與廣延相互外在的二元論。
而試圖通過人的創造活動去達到確定性的,則不僅有各色人文主義者,還有哥白尼、伽利略、笛卡爾等人也持有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都在某種意義上將制作視為達于確定性的通道。與亞里士多德哲學中對于制作的貶低不同,制作由于其類似于上帝的創造活動,能夠成為人接近上帝的中介,因而在近現代哲學中亦獲得了一個近乎神圣的地位。人們甚至可以一般地說,人的制作的神圣性在近現代哲學中成了某種“共識”。意大利哲學家維柯盡管對于笛卡爾哲學是持嚴厲批判態度的,但卻也以另一種方式發揮了這一人文主義精神,將真理視為創造本身,認為既然人類世界是人類自己創造的,人類就應該希望能認識它。
把歷史理解為主體或人的創造,把真理等同于創造,維柯就開辟了一種完全不同于近代科學的把握歷史的哲學進路。這種主體的創造活動在德國古典哲學中得到了系統的發揮。德國唯心主義將世界視為人的歷史性的創造物,似乎消除了唯意志論所帶來的人與上帝的間距,解決了問題,但這種消除或解決卻是以暗中置換了問題為前提的。這種置換可能以兩種方式出現:一種是將上帝從奧古斯丁主義或唯名論所賦予的超越的位置拉了回來,置于歷史性的世界之中,而這樣一來,那個超越的上帝就仍然處在彼岸世界,而無關乎人的創造;另一種方式是暗中將人性的主體設定為神性的主體,但這樣一來,所實現的統一卻又無關乎有限的人性主體了。顯然,問題并未解決。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試圖通過人的歷史性創造活動解決問題的思路,還導致道德的內化,即道德準則不再能是由超越的上帝所賦予的,而是只能出于歷史世界自身之中,于是,由奧古斯丁所區分開的道德上的惡與存在上的缺陷,便又被重新歸結在一起了,即惡被理解為一種歷史過程中的某種墮落、某種不完滿或缺陷。這便是德國唯心主義中的異化論。于是,在這里,道德或倫理生活也就被理解為人的創世活動的一個方面或環節,不再具有獨立于制作的意義。如果再加上笛卡爾哲學中已將理論和制作活動合為一體,在這里,亞里士多德所區分的理論、實踐、制作三種活動也就合而為一了,即成為了一種可稱之為包含這三者的理論化的創制—實踐活動,而創制也就成了一種把握理論與實踐的基礎性模型。在希臘哲學中,雖然創制被人們普遍地視為一種低賤的活動,但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活動實際上卻具有一種被用于描述其他類型活動的模式化的意義,這種作為理解模式所具有的基礎性地位與其在人類活動排序上的低下地位,形成了一種明顯的反差。而在現代哲學中,這種反差則由于創制的神圣化而被消除掉了。但這樣一來,道德生活既然只是創制活動的一個方面或環節,不再具有獨立于創制的意義,那么,由于人的創造總是功利性、歷史性的,與上帝的絕對創造不同,因而,道德準則在這個意義上也就被功利化、相對化了。也就是說,現代世界不再存在絕對的道德,而只有相對性、功利性的道德。但這樣一來,所謂的道德也就成為力量的表現,而不再成其為道德了。而這正是現代性困境的最為深刻的表現。
一言蔽之,貫穿于笛卡爾以來的現代哲學之中的主導精神,便是對于人的創造力的弘揚。盡管人是有限的造物,卻被視為具有類似于上帝的創造能力,但這種創造力又不足于真正通達上帝,從而便陷于種種困境之中。這樣一種理論困境,正是現實世界中現代性困境在觀念中的反映。
現代實踐觀念的現代性后果及可能的處置之道
現代實踐觀念及建基于其上的現代性哲學,其核心便是海德格爾所著力揭示的“世界成為圖象和人成為主體”,亦即他所著力批判的人類中心主義。而正是“人成為主體”以及隨之而來的“世界的圖象化”,與現代性現實生活所具有的深刻契合性,才使得現代性哲學為現代性現實生活提供了終極合法性之意義支撐。
因此,要走出現實生活中現代性困境,便須破除現代性哲學之人類中心主義,亦即承認人類的有限性。由此而來的便是拆除基于制作之神圣性的理論、制作與倫理實踐之合一的現代實踐觀念,將三種人類活動方式在觀念上分割開來,讓三者各行其是。亞里士多德關于三種人類活動方式的劃分,康德關于理論理性、實踐理性和判斷力的三分,似乎都提供了一種現代性條件下解決現代性困境的方案。這種方案的合理性正在于它抗拒了將人的本質視為神性的誘惑,敢于直面人類理性的有限性。
但康德哲學具有一種抽象的非歷史性特征,這是其理論上的嚴重缺陷。而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正是通過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而體現出來的。在這方面,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哲學中的歷史性觀念。但這一繼承,特別是對于《資本論》創作時期的馬克思來說,卻是在如同康德那樣承認人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的繼承,而非無條件的接受。這就是將“被看成神靈的過程”的歷史,改造為人的現實的因而有限的生產方式的歷史。因此,在馬克思后期思想中,存在著類似于康德的對于人類活動方式的切分,理論思維只是其中一種。馬克思對于人類諸活動領域的這種切分,可以說是對于康德哲學的一種歷史化,因而對于現代性批判有著更大的合理性。
我們看到,克服現代性困境的出路在于,跳出現代實踐觀念這一現代性哲學之根基,而在這一方向上,唯有通過黑格爾哲學批判而在某種意義上回歸改造了康德哲學的馬克思后期思想,才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合理的進路。這也意味著,以往人們對于馬克思哲學的闡釋無論是法國唯物主義式的,還是黑格爾式的,都是偏離了馬克思的。
(作者系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摘自《天津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