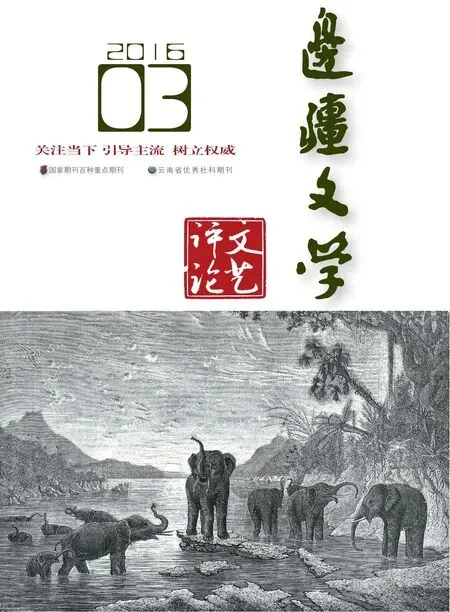行者之書
——讀張煒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下)
◎西 木
行者之書
——讀張煒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下)
◎西 木
從2010年開始閱讀至今,歷時七年,和之前評論家說的一樣,《你在高原》的十部書,它們絕不重復:無論從語言到故事,從形式到內容,從韻致到意境,十部書各不相同,創作風格差異之大令人嘆為觀止;其中的任何一部都會給人一個震驚,都會讓人來一次全新的刺激的盡興的全景式的游歷!《你在高原》幾乎囊括了自十九世紀以來所有的文學試驗。這種極為罕見的巨大的創造性和神奇變異,很難想象會發生在同一個作者身上。本文擬圍繞《無邊的游蕩》《荒原紀事》《曙光與暮色》《橡樹路》《鹿眼》這五個單元進行粗淺的解讀。
1. 生活,永遠在路上:讀《無邊的游蕩》
《無邊的游蕩》,從第一次翻開書本開始閱讀到落筆寫作此文,足有一年時間,書本反復翻閱,不計次數,一本新書,邊角已被磨卷,此次閱讀,可謂漫長。
“可憐的兄弟!你如此懊喪、悲傷和無助……我除了焦慮和難過,更多的只是袖手旁觀,是無濟于事的急躁。有時候我甚至不知該怎么安撫和勸慰,像你一樣慌促,一籌莫展。”這是《無邊的游蕩》的開頭,豐富,逼真,形象,焦灼,讓讀者無處可逃,同時考驗和磨煉閱讀者的意志力。
據說《無邊的游蕩》是《你在高原》的最后一本,很遺憾我沒有按照順序閱讀,也許錯過閱讀精彩,也許偶得閱讀妙趣。閱讀是一次奇妙之旅,翻開書本,邂逅文字之前,誰知道將會打開怎樣的潘多拉魔盒。
《無邊的游蕩》中,主人公寧伽正經歷著難言的人生苦痛,卻始料不及地走入了好友凱平令人心痛的情愛故事與家族傳奇:他正與養父丘貞黎進行著可怕的對峙與糾纏。這個過程漸漸牽引出一個令人震撼的人間悲劇。戰爭時期,邱凱平的父親于畔冒死救下了戰友丘貞黎。丘貞黎把邱凱平當做自己的孩子,撫養他長大。寧伽的岳父是丘貞黎的同事,因為這層關系,寧伽結識了邱凱平。丘貞黎望子成龍,但邱凱平卻總是不愿服從養父對人生道路的安排,甚至愛上了家中的保姆帆帆。可是,事情并非像人們所期望的一樣,朝著健康如意的軌道行進。小說用“游蕩”將兩個故事勾連起來。一個是關于慶連和荷荷的,一個是關于凱平和帆帆的。這是兩個讓人不忍卒讀的悲劇。悲劇的制造者一是“大鳥”,也即大享;二是高官,也即我們的某些“公仆”。前者以逼良為娼的種種惡行將以荷荷為代表的一批清純少女變作權貴階層下酒的珍味;后者則不知廉恥地將可以做他孫女的、養子愛上的女孩逼作自己的情婦,并且讓她為自己生下一個孩子,緊接著還要以一個垂暮之身圖謀霸占她一生。而悲劇制造的過程,又是充分“西西里”化(即公權黑社會化)了的。小說以“睡美人”荷荷放的一把沖天大火結束。是自焚,也是他焚。在《無邊的游蕩》里,張煒把19世紀的文學經典敘事和西方歌劇藝術及現代藝術、魔幻現實主義天衣無縫地、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從肉體到精神的“游蕩”, 從社會現實的矛盾到人物內心的沖突,在小說里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詮釋與展現。
2. 神話故事里的人性之光:讀《荒原紀事》
《你在高原》自出版至今,先后被評為亞洲周刊“世界華文十大小說”之首、中國出版集團“年度長篇小說五佳榜”等多項榮譽。《荒原紀事》獲過第四屆“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授獎詞寫到:《荒原紀事》通過講述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經歷,探究父輩及家族的興衰、苦樂、得失和榮辱,在廣闊的背景上展示20世紀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和心理特質。
《荒原紀事》的推薦語是:“觸目驚心的民間疾苦,一場關于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較量”。小說圍繞三條主線展開:現實生活中失地者與集團的權益爭斗;烏坶王與煞神老母雪恨的神話故事;孤膽英雄李胡子的傳說。小說的開頭幾乎像是復述了一則我們常見的新聞:一個村莊與周圍工業園區的沖突矛盾,這個廠區的污染使周圍村莊深受其害,水變質,胎兒畸形。從城里來的小白悄然醞釀了一場“萬民折”事件,最后演化為一場工業園與村民的暴力沖突。小白、紅臉老健、老冬子、葦子們四散逃去,成為工業園與警察都在緝拿的對象,開始無休無止的流浪。而主人公寧伽,也因為這件事情被關進集團的黑監獄,遭受“身上散發出濃烈怪味到無法忍受的阿侖等人的監禁和折磨。”被保釋后,他開始了尋找小白和鼓額的流浪之旅。
小說中神話故事的插入讓讀者十分著迷:神話里的烏坶王和煞神老母,都是被大神遺棄的人。為了達到報復的目的,大平原被他倆用匪夷所思的方式徹底出賣了。“一個大好的月亮天里,受母狐幾天來的暗中召喚,不知多少憨螈的后代都默默地往林中走來。這些人當中有野物生的,也有人生的。有的像河馬,有的像蟒,還有的像野豬和海象。”
李胡子是獨身大俠,打家劫舍,殺富濟貧,干的都是老百姓喜歡的事情。李胡子身上充滿了“義”字,死得讓人唏噓:李胡子放走了平原上顯赫的“戰家花園”的主人四少爺,上級要求對李胡子就地正法。司令兄弟使出罵他離開、命令部隊拔營出發急行軍一夜一天等方法,都沒有擺脫他追上隊伍主動接受處分的行為。
主人公的流浪情結在小說里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在流浪途中,那個把我擁在懷里、當做小孩兒的孤獨的老女人,那個不斷地講述李胡子故事給那群流浪漢的老者,那個迷人的美麗沙妖,無不美好。就連失蹤的釀酒師武早留下來的信,那些獨白式的、夢囈般的碎片語言里都充滿了去那塊聚集了一群流浪漢的,隱秘的沙島上尋找那個叫“大嬸”的女人的流浪情結。
神醫三先生是小說中一個閃亮的角色。采集“魂”和“魄”這兩味藥的神奇故事,半夜給精靈看病的故事,為美麗的沙妖治病的故事,讀來拍案叫絕。“一個人在醫術上出了大名必要遭來許多麻煩。還有野獸,甚至有妖魔鬼怪。”
有人說,《荒原紀事》第一次把民間文學的敘事框架與現實主義的寫作方法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了一起,其爐火純青的筆力讓人驚嘆。“傳說”與“現實”這兩個世界都構成了強烈沖撞,其劇烈程度又始終居高不下,終成為一出酣暢的大戲。
3. 黑暗之下,尋找光的另一只眼:讀《曙光與暮色》
當痛到極致的時候,人會集體失語。《曙光與暮色》整本書,圍繞不停的行走、逃離,那種不斷下墜的沉痛感,憋得讓人喘不過氣來。
誰是底層?被人冤枉而四處逃亡躲避通緝的莊周?當臟膩不堪的他裝成售賣破錫壺的人出現在海邊茅屋的“我”眼前,當他得知被摯友“老寧”拒之門外那一刻,陷入深深的絕望和憂傷的,不僅是莊周,更是“我”。自從心靈背負上贖罪的枷鎖,“我”也再次踏上了尋找之路。
不斷的出山,入山,是否就是不斷的出世、入世?有的人留在山里,就像那個據說家里開了工廠,開了銀行,為了一個女人的事情跟家人鬧翻后住進大山的、戴瓜皮小帽的石屋老人。有的人死了,就像那個在別人心目中差不多是一尊“神”的老教授曲涴,為了愛,為了自由,為了明天,他逃進大山深處,死在一片雪白的荼花之中。有的人歸來,就像回到梅子和小寧身邊的我。有的人在半路徘徊,就像那朵“校花”淳于云嘉,從會場,到林場,再到鹽場,在從人到獸的退守中,她成了一個精神時好時壞的女人。
誰是弱者?農場里那個在宣傳欄上寫詩的老教授?被初戀情人紅雙子折磨致死在禁閉室里的路吟?比所有人都狠的被沙石混起的“巨流”淹沒的工頭老五?支撐著一家經濟支柱的保姆小冷?為了找到出門打工的哥哥,倍受那么一些畜牲、一些狼一樣男人蹂躪,不僅自身的血液病惡化,還染上了“臟病”的冉冉?
誰是真正的贏家?永遠儀態大方的濱?八十多歲的老畫家聶老?學識淵博的靜思庵主有光?營養協會的主席黃科長?黃科長的頂頭上司、偶像首長?
堅守到底還有何意義?一個接一個的謎題,像潮水一般涌來,要把人淹沒。一如那些望不到邊的黑夜。一個個近乎匍匐在大地上討生活的人,一邊要忍受生命的磨難,另一邊要面對靈魂的拷問。一面是步步緊逼,另一面是步步退讓。不禁讓人仰天長嘯:生活到底有沒有深淵之底?在哪里?何時抵達?
就像那場十年浩劫,底限和底線的駁論就在跪著生和站著死的一墻之隔處,那里,站立著無數左邊是天使右邊是魔鬼的陰陽人。走,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停,便是身體或者心靈的萬劫不復。人終歸是高等的動物,可饑餓,可干渴,卻不能心死。心一旦死去,其他統統歸零。
有人說,《曙光與暮色》是一部結構主義的杰作,它以高超的寫作技巧完成了三個故事的鑲嵌與拼貼,催人淚下。就個人的閱讀經驗,那些關于創傷記憶的所有文字中,還似乎沒有過如此的沉重與戰栗。一個老人的一生,組成了一部集平庸與卓越、純潔與污濁的矛盾的生命樣譜。
無疑,這是一本讓我讀得很痛、很累的書。
4. 冥冥中的那些人和事:讀《橡樹路》
閱讀《橡樹路》的過程,是一個跟自己閱讀感執拗的過程,一個接一個的疑問,涌上來,翻滾著,一層,又一層,以致《橡樹路》的閱讀之旅無比漫長,前前后后將近半年,直至落筆,已是春節,新年老年,都是全新的一年了。
人,到底有沒有靈魂?有人說有,有人說無,更有研究結論:人的軀體死后,靈魂依然存活,在宇宙里漂游著、折騰著。《橡樹路》里,自從那個身高馬大完全像巨人的老妖被十二勇士殺死后,冥冥之中的魂靈便盤旋在老城堡里。而“我”在橡樹路的糖果店里遇到那個凹眼姑娘,像一根無形的線,牽出了橡樹路上那套兇宅,牽出了“白條”和那些臉色蒼白的青年。在雜志社上班的“我”擁有向往遠方并堅持出去走走的莊周、呂擎、陽子一干朋友,娶了杏眼圓通的小不點兒梅子,生了兒子“小鹿”,與住在橡樹路的岳父岳母“鐵來灰娃”關系也漸漸和緩。但是雜志社與“環球集團”合作,卻讓“我”邂逅了大山西部平原里冒牌的“橡樹路”和變成了老頑童的“們兒”。現實苦難和誘人難解的童話穿插相映,現實中的王子與仙女與童話中的人物遙相呼應,隨著小說的閱讀,歷史與現實、童話與真實切合延伸。
在黑色九月之花盛開的時節,環球集團的小白秘書出現在橡樹路那個最有名的大宅里,院子里挖出的像碾盤那么大的、砸去了一半的石獅子頭;石頭刻的小人兒;埋在院角的畫了一些八卦紙符的瓷壇,而“我”,親眼目睹了蒼白青年最后看一眼這個使他丟失了青春和生命的大宅,“我盯著那里:‘這是一次真正的……痛別……’”
5. 人生百味皆道盡:讀《鹿眼》
曾經美麗的平原上,奔跑著一個永遠不知疲倦的瘋子,他總是大聲喊叫:“發大水了呀,發大水了呀——跑啊——撒開丫子跑啊——跑啊——發大水了呀——”
瘋子的喊叫,一次次激起人們內心對那個古老傳說的恐懼心理:雨神的獨兒子“鮫兒”出去玩耍的時候被讓天下遭受旱災的妖怪旱魃擄走了。從此,急瘋了的雨神滿世界的尋找她的兒子,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會發大水。人們同情雨神,憎恨旱魃。為了消滅可惡的旱魃,人們曾經掘開大戶人家的祖墳,可惜一無所獲,狡猾的旱魃又一次逃脫了。第二年,發起大水,溝滿壕平,房屋倒塌……人們再次陷入雨神尋找“鮫兒”的夢魘。
清澈明亮的鹿眼,它看過來時,你的心上顫顫的。平原上曾經有很多這樣的鹿眼:那只被帶槍的人射殺的小鹿、有一雙黑亮眼睛的音樂老師、醫師嚴菲兒時的雙眸、教師肖瀟的目光、女生唐小岷亮晶晶的眼睛……可惜,在這個日新月異變幻的大平原上,一雙雙美麗的鹿眼,漸漸失去了曾經的光芒。
身體健壯的“蘋果孩”駱明的意外死亡,引發出過去“我”家被抄家、被流放,差點斷了香火的往事的真相,原來,這一切竟然都是“我”一直認為是恩人的夫婦所為。駱明的死亡,最終導致本來就與平原人家格格不入的教師廖縈衛和妍子的兒子廖若的精神失常和離家出走。
希望能夠為廖家和包家做好調解工作的“我”,被請到公司里,遇到傳說中那個留了光滑的背頭,穿了寬松長袖衣服,布扣子,黑色千底布鞋的蘇老總,一番話不投機的交談之后。“我”突發急病,躺進了那所話題不斷的醫院,成為了初戀情人嚴菲的特護病人。
神秘莫測的公司創始人“得耳”的身影無處不在,從劁豬匠發家的他,時而是公司董事長,時而是游走民間的大善人,時而是走村串巷的劁豬匠……他和蘇老總,一陽一剛,一陰一柔,就連那個對肖瀟一往情深的市長,也奈何不得。
小說從對音樂老師的講述開始,又在音樂老師的獨白中結束。關于平原上的各種沖突,居民們的憂愁和無望,瘋子無邊無際的游走……“我”沒有做出回答。
小說末尾說,“我”即將離開。讀過整部小說的人都知道,“我”的離開,更多的是一種回歸,一種對都市、對家庭、對社會、對身份感、對責任意識的再次抵達。大平原,只是“我”心中一個不可割舍的執念。執念,本身就是一種罪!
有人說,《鹿眼》以兒童的視角融合了魔幻、偵破小說,并以強烈的詩性攫人心弦,是一部令人心曠神怡的奇書。它有一種童年的清美,卻又將最悲傷的苦難元素融入了其中。在筆者所看到的所有關于現代信息時代對兒童的傷害,無論是紀實還是虛構作品,就其深刻與驚悚程度而言,本書都是完成了一次重大的超越。
至此,《你在高原》已全部讀完。劉維穎說,“39卷本450萬言的《你在高原》當稱中國文學史上名副其實的鴻篇巨制。這部作品讓人想到巴爾札克的《人間喜劇》,從中看到一位中國作家的勃勃雄心和浩瀚的氣象。從《家族》,到《無邊的游蕩》,張煒給讀者的印象一直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行吟詩人。其中,作為《你在高原》“開場大戲”的《家族》,在幾年前的閱讀中,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而《無邊的游蕩》作為《你在高原》的“壓軸”巨獻則讓我真切感受到詩人的錐心傾訴和泣血歌吟。一如作者過去的小說,主觀抒情性是一大特色。這是一把雙刃劍。它在詩化文本的同時,也讓人略感沉悶拖沓,有時真想跳過去往前行去。估計圈子外的一般讀者許多人都會做此選擇。另,婁萌那條線原以為是要在兩個悲劇間搭起一座橋梁令其最后完成膠結咬合的,后邊卻好像斷了,感覺有些結構性殘缺。當然,在張煒這樣的大師級人物面前,說這話,是有點班門弄斧自不量力的味道了。”
合上書卷,不知為何,心底更加沉重。忽然想起《安娜·卡列妮娜》的開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明日就是除夕夜,2016,年來了!
(作者單位:云南省楚雄州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