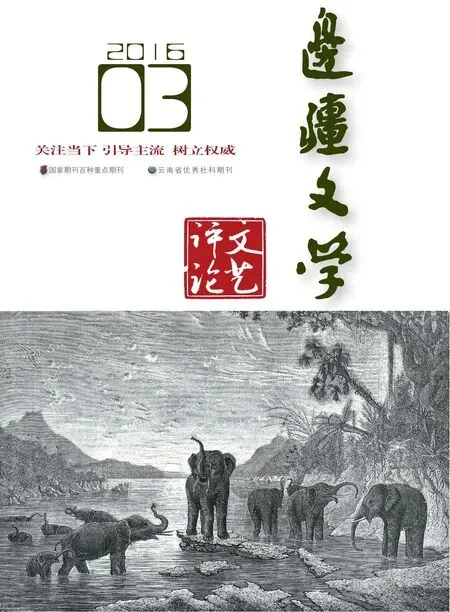鄉村守望與文化突圍
——對呂翼中短篇小說集《是否愛》的一種解讀
◎納張元
鄉村守望與文化突圍
——對呂翼中短篇小說集《是否愛》的一種解讀
◎納張元
昭通文學研究
主持人語:呂翼是昭通作家群中70后的代表,近年來,他的小說創作突飛猛進。引起文壇熱議的長篇小說《疼痛的龍頭山》之后,又出版了小說集《是否愛》。這部小說集再次受到讀者和評論家的好評。本欄目選發評論家納張元教授和詩人夏玲的文章,以期引起方家的關注。納張元的文章《鄉村守望與文化突圍——對呂翼中短篇小說集〈是否愛〉的一種解讀》,全面分析了小說集《是否愛》的得失,在肯定其創作特色的同時,也指出作品的局限。立論有據,分析得體,有較強的審美力度,是一篇有見地的好文章。夏玲、曾子芙的《天道人道兩難全——論呂翼〈冤家的鞋子〉的兩難未知結構》,運用結構學的理論解析小說集中的中篇小說《冤家的鞋子》,認為這篇小說“突出的特點是內在結構的提升,這個故事看起來是一個愛情故事,也有人把這個故事看成一個抗戰故事,其實故事的內在深層結構是一個彝漢文化沖突的故事,是一篇有著深層兩難未知結構張力的小說。”文章觀點正確,層次清晰,有一定的理論深度。(李騫)
中國當代文學發展趨向之一是視角廣度擴大,寫作視野向底層、民間、邊緣及少數族裔轉移,把地方性文化和民族特色納入現代視野,構建當代文學的民族化敘事維度。昭通作家呂翼以富有民族特質的創作崛起于文壇,為當代昭通文學平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小說集《是否愛》以滇東北烏蒙山區、金沙江岸為背景,敘述這片土地上百年以來的喜怒哀樂、人生百態,從不同角度展示了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間傳奇。昭通位于云南省東北部,坐落在四川盆地向云貴高原抬升的過度地帶,金沙江下游沿岸,地處云、貴、川三省結合處。昭通歷史上是云南省通向四川、貴州兩省的重要門戶,“鎖鑰南滇,咽喉西蜀”,是中原文化進入云南的重要通道,也是云南文化三大發源地之一。昭通是典型的少數民族散居地區,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數民族大分散、小聚居,濃郁的地域文化與各族文化因子相互滲透。昭通的少數民族雖然也被裹挾著進入國家現代性的歷程,但每個民族積淀了千年的文化傳統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習俗不會馬上消失,即使是表面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變,內在的文化觀念和民族自覺意識也很難輕易更改,傳統固有文化與新的異質性文化的碰撞和沖突始終伴隨著這個漸進現代化的過程。
小說懷抱著一種博大而深沉的家園之愛向外界,向世人昭示著作為少數民族作家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全球化浪潮背景下,民族文化覺醒與民族文化斷裂相生相伴,現代文化既給予民族文學表現的空間與動力,也沖擊著民族文學的獨特性與地方性。轉型時期,作為民族文化精神的載體,呂翼的小說彰顯本民族傳統文化,但民族特色彰顯、民族文化認同并非是呂翼作品的唯一價值取向,呂翼作品中體現更多的是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交錯叢生、新舊交織的多元形態,既有堅實的文化之根,更有超越的藝術之靈。作家一方面眷戀著獨特的民族文化氛圍和淳樸的民情民風,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了民族文化在現代化背景中的艱難前行與悲壯堅守。這就使得作家在傳統與現代、本民族與他民族的交流和碰撞中,體現了對現代文明的依存和對本民族文化的依歸,呈現出一種透明的深沉和優美的凝重,使得淺近與深邃同在,情趣與哲理同生。他筆下的鄉土風貌、民族風情與人文精神、民族傳統、兒童情趣融合在一起,既散發著一種清新、天然的生活氣息,又呈現為粗樸、自然的文化狀態。
呂翼小說的魔力來源于他的根——“楊樹村”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楊樹村是呂翼以自己家鄉昭通的風土人情、地理環境為依托,為自己的小說構建的一個典型的云貴高原烏蒙山區鄉村的名稱。小說《愛恨龍頭山》、《冤家的鞋子》、《蕎花如潮》、《方向盤》、《仙鶴湖紀事》都是發生在楊樹村的故事。呂翼說:“楊樹村是我的文學村莊,它所收藏的東西太多,它的苦難、堅貞、博大、深厚、迷茫、抗爭、污濁等等太多。走進楊樹村,采用一種適合于自己的寫作形式,這對于我來說應該是一生的選擇。”
作為70后作家,呂翼自覺摒棄了對民族風情的簡單展示,而沉潛到本真生活的深處,關注民族文化在社會進程中的改善與重建。他不屑于跟風獵奇,而致力于刻畫民族性格,表現民族心理,觸摸民族靈魂,反思民族文化。關注在社會進程中農村人所經歷的精神危機和蛻變,以個性化的寫作來溝通對民間精神和民族靈魂的熔鑄與反思,審視現代化語境中傳統與現代的契合、沖突甚至抗衡。探討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在全球化背景和后工業化時代中的張揚,再造與重生的大課題 “年紀大了,到死的那一天,人們才會把請祭司念經的事提上議事日程,才會有人突然說:請老爹來念三天經吧!爺爺從不推辭,立即戴著斗笠,披著擦爾瓦,敲著法器,給他們念經,為他們送葬。爺爺的聲音很古老,很滄桑,悠遠而粗糙。像從地獄里出,像到天堂里去。打小,大洋芋就在爺爺這樣的聲音里成長。”(《愛恨龍頭山》)爺爺一直在為楊樹村人念著《指路經》、《喚魂經》、《解災經》、《平安經》,卻苦于后繼無人,民族文化將面臨斷裂與消亡。作家通過原生態呈現人物實際生活狀態,力圖全真展示楊樹村的文化傳統、社會癥候。特別是對楊樹村人的精神世界給予深層關注,更為細致多元地展現內心圖景和鄉土反思。字里行間浸潤著樸素的鄉土情感和民族情結,因而也最能表明特定地域環境和時代背景下的鄉土特征和文化歸依。
《冤家的鞋子》講述了抗戰時期的一個傳奇故事:漢族女子開杏與漢族教書先生胡笙相戀,卻被彝族漢子烏鐵搶走,被迫和烏鐵成婚。婚后,烏鐵盡力對開杏好,但是開杏卻日夜思念胡笙,冷漠面對烏鐵。當胡笙來到開杏身邊時,開杏因為自身經歷避開胡笙。烏鐵和胡笙為了逃避情感困境奔赴抗日戰場,二人在戰場上成為并肩戰斗的好朋友,后方的開杏等待著二人歸來。這篇小說的表層結構是一個愛情故事或者抗戰故事,深層結構則是一個彝漢文化沖突的故事,小說通過對烏鐵、胡笙和開杏生活的地域環境、民族文化、風俗習慣進行描寫,暗示出每個人物的行為后面都有民族文化心理的強大慣性在起作用,人物行為的衡量標準帶有濃郁的民族文化特性。比如:在上個世紀初,彝族男人搶漢族女人在漢族眼里是壞事,而在彝族這里是英雄行為。呂翼沒有單一譴責或者是贊美其中的哪個人物,而是通過三個人的矛盾沖突讓讀者思考兩種文化的差異,體驗不同民族的人物精神世界的不同結構,探析漢族的主流意識形態與彝族文化的差異,思考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的方式與前景。如黑格爾所言,真正有價值的悲劇不是出現在善惡之間,而是出現在兩難之間。
《愛恨龍頭山》鐘情于以人之初的純凈潔白的目光觀照楊樹村的美麗與神奇,沾著厚重的泥土味兒,透著活潑的孩子氣。這部作品從龍頭山支教白潔老師在某天關于一堂“愛”的討論課開始,讓缺母愛的彝族少年大洋芋更加思念母親。“黑板上寫滿了用愛組成的詞語:親愛、仁愛、令愛、偏愛、樂山愛水、嫌貧愛富、相親相愛、舐犢之愛……不寫不知道,一寫嚇一跳,用愛居然可以組成近百個詞語。” “有愛是幸福的,沒有愛是疼痛的,渴望愛更是錐心刺骨的。”“他(郵遞員)是一根連接線,為大伙連接了鄉思,連接了親情、友情與愛情,連接了牽掛,還連接了幸福與疼痛。”這些溫暖的文字是一股股流淌的愛的河流,蘊含著對美好事物、美好情操、美好生活和美好理想的守望與追求,以及對丑惡、腐朽和陰暗事物的拒斥。體現了作家對藝術真實的探尋,對高蹈境界的向往,對高尚情懷的追求和對美的呼喚。讓人感覺到溫情與呵護,回味喧嘩中的寧靜與和諧。大洋芋與父親普麥和犸基(狗名)踏上千辛萬苦尋母的征途。然而當大洋芋在昆明尋到母親,帶著犸基隨白潔老師坐上金大叔的大貨車回到龍頭山,龍頭山正處在山崩地裂的地震中。小說刻畫了一批豐滿而生動的人物和動物形象,年少聰慧的大洋芋,伶俐可愛的小花嬌、傳承彝家文化的烏普老爹,愛妻心切的普麥,美麗善良的支教老師白潔等等,甚至公雞棵棵和狗犸基刻畫的鮮活生動。小說中一個很特殊的人物——烏普老爹,他是龍頭山彝族中年紀最長的祭司。每天晚上,他都會從木柜里取出那些發黃的、被翻得卷邊、開始破爛的神秘經書,坐在火塘邊,一邊敲羊皮鼓,一邊經誦。龍頭山生態被嚴重破壞,烏普老爹就天天念《平安經》,祈求彝人宗教里統治天地萬物的天神“恩體古孜”,保佑龍頭山平安吉祥。從烏普老爹身上可以看到呂翼對彝族文化傳承的重視。呂翼除了寫彝族文化傳承的重要性,還特別注重外來的研究力量。白潔老師與男朋友小羅潛心研究彝族文化,積極向外面推介,擴大影響力。白潔老師還充分使用現代化工具宣傳彝族文化,讓民族文化用各種形式走向外面的世界。呂翼在這部小說中思考了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的重要問題:民族文化的傳承。他不僅積極探尋傳承民族文化的方式方法,而且還客觀地認識到民族文化的缺陷,比如:念念經、送送鬼就可以改變一切,是迷信的,主觀的;在社會市場經濟下,一些傳統觀念過于保留、落后,也必須摒除;彝族能歌善舞,值得充分肯定,但嗜酒的風俗,作者以小孩的眼光委婉表示了反對。呂翼在小說中體現了文化自覺精神,即對彝族文化地位作用有深刻認識,對民族文化發展規律有正確把握,對發展文化歷史責任有主動的擔當精神。同時,呂翼將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結合起來,通過大洋芋這個形象的塑造,對民族文化的發展前途充滿信心。在這部作品中,呂翼既歌詠彝族的傳統美德和獨特文化心理結構,對洶涌而來的現代化象征物進行道德批判和負面想象;同時也無情地揭露民族文化的因循與落后,表達的是民族的革新和求變訴求。在生態被破壞的現代進程中,呂翼以民族文化的內在力量抗拒現代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義思想;在民族文化面對開放的世界的過程中,呂翼強調面向未來,讓民族文化吐故納新,借助時代契機實現民族的自我更新和現代轉型。
《方向盤》中的“楊樹村”充滿活力和希望。大學畢業生尉涪是現實中新農村建設的新生力量和希望,他反映了一個農村青年的成長歷程。人物出場時還顯得比較幼稚,在事業和愛情之間搖擺不定,對前途比較迷茫,“我跟他們不同,我既沒有留守楊樹村耕田種地,也沒有像其他年輕人一樣外出務工。我既不像那些老年人一樣心寧氣靜、固守鄉野,也不像那些孩子們無憂無慮,得到一塊土豆片就要樂半天。我心不甘,也放不下面子,我沉不下去,也浮不起來,在大學畢業后的兩年里,我像是一片飛揚在空中的白楊樹葉,上不沾天,下不落地。”讓他當村文書,他也完全不放在眼睛里。“我當然不去,我讀了很多的書,我志向很遠。一個大學生,回楊樹村這樣的破村當一個村文書,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楊樹村的發展變化、建設前景對他還是有著吸引力,加上女朋友許玫的吸引與勸說,使他最終能留在鄉村。小說體現了楊樹村年青一代價值觀念的更新,他們在生活、事業、理想方面都有著和老一輩完全不同的觀念與追求。這才是鄉村最值得期待的希望之光。外人看到的是楊樹村的貧窮、封閉、落后、愚昧,年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尉涪看到的卻是楊樹村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有開發利用的大好前景。他還看到深層次問題:楊樹村貧窮、落后的根源在封閉、保守。小說結尾部分,尉涪“手握方向盤”,“箭一般地朝著楊樹村駛去”。有意強化了新一代農村青年扎根楊樹村,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到新農村建設之中的新主題,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蕎花如潮》寫楊樹村兩父子和月亮地兩母女的命運。其中寡婦五姑是血肉豐滿、光彩照人的典型形象。從傳統觀念看,五姑是村中不守婦道的風流寡婦。“月亮寨是遠近聞名的風流寨子,這個寨子曾演繹過萬種風情。而在這個風流寨里,最美的就是五姑了。五姑是月亮寨絕妙的美人。她那種美呀,連再兇惡的狗見到都叫不出聲來,讓整個烏蒙山區的男人談之而向往不已、魂不守舍。當然五姑也就很風流,五姑這樣的人,生在月亮寨這樣的地方,不風流才怪,不風流就說不走了。反正她有的是容顏,有的是青春。這東西不用,過期就作廢,并且永遠無法找回。”這段描寫充滿了野性的粗獷和原始的魅力,既有民間文學的樸拙率真,又有文人文學的含蓄蘊藉,充滿民族性、地域性的質感和張力。五姑16歲嫁給月亮地村村長得癆病的兒子,才三天男人就死了。她在小白臉劁豬匠和麻子臉配種人之間輪流坐莊,以至于所生的四個女兒是哪個的也整不清楚。還勾搭上了楊樹村風流浪蕩的殺豬匠。性欲報復之下的愛情向往,自由抗爭之下的苦命人生,傳統道德與現代觀念之間的沖突等問題作家都進行了深度挖掘和詩化描寫。作家不再停留于故事的表面,而是深情地描摹人類的生活本相,深入人物心靈深處,把人寫透,全面展示人的精神世界,發掘人物精神之光。在對生活的富有歷史精神的肯定與否定、贊美與貶斥、同情與厭惡乃至于困惑、無奈的情感態度中,寄寓著作家特有的“悲天憫人”情懷。這種起自靈魂深處的悲憫,讓他的作品多了一份真誠與厚重,有了一種厚度與深度。感情發自肺腑,自出真心,誠摯動人。少有形式主義的花拳繡腿,也沒有任何先見之明的“偉大意義”,有的只是純粹的生活事實,作為一種寫作姿態,他的筆觸深入到底層民眾的生活,生存困境與生活苦難為呂翼的小說增添了一重深沉的色彩。
小說《此河彼岸》、《是否愛》是發生在城市的故事。尤其難得可貴的是,呂翼無論是對農村題材還是對城市題材的現代把握和詩性書寫上,都能在特定的人文時空中,對自然與人性的思考有著獨特的角度,既葆有云嶺高原崇山峻嶺包裹下的民族風情與地域特色,又有現代理念與蠻荒落后的碰撞。這是作家在現代性語境下獨特而復雜的情感體驗、生活經驗和藝術探索,是融入了生命感受的寫作,真誠而溫暖。呂翼自己也說:“文學不是保健和護膚,而是苦口的良藥;不是裝飾擺設而是刀劍斧錘。它強調的是批判和解剖,重量和光芒。”作家天生是人類命運的關注者和社會文明進步的促進者。舉凡各個民族各個時代優秀的作家作品,無不高揚人文精神。《此河彼岸》是呂翼城市題材中頗有特色的一篇小說,更像一篇寓言。題目就有些哲學的味道:“站在此河,看彼岸”,著名老作家白樺認為,最好的小說就是:“它既是一個現實的故事,又是一個寓言,且具有多義性。”呂翼在對雞零狗碎、一地雞毛的日子縱橫展示中表現了當代城市人的迷茫、堅守與突圍。體現了作家對鄉土世界的突圍和對城市文明的深沉思考和深刻感悟。作家有意引入婚外戀的眷戀與歸宿、官場角逐與友情背叛、失意君子與無聊小人、情場得意與官場失意、情愛與性愛的對抗與回歸、球場和情場的互質轉換等多義主題。作品中對江薇、夏大樺、房琚、梅先笙等底層小人物的生命、尊嚴、價值、生存狀態及未來命運的深情關注,同歷史理性血肉般地聯系在一起。這正是童慶炳先生提出的:“歷史理性存在著人文的維度,人文關懷存在著歷史的維度。”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加速了現代化和城市化進程,整個社會進入生活與文化的重重變革震蕩中。任何歷史時期的社會轉型通常充滿艱難掙扎的陣痛,處于地理與文化雙重邊緣的少數民族尤其如此,需要經歷多重的文化沖突與改變。少數民族作家在這種歷史沖突時刻往往比其他作家還要處于首當其沖的位置,他們是本民族文化的嫡系傳人,對本民族文化懷有深厚的民族情感,但作為有文化自覺的知識分子,他們對現代化的歷史要求也最為敏感,深知在一個普遍的社會轉型期民族自我現代化是必由之路。這種時代歷史沖突在他們身上常常表現為自我沖突,體現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甚至是文化焦慮,他們既不能盲目認同以西方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進程,又擔心民族保守文化立場與守舊心態會使他們錯失全球化語境中改造傳統文化的歷史機遇。不同作家對此處理方式不盡統一,從而決定了不同文本的文化價值取向和思想深度差異。在一部分少數民族作家的筆下,作品的一元化取向與思想平面化傾向比較明顯,但在呂翼的作品中,已經擺脫了初期的單一化,獲得了文化承擔和思想力度。因而,呂翼作品中的文化沖突是對多元文化選擇的自覺,推動創作主體反思自身的文化結構,為理性的文化選擇作出最初的清理。全球化浪潮下的民族文學創作,民族性與現代性的碰撞不可逃避。呂翼作為一個少數民族作家,他的創作面臨著一元與多元、現代與傳統、東方與西方、邊緣與中心、自我與他者、全球與本土、漢語寫作與母語寫作等多重復雜問題。呂翼用創作的自主性來呈現民族自信的張力與對現代文化的接納融合,呈現給讀者有質感的社會重大問題,不以理想的大團圓結局代替復雜的現實,構建起在現代性與民族性沖撞中的民族文學主體性,表現出少數民族作家對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反思的深入,呈現出與時代脈搏同步的創作理念與方法革新。
呂翼以彝家漢字的真淳樸拙走入文學殿堂,情緒飽滿熾烈,文字飛沙走石,具有粗獷直硬的質地,但難免有失精純。從藝術角度看,小說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比如對人性深度的開掘,以及敘事方式、語言個性和小說風格的形成,都還需要在寫作實踐中進一步思考,繼續向新的高度攀登。
小說敘事過于拖沓,枝蔓太多,開門不能見山,一通云遮霧繞之后未能展示出烏蒙磅礴的厚重,金沙水泊的氣勢。如《方向盤》原本是站在主人公尉涪的角度以第一人稱敘事,但是在敘事視角上過于開放,未能使第一人稱敘事的參與性、限制性特點很好地體現出來,反而具有全知全能式敘事的駁雜與開闊,這就使得人物主體的聚焦不夠集中,多少沖淡了人物形象的個性特征和小說主題的表達。部分敘述過滿,過實,水滿則溢,月滿則虧,過猶不及。如《蕎花如潮》中“最近,縣里表彰了一批優秀教師,汪老師是其中一名。……這樣,他有了機會隨著那一批教師,到了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參觀學習。一路上,他的思想受到了強烈的沖擊。他為自己對新瑞的態度而深深內疚。自己是個老師,為人師表,卻將個人恩怨、情感糾葛引發的怒火轉移到一個孩子身上,這是多么不應該的事。更何況新瑞是個優秀學生,是個通過自己努力,可以成才的孩子。自責像鞭子一樣抽打著他的良心。一回到楊樹村,他就跑到樹根的家,要樹根將新瑞接回來。他要好好教他,他會讓他成器。”這樣的敘述過于蒼白、空洞,缺乏細節的發掘和情境的展示,反而失去文學“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
天道酬勤,著名作家從維熙說:“生活和命運把你蹂躪了一番以后,才會把文學給你。” 呂翼在《邊疆文學》筆會上的一次發言中也說:“如果作品是花朵,苦難則是風雨,經歷過了,美麗的花蕾才能開放,才能脫出魂魄一樣的香艷,才會花謝花飛,結出累累果實,讓你生命力得以延續。如果作品是一塊礦石,苦難則是烈火,浴火再生,就會剛硬無比,無堅不摧。如果作品是刀具,苦難則是粗礪的磨刀石,脫了一層銹,就會變得更鋒利。”我們有理由相信,經過一番深寒徹骨之后,作家的生活視野更博大,思想視野更高遠,知識視野更寬廣,審美視野更獨到。我們期待著呂翼有更多更優秀的文學作品誕生。
(作者系大理大學文學院院長、二級教授)
責任編輯: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