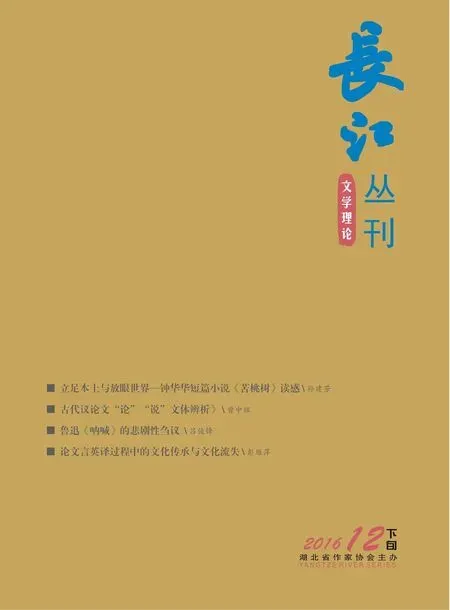淺談枚乘之子枚皋的“文人”身份
羅 靜
淺談枚乘之子枚皋的“文人”身份
羅 靜
枚皋成長中經歷了父親枚乘的缺席,又繼承了其父的文學才能及政治遺產。其作品有成文快、數量多、詼諧、創新等特點。本文認為枚皋身處中央政權的邊緣,雖文學史上影響有限,但在文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發展歷程中非常關鍵。
枚皋 父子 文人身份
枚皋生約公元前156年,卒年不詳,今人對他的了解主要是來自《漢書·賈鄒枚路傳》,《漢書·藝文志》記其“賦百二十篇”,今不存。本文將以《漢書》為主要資料來源,從枚皋與其父枚乘的關系及其作為一個漢代“文人”的身份兩方面進行梳理。
《漢書》記載“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枚乘游于梁孝王時娶枚皋母為“小妻”,即妾,后“孝王薨,乘歸淮陰。”(《漢書·賈鄒枚路傳》)皋母不肯隨,枚乘分數千錢而怒去。皋母很可能生于梁孝王轄區,嫁給游士①,枚乘去后留梁孝王轄區。此地濃厚的文學氛圍對枚皋有不可忽視的影響。枚皋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時年十七歲。三年后為王使,得罪后逃亡,漢武帝大赦天下時以賦得武帝喜愛,與東方朔同留在武帝的身邊。
一、枚皋與父親枚乘
枚乘是漢辭賦家,其《七發》在文學史上被認為是漢賦形成的標志。枚乘枚皋相繼具有優秀的寫作能力且有種大一統意識,本文將從兩方面敘述“父親”對枚皋的影響。
其一,成長歷程中“父”的缺席。
從枚皋的成長歷程來看,枚乘在兒子需要父親時處于缺席狀態。“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后乃得其孽子皋。”枚乘死于征召途中,武帝特問枚乘諸子,惜求之不得。“后”說明了枚皋似已被眾人遺忘,若非上書自薦便徹底湮沒無聞。父親雖未在枚皋的身邊,枚皋卻繼承了父親的才能,并以之走上文壇。或許枚皋正是因為被留在了有較好文學傳統的梁孝王轄區,才能脫穎而出。
其二,求仕路上“父”的強化。
枚皋在求仕路上開始強化“枚乘之子”的身份,這要從枚乘留給枚皋的遺產來說。枚乘固然留下“數千錢”的財富及大量文學創作。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政治遺產。
吳王妄圖謀反,枚乘力諫不得,只好離開。吳王謀反失敗,枚乘的遠見名揚天下。枚乘對“謀反”的思考很有見地。他反復向吳王說明,天下已非戰國,吳王一人一地不足與中央抗衡。雖是現實利害的權衡,仍有戰國縱橫家審時度勢的余味,但其中包含了枚乘對中央與地方新關系形成的體認——漢諸侯王不同于戰國割據政權。這種大一統意識及其政治敏銳性使他與同游于吳王的鄒陽差異立判。
漢武帝需要枚乘這樣的人才。《漢書·本傳》“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②無論是不是枚乘真心想參與到政治中,但他已表明了想被納入到國家官吏的體系中的意愿。而枚乘之死是他留給兒子的政治資本。“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枚皋能得到漢武帝承認,自然是“因賦殿中”之能,但另一打動武帝的是“枚乘之子”。
由此可見,父親枚乘帶給兒子的政治遺產加上枚皋本人的文學才能,使得枚皋迅速踏入了體制之內。
二、“文人”身份
今人看來枚皋是一個較為典型的專職從事文學創作的文人。下面從他的創作特點、他對自己的認識來分析其“文人”的身份。
其一,從他的本傳記載來看,他的創作主要有以下特點:
創新性。太子劉據出生后,枚皋、東方朔等人作《皇太子生賦》,惜其不存。“皆不從故事”,既表明了賦這種文體在草創時期活躍的生命力,也表明了枚皋、東方朔等較強的創新能力。
成文快、數量多而今不存。“皋為賦善于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寫得快,作品也多。《漢書·藝文志》記枚皋賦百二十篇。這也和他職業文人的特點有關。不處理政務只專職寫作。
風格詼諧。“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曲隨其事”是將實際的情況用詼諧的方式表達,“得其意”又“詼笑”。
其二,枚皋的自我認識。“皋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非。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據《漢書》記載很可能枚皋對賦的認識、對文人的認識,也是有一個過程。起初,寫作讓他進入體制內的捷徑,而非最終目的。無論上書梁共王還是上書武帝。而成功進入中央體制之后,在武帝身邊,枚皋也曾經嘗試過用寫賦的方式勸諫過衛皇后,可惜似乎沒有什么影響力,可以作為他對自身創作放入政教體系中的嘗試,這種嘗試以失敗而告終。武帝把他帶在身邊不離左右,是對他個人才華的肯定,但是這種才華使得他受制于此難有突破,只能保持與政治的距離。但是他的存在價值是“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他必須要說出“上”想讓他說出的東西,而他又要讓這些東西從自己口中說出來具有其不可代替性,他于是在寫作的形式上創新發展。在這樣的矛盾之下,他會后悔自己只能從事文學創作,對自己“見視如倡”的地位不滿。他對自我的這種否定,也否定了自己文學創作存在的獨立意義。
其三,枚皋對其他文人的看法。《漢書》中說“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又自詆娸。”他與東方朔類似的地位,讓他對自己和對東方朔的存在都不滿意,他拿自己打趣,拿東方朔打趣,無法對自己的地位產生滿足感,缺乏對自我“文人”身份的認同。他的偶像,并不是父親枚皋,而是司馬相如。枚皋羨慕司馬相如,悔恨自己不如司馬相如。一方面因為司馬相如是自己的前輩,另一方面則是司馬相如的經歷是文人的理想境界。枚皋和司馬相如類似之處是他也因文章得到武帝的喜愛,得到中央大一統體制的承認;但是后來兩人的經歷卻迥然不同。司馬相如后來能夠代表中央政權出使巴蜀地區,成功轉型成為封建官吏;而枚皋卻一直作為漢武帝身邊的文人,政治生涯便停滯了。司馬相如的人生代表了枚皋人生的另一種可能,或者說,是枚皋理想中的發展歷程。也就是司馬相如受到他崇拜的原因。
其四,漢武帝對枚皋的認識。漢武帝得知枚皋的存在后“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當武帝得太子之后,“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為”。枚皋常在武帝左右,“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武帝欣賞他的寫作才華,也清楚得認識到枚皋沒有從政的能力,他不通經術,沒法將他作為一個專門的官吏去使用。枚皋站在中央政權的正中心,但是卻不能真正參與中心,只能成為中心的邊緣。
三、結論
《全漢賦》評枚皋:“其個人在當時的政治地位也并不高。漢武帝只是以一種類似俳優的文學侍從的待遇予以安排。至于在賦史上也沒有產生重大的影響。”誠然,對枚皋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枚皋在文學史上影響有限。但是將枚皋放在文人自我身份認同的發展歷程中,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枚皋以文學能力靠近中央政權,走上政治舞臺,但是卻僅限于此。這當然與他獨特的知識結構有關——缺乏經學知識,故只能專職從事文學研究。他有過掙扎,有過嘗試,最終也只能到此為止。通過枚皋的人生歷程,我們或許可以體會到那個漸漸遠去的時代之“文人”。身處中心卻只有邊緣地位,對身份充滿困惑。通過了解文人的歡喜與悲哀,有助于我們想象他們的人生歷程及理解他們的過往如何塑造我們的現在。
注釋:
①以藩國女嫁游士,似非僅在梁孝王轄區.《漢書·地理志》:"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晉灼曰:‘有女者見優異.’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淮南王用當地女子許配游士,淮南王與梁孝王皆愛士,或有類似之處.
②漢武帝征召枚乘確實達到吸引人才的效果.《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并出."
[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于迎春著.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
[3]于迎春著.秦漢士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4]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