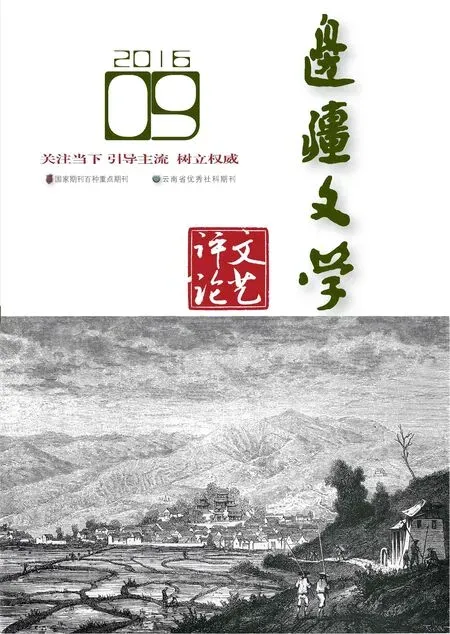神合感探幽
◎姚全興
神合感探幽
◎姚全興
神合感是古代文學家的幻想
中國古典文學中,常有這樣的描寫:“心凝形釋,與萬物冥合”、“精浮神淪,忽在世表”。這種物我同一、人與宇宙默契的心理狀態,就是神合感。它只是一種主觀感想,并沒有客觀實在與它相應,但確有這種精神境界。這種精神境界的描寫,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一種別具一格的令人為之低回和遐想的藝術特色。
那么,神合感是什么樣的主觀感想呢?它實際上是中國古代文學家的幻想。按照心理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觀點,文學家產生幻想,主要是因為文學家的愿望未滿足,或者說他在現實中不是一個幸福的人。弗洛伊德又把幻想說成是文學家潛意識中受壓抑的欲望的曲射,一種心理上的升華。他認為文學家的創作是白日夢,他們創造在現實中并不存在的事物,來滿足自己潛意識中得不到滿足的欲望。這種觀點無視社會對人的影響,但包含了若干合理因素,比較正確地揭示了幻想的實質,幻想與現實的關系,以及文學家產生幻想的原因。
我們不要看許多神合感的描寫瀟灑而浪漫,似乎文學家熱情奔放,精神愉快,有優哉游哉、飄飄欲仙之感。其實,他們中有些人的內心是很痛苦的,受著壓抑,欲望得不到滿足,就只能利用文學創作做白日夢了。于是,白日夢中出現了奇特的神合感,一種不折不扣的幻想,這使得神合感具有變相滿足的補償功能。
那么,中國古代文學家有什么痛苦和內心欲望呢?從中國歷史上看,凡是象魏晉時代那樣政治黑暗、現實紛亂的社會,總有一些文學家如嵇康那樣“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現實生活使他們意志消沉,成為退避山林的墨客騷人。那些寄情于自然的詩文看起來超脫,骨子里卻潛伏著無窮痛苦。阮籍、陶潛之類的文學家內心都有擺脫人間桎梏,一心追求自由的強烈欲望,他們那些帶有神合感的作品,正是這種欲望的導泄,并通過導泄,使自己的緊張心理松弛。正因為如此,神合感雖然在事實為幻,卻是有現實根據的,或者說在假象中寓有客觀的本質。
神合感是消極的心理現象,但其表現看起來又是積極的,可以說是心理上的征服沖動。文學家向往宇宙,想飛向沒有煩惱沒有痛苦的宇宙,因此每當他們產生恍然出世、超然物外的神合感,就覺得自己征服了現實,擺脫了人世,于是在作品中顯得飄逸、靜穆和空靈。
神合感的心理特征
神合感的一個心理特征是自我暗示。文學家為什么能夠從一顆沙里看出一個世界,從一朵野花里看出一個天堂?這是因為文學家觀照自然時向自己暗示了一種宇宙觀念。自我暗示即自己向自己暗示某種觀念,并通過想象表達出來。例如失眠者不是強迫性的命令自己入睡,而是平心靜氣地躺著,想象自己睡的時候如何輕松,頭腦如何昏沉,不多時候會自然入睡。文學家的自我暗示也是這樣。陶潛“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為什么能夠這樣呢?他說是因為“心遠地自偏”。確實,陶潛“采菊東籬下”時,萬念俱滅,只讓自己“悠然見南山”。通過觀照時的自由想象,暗示自己從“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的景象可以得到宇宙之感,即與宇宙冥合,與物同一。這種自我暗示是自然而然、平心靜氣的,雖然“此中有真意”,然而“欲辯已忘言”,說明他的精神修養和文學修養,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
神合感的另一個心理特征是自居作用。自居作用是把自己和對象視為同一,把自己所欽佩或崇拜的對象的特點當作自己的特點,形成主客體的和諧統一。科學家往往把自己的全身心進入到他認識、研究、創造的對象中去,即全神貫往。文學家也往往在觀照時形成自居作用。他們“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王羲之《蘭亭集敘》)其時,他們的精神世界不僅和客觀世界溝通起來,而且完全“進入角色”,覺得我即宇宙,宇宙即我。王維的《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就是自居作用的范例。詩人的心靈和自然打成了一片,或者說沉浸于自然的天機之中。這種靜穆的觀照形成的靜穆的詩境,盡管是置身于塵世之外超現實的境界,但也確實是詩人自居作用的結果,在心理學上是有根據和可以說明的。
容易引起神合感的事物
云霞、流水會引起而且特別會引起神合感,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云水的清輕空靈,和廣袤寂寥的宇宙的清輕空靈有一定的相似性,或者說二者的質地基本相同。當精神淡泊的文學家凝神觀照云水時,就通過這種相似性把云水和宇宙這兩個不同事物聯系起米,產生新的感覺——神合感的宇宙意識。這正如經驗豐富的科學家,善于運用類比法,把兩個不同的事物聯系起來,產生新知。中國文學家在人格上崇尚精神淡泊,在藝術上崇尚空靈簡淡,這種志趣修養在本質上是和宇宙意識相通的一致的,有助于他們產生神合感。
從審美心理學看,云水以及花草之類引起的神合感是一種優美感,其特點就是清輕空靈、委宛舒徐、縈回繚繞、秀麗優雅等。但是,神合感又不僅止于優美,而是通過優美達到崇高,從優美感進一步引起崇高感。只有崇高感才能和宇宙感或宇宙意識相稱,只有宇宙才能體現世界上最偉大的崇高。這是因為自然界的崇高主要是以量即數量上與力量上的巨大為特征的。
中國文學家的生命力在黑暗的現實中受到阻滯,但他們又不甘心于現實的桎梏,一旦他們接觸到宇宙,內心的生命力變得更加強烈,從而有崇高的情緒產生。崇高的宇宙又提高了他們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超越世俗平常的尺度,并賦予他們勇氣與現實的壓力進行較量。這也就是產生征服動機的心理原因。而崇高的宇宙,之所以能提高他們的精神力量,是因為它激發了人的本身所潛在的抵抗力,即人的理性、勇氣和尊嚴。這使得他們保全自己的人格,即使他們知道自己是難以和現實匹敵的。所以中國文學家的神合感本質是崇高,它通過宇宙寄托崇高的精神。中國文學家心目中的宇宙既優美又崇高,可敬畏可親愛。他們并不因為宇宙的廣袤寂寥而感到恐怖,感到人的渺小和無能為力,恰恰相反,而是和宇宙合成一體,親密無間。由此可見,神合感是崇高的又是積極的,潛在著主體能動性。
神合感又包含著宇宙空間感。中國古代文學家對空間一向充滿感情,并且總是在空間中馳騁想象。他們探索、歌詠、描繪空間的詩文連篇累牘,不勝枚舉。且不說屈原的《離騷》《天問》對空間的叩問何等熱誠,歌詠何等瑰麗,描繪何等奇特,也不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山水文學對空間的向往和追求何等真摯,就說古典文學的鼎盛時期唐代吧,許多詩人對空間的仰慕是那么深切。王維詩云:“徒然萬象多,澹爾太虛緬。”韋應物詩云:“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浪漫詩人李白的空間意識自然更為濃厚。他的《大鵬賦》和《悲清秋賦》和他的許多詩篇一樣,意境遼闊,極富有空間感,“上摩蒼蒼,下覆漫漫”、“水流寒以歸海,云橫秋而蔽天”之類佳辭麗句俯拾即是。杜甫比起李白,更重視現實,然而他的作品也不乏空間感,“游目俯大江”、“乾坤萬里眼”等名句表明他也有俯仰宇宙的氣概。
酒仙與神合感
除了云水花草容易引起神合感的優美情緒,宇宙之大更能引起神合感的崇高情緒外,即除了自然現象會引起神合感外,某些刺激或麻醉神經的東西也會引起神合感。酒與神合感有點關系,酒固然未必都能引起神合感,而常常能引起“忘我”的心境,因此有“有酒學仙”之說。那么為什么酒有這種作用呢?因為酒精能改變心理狀態,對心理變化有明顯的效應。中國文學家常以酒解憂,以酒澆愁,直至“有酒學仙”,都是企圖用酒使自己忘卻黑暗的現實,短暫的人生,接近崇高而永恒的宇宙。現代科學已表明,這是由于酒引起強烈的有力量的幻想,使人感到能為挽救世界盡一臂之力。酒引起神合感的感覺經驗正是這樣的:比較輕松、精神安定、向各種感官刺激開放并敞開情感的大門。開始出現感覺提高——感到一個人在所有感覺通道中比平常更加細致、更加敏感地覺察事物。物理感受性的實際增強大約并未出現、但在感官信息察覺的方式上出現了質的變化。這種質的變化表現在酒醉者陷入自己的內在意象和心理作用中,暫時失去同周圍環境的感覺接觸,個人身分感可能暫時衰退,感到自己是遠遠勝于一個凡人。真正的神合感只能產生于陶潛、李白那樣的“酒仙”的頭腦中。也就是說,豪飲而又很有文學修養、精神情操的人才能產生嚴格意義的神合感。
還有飲酒能使人在精神放松時情緒意興勃發。據最近媒體報道,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研究人員把40名志愿者分成兩組,讓他們做解題游戲時,一組吃零食看動畫片,喝少許酒,另一組也看動畫片,但不給吃喝。結果表明微醺者做題時直覺更強,沒有喝酒者則靠審慎推理。研究人員認為,微醺讓人放松,有助提高創造力,希望創新的藝術家有較大可能從微醺中尋找靈感。這也證實“酒仙”喝酒容易產生神合感。當然并不是說能產生神合感的文學家都是“酒仙”,“酒仙”也不一定都能產生神合感,這是不言自明的。
神合感與中國哲學的關系
中國哲學對天也即宇宙是很重視的,儒道佛三家哲學無一不對宇宙有所反應。魏晉時代這三家哲學合為一體,形成頗有思辨特色的玄學,仍然對宇宙極感興趣。其時不管入世者也好,出世者也好,都要對宇宙寄托自己的感情。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唐宋,其間山水詩人和山水畫家都受這種哲學影響。他們共同的特點是,都要“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從自然山水中尋求宇宙天理。應該說這個時期中國哲學對中國文學和藝術的影響有積極意義的一面,即中國的文學家和藝術家,像一些進步的哲學家一樣,開始了人的覺醒,對世界的認識從被動變為主動,從微觀變為宏觀,從有限變為無限。
那么,儒道佛哲學為什么會使文學家產生神合感呢?這主要是這些哲學中的泛神論在起作用。一般說來,有神合感的文學家多少受老莊的道家哲學熏陶,而老莊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泛神論。老莊認為道無所不在,實際上也就是神無所不在。這種神具有超時空的絕對性獨立性,即老子所謂“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正因為這樣,這種神非普通人所能認識,要認識必須“滌除玄覽”,“致虛極,守靜篤”。莊子在老子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人不僅應該認識道,而且應該與道合一,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卸六氣之辯,以游無窮”。顯然,這正是泛神論者追求的物我同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境界。而這種境界,常常導致文學家沉湎于神合感中飄飄然的羽化成仙似的心境,超然物外的情調和意蘊。
神合感的文學創造性
如果說創造性是指揭示事物新的內在聯系的能力,改變現行規范的能力,那么神合感正是這種創造性。具有創造性的基本特征:獨特性、變通性和流暢性。古代文學家由于有神合感,作品中的意象往往奇特新穎,甚至有些神秘,非一般文學意象可比。謝靈運、李白的詩,往往奇思放縱,浮想聯翩,從山水景物的審美觀照中表現宇宙里面活潑的天機、深刻的哲理,而置漢儒的名教、世俗的禮節于不顧。他們藝術思維靈活多變,不受定勢或習慣性思維的約束和影響,顯得灑脫和飄逸。陶潛、王維的詩表現“虛以待物”的入神狀態,看來是一種不動聲色的禪機入定,卻不是僵硬蹇澀的,而是像劉勰所說的“神與物游”的神思。這類詩人大都“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在創作過程中,活躍而富于變化地產生大量意象,如行云流水從容不迫,天風海濤狂放不羈。柳宗元、蘇軾的作品就達到這種融會貫通、無掛無礙的化境。與物冥合的神合感使他們的創作得心應手、揮灑自如,必然通向自由。
而且,古代文學家能夠“精騖八極,心游萬仞”,無疑是神合感的創造性想象起了作用。創造性想象的特點是創造新的表象和形象,文學家發揮了這種想象,所能把握的領域就遠比直接感知的領域廣泛而深刻。因此神合感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能夠使文學家超脫有限的現實和無限的宇宙冥合。古代文學家創作活動中還通過神合感釋放大量情感,如陶潛“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從而把深刻而獨特的生命體驗,化成清高悠遠的情感之水。這類作品和訴求人間真情的作品顯著不同,其情感表達不是動天地、泣鬼神那樣慷慨和激越,而是在浩瀚的宇宙意識里傾注作者博大的內心感受,像陳子昂的《登幽州臺歌》那樣,“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發人深思和令人全身心的震撼,具有歷千年而不衰的的藝術感染力。
(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楊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