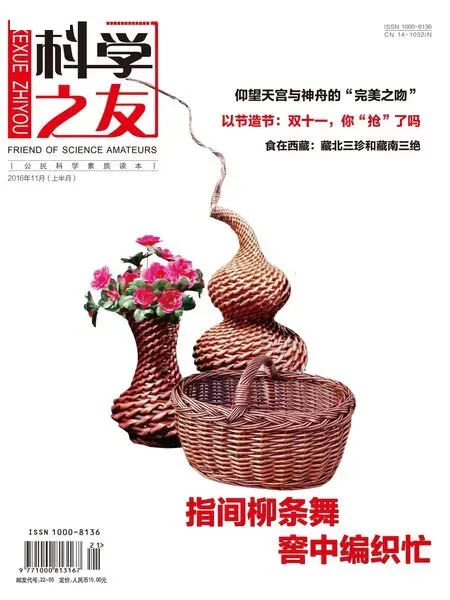堡壘
文| 地瓜
堡壘
文| 地瓜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不要為我哭泣;
如果有一天我們不能再相見,不必把我記起。
我們只是小徑上的過客,偶然交疊足跡,
在小徑的盡頭,我仍會記得那一天,
你出現在我的生命里……
——無名詩人
一
“檢查驅動程序……完成。加載戰斗序列……完成。”伴隨著一個冷冰冰的電子合成女聲,我眼前出現一片白茫茫的雪花,像在看一臺壞掉的舊電視機,只不過我好像是在這臺舊電視機的里面,身體一片冰冷,被固定在一塊金屬臺上。
“B-9‘堡壘’式多用途戰斗機器人,編號E54,請確認。”那個女聲繼續說道。“確認。”我機械地回復道,然而傳出揚聲器的聲音,不是語言,只是一連串無意義的電子合成“嗶嗶”聲。但那個女聲顯然聽懂了,冰冷的聲音中似乎摻雜進一絲喜悅:“E54已被激活,可以執行任務。”
“等等!”我打斷她,“我的聲音怎么了?”女聲沒有理我,自顧自道:“視覺系統上線……完成。”
我能看見了。一個冰冷的世界,一切都是深色的。我面前下方有一團明亮的紅色,根據聲音方向判斷,它就是女聲的來源。
“我眼睛怎么回事?”我又哀號道。
“你的視覺系統是熱成像的,別緊張,你會習慣的。”女聲安慰道,“我是N-2‘風鈴’式護理機器人,編號D63,我會幫助你度過這段過渡期。”
“我怎么是機器人?”我終于意識到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檢查你的記憶硬盤。”女聲緩和了許多,“你還記得嗎?”
“我……我……”我抬起左手,只能看見一條銹跡斑斑的機械臂,還能聽見“嘎吱嘎吱”的金屬聲;我抬起右手,看見了一支大號沖鋒槍;我低下頭,看到一雙液壓腿下面各連著一個鐵疙瘩腳板。恐慌漸漸在我的身上蔓延開來,“我什么都不記得!”
接著,我兩眼一黑。在意識飄走之前,我聽到女聲說:“操作系統死機,準備重新啟動。”
二
那個女聲說得沒錯,記憶硬盤里確實保留了一些資料,只不過很多都已經損壞了。這里像一座支離破碎的迷宮,我只能通過里面的只言片語,拼湊起我想知道的一切。
很顯然,一切都始于人類與機器的一場戰爭,而發生的年代與原因已不可考。
人類的策略與意志,在機器的計算能力和銅墻鐵壁面前,不值一提。很快人類就意識到,單靠自己的血肉之軀,根本阻擋不住機器的鋼鐵洪流。能抗衡機器的,只有機器,但他們不信任任何機器。
一項融合計劃于是被提上日程:尋找人類志愿者,將其意識數字化,注入到機器中,與各種戰斗程序融合。這樣的士兵具有機器的計算能力,必要時刻還會憑借經驗和本能作出判斷,兼具機器和人類的優勢。他們所組成的軍隊,作戰能力與機器軍隊不相上下。同時最重要的,他們具有人類的慈悲,不會成為冷酷無情的機器殺手。
人類勝利了,戰爭結束了!
三
“你還記得你當年怎么被數字化的嗎?”那個女聲問。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平躺在一個平臺上,四周仍舊是藍黑色的,頭上吊著一盞大燈。比起剛剛兩眼一抹黑,我隱約能分清墻壁與各種器具了。這似乎是一個廢舊倉庫。那團紅色的“火焰”在離我腦袋很近的地方來回游移,不時有火花從我腦袋里蹦出來。
“當年是哪一年?”我問。
“我不記得了。”女聲答道。
“今年是哪一年?”我又問。
“從我被啟動執行任務開始,已經過了3 000個地球日。”女聲答道。
我思考了足足一秒,“這個時間標準對我來說沒什么意義。”
“對我也沒有。”女聲答道。
5秒鐘的沉默。
“你在做什么?”我問。
“修理你的視覺系統。可能是系統老化,你的視覺對比度過高,導致了畫面的細節損失,所以你才會什么都看不清。好了,這回再試試。”她敲了敲我的腦袋,發出沉悶的“砰砰”聲。
我轉了轉頭看看四周,同時調整視覺焦距。確實,明暗對比變小了,倉庫的細節看得更清楚了。這時,紅色的火焰經過我的眼前,挪到我的腳邊忙東忙西去了。現在我看到,這團“火焰”其實是護理機器人的能源核心,她的核聚變能源比我的核裂變能源更高級。在我的眼中它照亮了護理機器人的輪廓:她有修長的流線型身軀和橢圓形的頭部,與我身上的棱角、銹跡和坑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重力引擎使得她能夠靈活移動,而不像我只能邁著沉重的步伐;她的四條細長手臂靈巧地揮舞著,可以變換為不同的工具,不像我右手永遠是一個跟她體重差不多沉的沖鋒槍。
“你還真像個風鈴。”我說,“以后我就叫你風鈴好了,你可以叫我堡壘。”
“你愿意叫啥就叫啥吧。”
我注意到了她說話的語氣詞,一般人工智能是不會這樣的,“你不是普通的人工智能,你當年也參加了融合計劃嗎?”
風鈴突然停了一下手中的活兒。“嗯。”她又繼續忙活。
“你還記得……”我突然不知道該怎么表達,“你當年是誰嗎?”
風鈴這次完全停下了。“我不記得了。”她頓了頓,“好像是上輩子的事兒了。”
接著,風鈴像是想起了什么。“E54……呃,堡壘,你呢?你還記得什么?”
“我?”我又陷入了長達10秒的沉默,“我全都記得……除了一樣東西。”
……
四
午后的太陽被涌動的云彩遮住,天空變成發亮的灰白色。遠處傳來隱隱的雷聲,預示著一場夏日雷雨的臨近。我離開畫室,抱著買好的清潔機器人,去她的實驗室找她。
實驗室的院子里一片混亂。滾滾濃煙中,出現一個高大身影的輪廓。透過濃煙,我看到它的頭部正面泛著紅光,刺破煙霧,對準了我。
我聽見她在喊我的名字。接下來我倒在地上。我臉朝側面,看見小清潔機器人被甩出老遠,然后它啟動了,又朝我開回來,開始清潔我流淌到地上的漸漸凝固的血跡。我作為人類的記憶中的最后一幅景象,是她奔過來時穿的白裙子。
“所以你就這樣加入了融合計劃。”風鈴說,“是她救了你的命。”
“我更希望她沒有。”我答道。
“對了,你說你還記得一切,”風鈴問,“除了什么?”
“她的名字。”我答道。
這次輪到風鈴沉默了。
“修得差不多了。”風鈴不再多說,輕盈地飛到固定我的平臺邊上,開始旋轉它,直到我前面出現一面鏡子。
我審視著鏡子里的我。右手是一架沖鋒槍,后面背著一挺六管加特林機槍,一雙鐵腳板有力地踏在地上,龐大的軀干上立著一個盒子狀的頭,頭部正面的視覺傳感器是一塊發著紅光的長方形面板。
是的,這就是我的樣子,和殺死我的機器一模一樣。時至今日,我仍心有余悸。
“戰爭已經開始了,”她流著眼淚對我說,“他們要求你必須參戰……但我盡可能地保留了你人類的成分,比誰都要多。對我來說,你從來都沒變過。”
于是我參戰了——這可能是解脫的最好方式。我以突擊模式在戰場上穿梭,我以衛戍模式向機器傾瀉加特林機槍的炮火,我以坦克模式撕裂機器的裝甲。
很多人死了——很多英雄死了,但我活了下來。
活著回家——這是我所沒想到的。
英雄的禮遇很快就成為過眼云煙,我也獲準退役,但我和她無法相處下去了:熱成像讓我分不清色彩,我的鋼鐵左手會捏斷哪怕最堅固的畫筆,我對她說的任何情話都會變成無意義的電子合成音。
于是有一天,她消失了。我不怪她。
我經常到公園里去,忍受人們異樣的目光。我有時執行衛戍模式,變成一座固定加特林機槍炮塔,一待就是幾天,有鳥兒甚至在我的裝甲上筑巢。
又過了一段時間,昔日的英雄成為人們眼中的異類,進而成為敵人。我還記得那些游行、騷亂……還有燃燒瓶砸在頭上的感覺。
人類其實從不信任任何機器。
我被強制封裝入庫,進入休眠模式——直到今日被喚醒。
比起那些被拆毀的同類,我又成了幸運者,抑或是不幸者?
五
“這是什么地方?為什么把我激活?”我跟著風鈴走過長長的走廊時,我問,“戰爭已經結束了?”
“你說的是第一次戰爭。”
我愣住了。
“這里是地球上所有物種的基因庫,包括人類的,代號:方舟。”風鈴繼續說,“這里是人類在預感到自己的覆滅時修建的。”
“覆滅?”我更驚訝了。
“你休眠后,第二次戰爭爆發了。機器的攻擊更加迅猛和致命。人類匆忙啟動了第二次融合計劃,我是這次計劃的產物,但人類還是輸了。他們在發動核戰前,建造了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現在世界上只剩下我們了?”
“我不確定人類的情況,但機器還保留下一支軍隊,它們被編程執行摧毀方舟的最后任務。在牽制戰斗中,我們已經損失了所有守備部隊,所以我需要動員一切力量來保衛方舟,這就是為什么你會被重新激活的原因——你是這座基地最后的戰斗力量,最后的堡壘。”
我感到憤怒,我的情感程序感受到了壓力,“所以你把我叫醒就是為了打仗?和平日子我沒撈到幾天,一醒來就要打仗?!”
風鈴被嚇到了,她轉過身來看著我,“對不起,我以為這是你的職責。”
“這曾經是。”我說,“但那是在人類那樣對待我之前。”
風鈴沒答話。
“我們兩個人要怎么對抗一整支機器軍隊?而且還是為了這么一個都不知道管不管用的破基因庫。”
“管用的。”風鈴小聲說,在一扇門前停下。
門開了,我驚訝地發出一陣“嗶嗶”聲。
這是一個小型雨林生態系統,煥發著充滿生機的紅色與黃色,與四周冰冷的藍黑色形成鮮明的對比。這里有熱帶植物、昆蟲、小型嚙齒類動物。
一只鳥突然飛到我的頭上歌唱,它在我的眼里通體赤紅。我伸出沉重的手臂,它落在我關節嘎吱作響的手指上。我扭頭看著它,入了迷。視覺系統中的瞄準程序自動將它鎖定,但隨即判定為沒有威脅。
風鈴看著我,“你仍然是個人類。”
“我不知道。”說完,我邁著沉重的步伐扭頭走了,小鳥匆匆忙忙地飛回到雨林里。
六
第二天,我從休眠中醒來,發現自己左手上多了一個東西,是一臺激光器。我開啟了通話頻道,“風鈴,搞什么?還給我配備武器?”“大功率的話是武器,小功率的話……就是你的畫筆。”
我愣住了。
“如果你想走的話,就走吧。”風鈴又說。我沒走。我其實完全可以離開她,獨立行動,但我沒有。可能是我“獨立”太久了。
接下來的幾天,我在迷宮般的基因庫里游走,在一切可以用激光切割的物體上畫畫。基因庫里并沒有太多我可以臨摹的東西,所以我畫我記憶里的東西——我以前住過的樓房,我家附近的電影院,我買的第一輛汽車。風鈴時不時會來看我畫畫,但她從沒有打擾過我,她默默地把我畫完的作品掃描成電子版。
有一天,我舉起左手,想畫記憶中她的樣子,但我突然想不起來她什么樣子了。我手臂端了12個小時,然后放下它,離開了。
我經過雨林室,大門開著。我猶豫了一下,又退回到門口,走進去。風鈴正在里面測試溫度、濕度等數據。
我在那看了她一會兒,然后把激光功率調到最小,在旁邊的墻壁上畫了一幅畫:一片雨里,一個像風鈴一樣的機器人正在勞作,一只小鳥在她旁邊飛舞著。
畫完之后,我退后一步,甚為滿意;再一轉身,發現風鈴就在我身邊。“畫得不錯。”她歡快地對我說道。
我想起來,很多年以前,她也對我說過同樣的話。我突然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其實還是有值得保衛的東西的。
七
接下來的日子平平淡淡,我已經習慣了蘇醒后與風鈴一起的生活。除此之外,我也開始外出修理毀壞的隱藏自動炮塔,布設感應地雷,還會定時放飛無人偵察機。我幾乎沒有什么時間畫畫了。
“我希望機器們永遠也找不到這里。”有一天,風鈴對我說。
“我也是。”
不過那天終究還是來了,我和她靜靜地看著機器們出現在雷達屏幕邊緣。我把激光功率調到最大,我的沖鋒槍自動上膛。
“你可以不去……”風鈴緊張地說,“這里很深,我們……”
“這是唯一的辦法。”我看向她,“我用筆描繪這個世界,現在該用槍來保衛它了。”
我走過長長的走廊,風鈴跟在我左右。我希望這條走廊永遠不要走完。然后我走進了升降梯,轉身面對風鈴,“我有辦法,你把門封死。”
風鈴點了點她的小圓腦袋。升降梯的門緩緩合上,我想說點什么,但終究想不出來。
“你還記得她的名字嗎?”風鈴突然問我。我搖搖頭。
“你還記得你的名字嗎?”風鈴搖搖頭。
升降梯的門合上了。在升降梯上升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究竟算不算一個人。在升降梯上升的這135秒內,我也沒有得出答案。
我走出方舟的掩體,來到一座高高的山崗之上。這里在下雪,冷冰冰、藍黑色的雪。萬籟俱寂。遠方揚起雪塵,機器大軍出現在視野里。我感到我最核心的戰斗序列被激活了。
“風鈴,你在嗎?”
“在。”
“你是什么顏色的?”
風鈴沒有馬上回答。“白色。”
我變成坦克,朝機器大軍沖去。
“那只鳥呢?”
“它……它的羽毛是黃色的,頭上有一點是紅色的。”
流彈剮蹭我的裝甲,炮火在我身邊綻放。
“有時間的話,你可以幫我把那些畫都涂上顏色嗎?”
通訊頻道里傳來陣陣靜電雜音。“好……我會的……”風鈴斷斷續續地說。
我啟動了核心熔毀程序,并替換了高濃度的核燃料棒。我感到我自己越來越紅熱,超越了這世間一切的冰冷。我繼續一邊開炮一邊向機器大軍沖去,用京劇小調哼起我在記憶硬盤里找到的打油詩:“大炮開兮轟他娘,威加海內兮回家鄉……”
我感到我的金屬外殼漸漸脫落,血肉重新包住我的骨骼。我感到我的靈魂離開了機器,重新回到了過去的我的體內。我看見了風鈴,漸漸變成她。
“風鈴,我很高興喚醒我的人是你。”
電波穿越隆隆炮聲,與我的思緒一起,飛向地心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