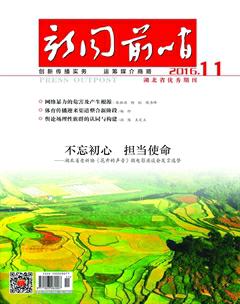“聽書”: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閱讀新方式
江瑩瑩
[摘要]有聲書“伴隨性”的特點恰巧豐富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下人們多維度閱讀體驗的需求。隨著網(wǎng)絡的飛速發(fā)展,我國的有聲書市場開始面臨新的商業(yè)契機。擁有多層次受眾布局的有聲書市場,要想做到與紙質(zhì)圖書、電子書“一書三發(fā)”,版權(quán)問題、贏利模式及制作團隊是有聲書出版平臺要考量的關(guān)鍵因素。
[關(guān)鍵詞]有聲書 閱讀 新方式
閱讀通常指看(書報等)并領(lǐng)會其內(nèi)容[1],是相對紙質(zhì)讀物而言。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逐漸興起壯大的今天,書籍不再作為唯一的一種實體文化而存在,閱讀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模式。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生活,充分利用碎片化時間的需求,都促使人們尋找更為便捷新穎的閱讀方式。不可否認,在網(wǎng)絡環(huán)境下不受時間、行動限制的“聽書”,已經(jīng)為人們的閱讀生活開辟了新的閱讀路徑,也為傳統(tǒng)書業(yè)提供了新的機遇。
一、有聲書市場的規(guī)模和發(fā)展現(xiàn)狀
有聲書源于美國,已有八十多年的歷史。1930年前后,那時美國國會圖書館和美國盲人協(xié)會為盲人讀者設立了一個有聲書籍的項目。伴隨著汽車產(chǎn)業(yè)一路成長,歐美各大城市的車載有聲書得到了較大的普及。然而,歐美有聲書實現(xiàn)真正的爆發(fā)是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快速發(fā)展的當下。在歐美閱讀市場,近兩年有聲讀物猶如一匹突然殺出的黑馬,以兩位數(shù)增速發(fā)展,迅速崛起為市場主流出版類型。美國出版商協(xié)會(AAP)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2015年前三季度有聲書依舊是整體市場增長最為迅速的板塊,同比增長高達37.7%,其總體市場規(guī)模約為1.6億美元,占總體市場的1.5%左右。這基本是來自出版社的收入。2015年英國市場有聲讀物購買數(shù)量增長27%,已經(jīng)占到圖書購買總量的3%。對于英美出版社來說,有聲讀物不僅僅是賬面上的數(shù)字,而是有1.5%—3%的實際收入。[2]
相比海外有聲書市場的繁榮,到了20世紀90年代前后,我國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發(fā)行有聲書,當時的有聲讀物大多以名著為內(nèi)容,如高等教育出版社音像中心出版了《世界名著半小時》,中國唱片總公司出版過《紅樓夢》等。我國有聲書不僅起步較晚,社會認知度也較低。隨著網(wǎng)絡時代的到來,有聲書也搭上網(wǎng)絡快車,開始面臨新的商業(yè)契機。某知名市場調(diào)研機構(gòu)的有聲書市場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有聲閱讀市場規(guī)模已達16.6億元,同比增長29.0%,其中僅電信運營商的收入就將近3億元,預測2016年該市場規(guī)模將達到22億元。”[3]
二、有聲書:做到多層次的受眾布局
碎片化生活無疑是孕育有聲書的絕佳外部條件。筆者認為:相較于傳統(tǒng)閱讀,有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伴隨性”。這種特點,可以讓人們利用一切碎片化時間隨性地從有聲書中獲取信息。難怪有網(wǎng)友評價,自從手機里裝了“聽書”應用,“一心”就可以“二用”了:每天早上開車上班的路上,限行坐地鐵時,下班健身練瑜伽以及做家務時,都可以聽書……以往沒時間看的書,漸漸地就聽完了。在筆者看來,目前我國有聲書的受眾主要分為三類:
第一類,主要受到閱讀文本限制的受眾。由于人們在生活中受到多方閱讀條件的限制,因此,在閱讀文本的選擇上也受到了影響。當閱讀條件不適宜紙質(zhì)圖書或電子書閱讀時,人們自然就傾向了受閱讀條件限制較少的有聲書。作家馬伯庸曾在微博中寫過有聲書的體驗:“我現(xiàn)在上下班經(jīng)常堵在路上,一堵一兩個小時,所以聽書比看書還多。”
第二類,是缺乏閱讀能力的受眾,比如幼兒、盲人、有閱讀障礙的人群。2015年國內(nèi)家庭教育信息平臺“工程師爸爸”創(chuàng)始人兼CEO李文華公布的當年兒童聽書的相關(guān)大數(shù)據(jù)表明:當前的國內(nèi)聽讀教育呈現(xiàn)低齡起步特征,將近80%的家長在孩子3歲前就開始培養(yǎng)孩子的聽讀習慣,6—10歲孩子家庭是音頻故事的付費主力。聽書時間方面,周一、周六和周日是故事播放高峰,周末的播放流量大約是工作日的1.2倍;故事播放時段呈現(xiàn)穩(wěn)定,意味著兒童生活方式存在巨大的聽書需求。
第三類,雖然有條件進行傳統(tǒng)閱讀,但單純對有聲書感興趣的成年人。這類人以容易接受新鮮事物、有良好教育和經(jīng)濟條件的年輕人為主。
可以說,“閱讀”在當下“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已經(jīng)不是單純使用眼睛的行為,而是多維度的內(nèi)容體驗。有聲書將紙面的閱讀轉(zhuǎn)換成為多維的聽讀方式,容易和使用者的閱讀體驗相匹配,做到多層次的受眾布局。
三、有聲書的平臺類型:運營商與互聯(lián)網(wǎng)出版公司“各顯神通”
傳媒的價值跟每個受眾的接觸點有關(guān)系,接觸點接觸時間越長,商業(yè)價值越大;受眾越廣,商業(yè)價值越大。有聲書的“伴隨性”和多層次的受眾分布,也讓這個領(lǐng)域散發(fā)出“誘人”商機。據(jù)筆者了解,有聲書平臺與數(shù)字出版平臺相似,主要分為三大運營商和互聯(lián)網(wǎng)出版公司兩類。三大運營商擁有巨大用戶基礎(chǔ),通常說來,聽書業(yè)務參照其成熟的手機閱讀運營業(yè)務,更容易推廣。互聯(lián)網(wǎng)出版公司則主要分為微信自媒體類和APP類。微信自媒體類像“凱叔講故事”,借用有聲讀物帶動紙書的熱賣,日活量已十分可觀。APP類相對更多一些,隨著國內(nèi)聽書品牌如懶人聽書、氧氣聽書、酷聽聽書以及喜馬拉雅、蜻蜓、荔枝等FM正致力于移動聽書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被有聲化。
有人認為:有聲出版即將成為文化出版下一個關(guān)鍵點,幾乎已成為行業(yè)內(nèi)的基本共識[4]。目前我國各類聽書網(wǎng)站已有200余家,有聲聽書類APP已接近200款,很多電子書閱讀軟件也添加了“聽書”功能。我國有聲閱讀用戶規(guī)模也已突破1.3億。隨著“解放雙眼”運動正在贏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者,不少國有出版社也開始嗅覺敏銳地開展故事內(nèi)容與聽書平臺的合作。
實際上,從國內(nèi)出版社與聽書平臺的合作情況看,已經(jīng)有了不少的嘗試。據(jù)筆者了解,目前,除了浙江少兒社、長江少兒社,北京師范大學音像電子出版社、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上海教育音像出版社等多家出版機構(gòu)都與相關(guān)聽書平臺有合作。
四、有聲書會沖擊紙質(zhì)書嗎
一直以來當一項新的技術(shù)載體勢如破竹攻占市場后,一些人總夾雜著悲觀情緒預言一個行業(yè)的消亡,“電子書取代紙質(zhì)書,新媒體取代傳統(tǒng)媒體”。那么有聲書的繁榮火爆會沖擊紙質(zhì)書甚至電子書嗎?當人們紛紛解放雙眼后,是否還愿意拿起書來看?“聽書”是否會讓靜心閱讀的習慣受到挑戰(zhàn)?筆者認為,各取所需。對于文字閱讀有障礙的孩子、老人以及視障人群來說,“聽書”降低了知識獲取的門檻。新媒體閱讀將閱讀的平臺和渠道都做了進一步的延伸,這是好事,“互聯(lián)網(wǎng)為閱讀注入了社交元素——分享、互動、傳播,在讀者與讀者、讀者與作者的交流互動中,閱讀的價值被放大。至于閱讀方式,每個年齡階段,他自然會做出適合自己的選擇”。對于轉(zhuǎn)型期中的出版業(yè)來說,“聽書”豐富了數(shù)字出版的形態(tài)。有業(yè)內(nèi)人士認為,中國人喜歡紙質(zhì)閱讀,這是一項傳統(tǒng)。他曾為此做過一項調(diào)查,問到能不能接受聽書,受眾較為普遍的答案是:他們會將聽書與閱讀結(jié)合起來,不會一味地只聽或只看,兩者是有機結(jié)合在一起的。還有人指出,當數(shù)字出版與紙質(zhì)書平行發(fā)展,人們擁有更多閱讀方式的選擇時,聽書產(chǎn)業(yè)才有可能迎來發(fā)展的黃金期。
五、“一書三發(fā)”的時代會來臨嗎
如果我們關(guān)注歐美各國的圖書市場,會發(fā)現(xiàn)其中很多新書已經(jīng)做到了紙質(zhì)版、電子版、音頻版同步發(fā)售。近兩年國內(nèi)出版領(lǐng)域的一個大趨勢是,很多最新紙質(zhì)圖書出版后,電子版也相繼在各大閱讀平臺上發(fā)行,可以說這幾乎形成了同步趨勢,而聽書市場相對而言則要滯緩一些。未來,我國“一書三發(fā)”的時代會來臨嗎?
在2013年作為以內(nèi)容出版為核心的酷聽就已經(jīng)將這一想法付諸行動了。2013年酷聽在騰訊文學電子書下有了“此書可聽”的選項,與中國移動開啟了“有聲同步”合作。此外,酷聽網(wǎng)站與APP上,原創(chuàng)作者在更新章節(jié)后,酷聽能夠保證跟進錄制,實現(xiàn)了“同步”功能。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有聲書業(yè)尚處于起步階段,要想做到“一書三發(fā)”,有聲書的版權(quán)問題、贏利模式是兩道必須跨過去的坎。與視頻類網(wǎng)站、電子書的發(fā)展類似,版權(quán)成為有聲書應用的發(fā)展瓶頸之一。目前,有聲聽書類APP博弈激烈,他們或多或少都陷入了侵權(quán)風波。從用戶自制節(jié)目到網(wǎng)站購買版權(quán)和自制生產(chǎn),版權(quán)是有聲書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未來發(fā)展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因素。此外,贏利模式同樣令人擔憂。英美有聲書市場一直都是收費狀態(tài),盡管收費方式不一,如零售、無限訂閱、捆綁銷售以及圖書館銷售等方式,但價格不低于紙質(zhì)出版物,美國的有聲書平均價格在20美元左右。這與英美多年來通過磁帶、CD等介質(zhì)消費有聲讀物的習慣有關(guān),2014年美國仍有30%的有聲讀物是通過磁帶或CD銷售出去,2015年英國的這個數(shù)字是40%。[5]與國外相較,我國有聲書運營模式也有按下載量付費、買斷、預付加分成付費幾種類型,比如“喜馬拉雅”、“懶人聽書”等多家聽書平臺都有優(yōu)質(zhì)內(nèi)容的訂閱收聽。雖然上述某知名市場調(diào)研機構(gòu)的有聲書市場報告也給出了2015有聲書收入規(guī)模數(shù)據(jù)及其對2016年該市場收入的預判,但不可否認,有聲書市場主流仍是依靠廣告等“吸金”,用免費的內(nèi)容吸引流量的“免費餐”,目前仍處于資本輸血階段、燒錢狀態(tài)。
除了上述兩個重要因素,筆者認為成熟的制作團隊尤其是優(yōu)秀的朗讀者也是一大缺位。有聲書并非簡單地朗讀文字,而是由撰寫錄音方案、分設角色、融合背景音樂、制作特效、成品剪輯等步驟完成的一種有別與紙質(zhì)圖書、電子書的全新的內(nèi)容呈現(xiàn)形式。可以說,一本書從文本到高質(zhì)量的音頻產(chǎn)品,平均要經(jīng)歷一個月到一個半月的制作。
因此,在短期內(nèi),所有的最新紙質(zhì)圖書完全實現(xiàn)有聲書的同步發(fā)行,實現(xiàn)“一書三發(fā)”,也許還要走一段很長的路。盡管如此,筆者認為有聲書的市場前景仍然值得期待。這項新技術(shù)的出現(xiàn)極大地豐富了“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中的人們的閱讀方式。亦如僵尸小說《末日之戰(zhàn)》的作者馬克斯·布魯克斯說:“新技術(shù)非但沒有毀滅某一藝術(shù)形式,反而使它得到復興,這在歷史上并不多見,有聲讀物應該就是其中之一。”[6]
注釋:
[1]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xiàn)代漢語詞典(第5版)》,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1684頁
[2][3][5]龔牟利:《有聲書爆發(fā),出版界波瀾不驚?》,《中國出版?zhèn)髅缴虉蟆?016年3月29 日
[4]http://culture.china.com/11170621/20150821/20243724.html
[6]王炎:《歐美明星熱衷錄制有聲書 有聲讀物成出版界新寵》,《北京晚報》2013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