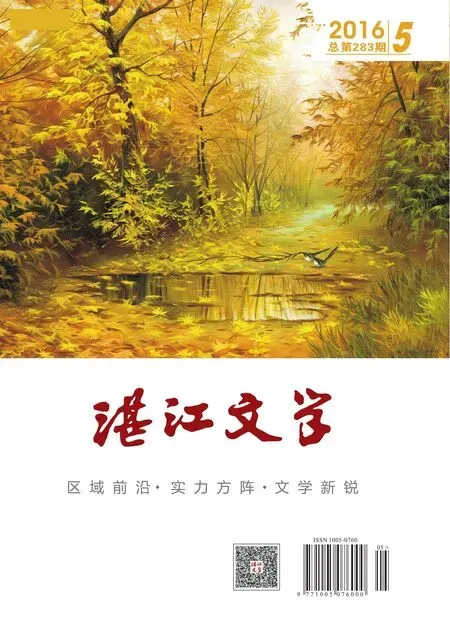不敢閑的父親
※ 李百合
不敢閑的父親
※ 李百合
當年生產隊的馬圈位于整個生產隊大院的西部,占據整個大院四分之一的面積,大約有十五六間房子的樣子。那個年代的房屋結構基本上全部是堿土房結構的,墻壁是由黑土脫成的坯壘成,房蓋多是用高梁秫桿棚成,上面抹上幾層堿土。最靠東邊的一間小屋能住人,是供飼養員休息的地方,最靠西的一面有兩間專用來存貯飼料的房間,南墻有窗,用幾根木棍支撐著的窗欞七零八落,便于里面堆積的草料貯存通風。主體區域是中間的部分就是供馬和牛“食宿”的地方,分為兩部分,一面用來栓馬,一面用來栓牛。馬大約有五六十匹,牛大約有三十頭左右,物以類聚地各置一側非常分明。生產隊的飼養員又稱“馬倌”,但那個時候的大多數人都稱其為“老更倌”,雖說那時候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專門“打更”人員,但還仍然是這么個叫法。父親是生產隊的老更倌,小時候上學之前的我,基本上一直常常年伴隨在父親的身邊,那股子悠悠馬糞的騷臭味,那種牛馬咀嚼草料時牙齒發出有節奏的磨合聲,父親用木棍攪拌草料的聲音、吆喝牛馬的聲音,那幾堵黃泥抹就的陳年老墻,成為我一生從視覺到聽覺,再到嗅覺都無法抹卻的記憶。
當年,我家人口最多的時候有十二口之多,這在當時是為數不多的,雖然那時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家家人口多。人口多、勞力少,所掙工分支付不了年終分配口糧的現象,稱為“脹肚”,這種人家稱為“脹肚戶”。我家是全村有名的脹肚戶,為了盡量減小“脹肚”的程度,讓全家人吃飽,父親挑選了在生產隊最吃辛苦的這種工種,不分白天黑夜地勞作著。他的勞動工具是一副扁擔,外加兩對挑糞和挑草用的柳條筐,還有一對用來挑水用的“喂哆鑼”(俄語音譯,一種小水桶)。
父親的扁擔是用榆木制作的,被父親的肩膀磨得光光的、滑滑的,悠悠地發著光亮。時常記得父親挑糞的情行,個子長得比較矮小的父親,把扁擔鉤往兩只筐梁上一吊,兩只手搭住扁鉤,身子略屈,一挺腰桿把裝得滿滿的兩筐牛馬糞挑起。長長的扁擔在父親的肩上,仿佛具有了神韻一般,悠悠地顫動,發出不知是筐子還是扁擔傳遞出的輕微的顫動聲。父親出了馬圈,一路走出三十米遠,把糞肥倒在生產隊的大糞堆上。日復一日,生產隊的大糞堆堆起了十幾米高,像一座小山般矗立在生產隊的大院里。每天牛馬下地干活后,從馬圈里起糞、挑糞是父親必干的一種活計。外生產隊這種活多是配備專人打理,父親為了多掙工分,減少了休息時間,增加了勞動強度,竟然一人把這個活計擔起。長長的扁擔立起來,要比他的個子還要高。兩只裝糞的筐子高過父親的膝蓋,父親矮小的身體從馬圈到糞堆,從糞堆到馬圈,來來回回,每天都要走上四五十個來回,才能把馬圈清理干凈,看父親每天忙碌的情形,仿佛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力量榨干,拚了命一般。
挑完糞的父親,把筐子在馬圈的泥墻上磕凈,坐在馬圈墻跟下擺放著的一條長長的、寬寬的板凳上,從衣兜里掏出母親給他縫制的煙口袋上,裝上一袋煙,長長地吸了一口,之后一股濃煙從他嘴里噴出,直直的、長長的、悠悠的,一種勞累后的愜意掛在父親汗水凝固得亮亮的臉上。

父親屁股下的板凳長兩米,寬三十公分,高八十公分,是全大隊最長最寬的板凳,是多年前用老榆木做成的,外表粗糙,但質地非常好。這條板凳的作用非常大,不但可以當做人們休息的工具,還可以作為各種工具供全隊的人使用。父親在板凳的一頭,釘了一塊帶有牙齒的角鐵,可以在牙齒前頂著磨刀石、頂住木方等進行磨刀和刨木頭。父親是全大隊有名的能工巧匠,一人多能,拿老百姓的話說,非常“專技”。他不但熟稔于所有的農活,還會木匠、磨匠、織匠等活,做出的活計也堪稱一絕。
父親是半個木匠,說他是半個木匠,是因為他沒有拜過師,完全是自悟的。具體一點涉及細加工、精加工的木工活父親做不了,但像一些做個車“剎箱板子”、犁杖、牛馬套、小桌椅板凳什么的不需要太專業的木工活他都會。每年犁地前后,或收獲的前后時間里,父親的身影就要忙碌在這條寬寬的板凳旁,木方一條條地在板凳上刨出好看的刨花,發出好聞的木香味,各種工具或擺放在凳子上,或擺放在凳子下,父親勞動起來非常有條不紊。這些勞動都是他本職工作以外的活計,打一套車給多少工分,打一個爬犁給多少工分,打一套剎箱板子、絞椎等等生產隊按勞動量大小給不同的工分,別看這些小活,積年累月積累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我所說的磨匠活,分為兩種,一種類似于石匠。生產隊有兩架石磨,一架是磨房里碾米用的石磨,一架是豆腐坊磨拉豆腐的石磨。石碾和石磙要定期打磨才能培加磨合力。父親用磨石的專用工具鐵鑿把幾近磨平的石碾石磨等的凹面打深打細,叮叮當當,鐵錘撞擊鐵鑿的聲音,仿佛全隊人都能聽見,石碾石磨等崩起的石灰染白了父親的雙眉染白了父親的黑發,染白了父親那古銅色的臉。父親說一有這磨石活,滿嘴都是這些石頭粉末,怎么漱口都洗不凈,吃飯的時候要牙磣好幾天。不但有這兩架石磨要磨,隊里還有大小近二十多個打場用的石磙要磨,所以在我印象當中父親好像一年四季都沒有閑著的時候。永遠記得父親端坐在板凳之上打磨石盤石磨的情景。父親一手緊握鋼鑿一手輪動鐵錘,神情非常專注,那叮叮當當聲非常有節奏,像賦予了一種神韻,不亞于一種非常高超的打擊樂。長大后的我,感覺父親當時的情景仿佛置身于遠古時代,一處打石場匠人們不斷勞碌,是一種古樸和厚重的穿越。父親說這種活,鑿子在石頭上要定好位,一錘子下去,既要準又要穩又要狠,打偏了用力小了都影響效果。
磨匠的另一種工種是磨豆腐。社員們開父親的玩笑說,他既能磨最硬的石頭,又能磨最軟的豆腐。父親做的豆腐在周圍十里八村都是最好的,質地不但細膩,口味還非常不錯,家家戶戶都最愛吃他做的豆腐。父親做豆腐也是一種額外的工種,但這種活不是一個人能忙乎過來的,父親領著他的小徒弟,也是我本家的一個大侄子一起才能完成。本家大侄子因跟父親學了幾年,最后能獨擋一面,到生產隊解體時居然承包了隊里的豆腐坊做起了專門加工豆腐的生意,一時在周圍十里八鄉成了有名的豆腐匠。做一個豆腐生產隊給半個工六分,無疑父親因攬了做豆腐的活,又增加了一份額外收入。父親做豆腐要擠時間做,每天晚上父親忙完上半夜喂馬的一些活計之后,緊接著就要準備泡好做豆腐用的黃豆,備第二天早晨磨豆腐用。磨一板豆腐需要很多水,父親用他那副喂哆鑼挑完給牲口拌料用的水之后,還要挑夠做豆腐的用水,往往兩項用水達到二十多桶,缺油的轆轤發出的沉重嘆息聲,扁擔落在肩上輕顫聲,父親擠夾豆腐包的聲音,仿佛定格在了我的記憶深處。

織匠有如南方的蔑匠,那個年代干什么活一色靠的是人工,睡覺鋪的炕席要人工編織,運土裝糧食的筐需要人工編織,屯積糧食用的茓子需要要人工編織,就連人戴的帽子、醬缸上戴的帽子都是靠人工編織而成。家里的還是隊上的編織活,父親都是坐在這條板凳上完成的。炕席、帽子等要把高粱秫秸破成高粱批兒才能編。父親先是把高粱桿涸濕幾天,之后用“破子”(一種內三棱工具)把一根秫桿一破成三掰,用鐮刀頭把每掰里面的瓤在板凳上刮凈,之后剩下的批兒才能用來編炕席。給生產隊編炕席編茓子都不白干,生產隊要給工分的,這又成了父親增加額外收入的另外一種途徑。生產隊的用筐大多是父親編織的。父親編制的筐,不但樣子美觀,而且還結實耐用,一天能編制七八只,是全村有名的快手,提起編筐織簍的沒有不服他的。
家里孩子多,屎一把尿一把的或在炕上玩就非常費炕席,所以,我家南北大炕兩鋪,一年要用上四檁炕席,父親除了編家里的、編隊上,還要趕著幫年跟前多編上十幾檁炕席拿到集市去賣,趕上好年頭,一檁炕席能賣上三、四塊錢,這在當時來說可算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了,全家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的零用花銷,不能只指著僅有的幾個母雞的雞屁股下的那點兒蛋活著。那時錢實得狠,兩個人花個八、九毛錢,能下一頓挺好的館子。
父親是一個閑不住的人,也是一個不敢閑的人。拿他的話來說,一閑下來,心里就忙得慌,這好像成了他一生中的一種“病”,他是“不能閑”又“不敢閑”的人。一些活計忙完之后的夏季歇鋤時或冬季貓冬時,父親和他的板凳也不閑著。父親磨刀快而鋒利,全屯的人都愛找他磨,這一項父親不收費,拿上求他的人遞過來的紙卷關東煙,父親一口唾沫唾在磨石上,“噌噌噌”一天也不撈閑。一把笨鈍的刀,經他磨拾仿佛具有了靈性,一刀剁在硬硬的豬排骨上:“這!老更倌的刀就是磨得好,你看看你,跟人家老更倌學學,人家這刀磨的。”家里的老娘們就數叨著自己的老爺們。老爺們就假生氣說:“我愿意!你看老更倌好,你跟老更倌過去啊!”老娘們翻了一下眼,白了老爺們一眼,一臉的不屑。父親聽到這句話就樂得嘴都合不上了,他的前門牙不大,但都露出兩個小豁口,小時候大鼻涕狼湯的我,怎么瞅他的這種笑有點奸詐的味道。于是我也跟著笑,全家人一看我笑得鼻涕流得挺老長的,也都哈哈大笑起來。
“老更倌,看你一年到頭沒有閑著的時候。”有人說。
父親抬起頭來,看了看這個人,之后長長嘆惜了一聲:“哪敢閑啊,家里有十個‘嗷嗷’待哺的狼崽子呢。不干活他們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全家人喝西北風啊。”父親正因為有了這種信念,所以他不敢閑,閑下來就心里忙得慌。
父親得病的那天早晨,是剛剛拉了一早晨磨回到家才倒下去的。我們一家十幾口仿佛失去了主心骨一般圍在他的身邊。父親得的是腦溢血,不能吃不能喝,全身都動彈不了。但盡管如此,在他稍微明白點的時候,含混不清地發著音,不是好眼色地看著幾個哥哥們。最后母親解釋了一句大家才算明白過來。父親的意思是說,日頭都老高了,咋還不都出外挎筐撿糞呢?多撿點兒糞,交給生產隊,就能多得工分的。我們幾個嚎淘大哭。不敢閑的父親,即便是在他冥留之際,念念不忘的還是勞作勞作再勞作,掙工分掙工分再掙工分。
從得病到去世僅八天時間,這八天有可能是他作為丈夫、作為父親一生僅僅唯一閑下來的時間。那根磨得光光亮亮的扁擔,那條斑斑駁駁的板凳,似乎見證了父親一生為人的一種責任一種擔當的偉大!
李百合,男,漢族,1967年3月出生,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老年日報特約專欄作家,《小說閱讀網》《網易云閱讀》簽約作家,曾被聘為綏化日報星期周刊特約撰稿人。出版過長篇小說《天生我材之關東匪后》,發表網絡長篇小說《大堿溝》,在《黑龍江日報》《農村報》《黑龍江林業報》《黑龍江晨報》《黑龍江工人報》《黑龍江科技報》《作家報》《當代散文》《作家選刊》《中國鄉土文學》等全國各地報刊、雜志發表文學作品近二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