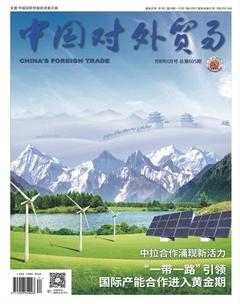中國外商投資法律修訂完善迫在眉睫
金善明
外商投資在我國市場經濟建設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無論是在資金引進,還是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的導入等方面,都立下了汗馬功勞。當初,為了吸引外資、保障外資安全,我國先后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等俗稱的“外資三法”。毫無疑問,“外資三法”為中國對外招商引資、維護外商投資秩序、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但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改革開放的深化,“外資三法”卻逐漸成為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掣肘之處,制約甚至束縛了我國開放型經濟體制的推進與發展。因而,對現行外商投資法律體系予以改造和完善,營造統一、公平、有序、規范、透明的投資法治環境,便成為當下經濟體制改革和法治建設的當務之急。
外商投資立法轉型的必然與訴求
“外資三法”是我國改革開放后最早啟動的經濟立法,是回應外商投資法制需求的產物,為鼓勵、保護和規范我國外商投資行為提供了制度依據和保障。但隨著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加劇,我國利用外資不斷從追求數量向講究質量轉變,這亦相應地對我國外商投資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我國保質高效利用外資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一方面,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提出了新的制度訴求。改革開放之初,無論是資金實力還是技術水平,較西方工業化國家相比,我國都不占優勢,因而以市場換技術、引資金等方式改變國民經濟落后狀況成為必由之路。但彼時法律制度整體缺位的情形下,招商引資談何容易?因此,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的構建便成了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本著“摸著石頭過河”的精神,我國相繼出臺了“外資三法”,對外資準入門檻、組織形式、監管方式等內容作了粗線條的規范,雖不夠細致但也為我國利用外資提供了制度依據和保障。
當前,我國經濟體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對外資利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從過去一味強調引進外資的數量轉向注重外商投資的領域與技術含量等質的要求,更加偏好外商投資與國內既有資本運營形成互補,尤其青睞高新技術產業的資金導入和技術引進。顯然,這對現行的外商投資法律制度也提出相應的更新要求,以應對經濟轉型升級之需。與此同時,我國市場經濟建設進程中,利用外資的形式紛繁復雜,甚至不乏規避法律約束的模式或方式,但因對國民經濟發展亦作出了不容否定的積極作用而成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要求國家從法律層面對其予以定性并給予合理的保障。可見,國民經濟發展的現實,對現行外商投資法律制度不斷提出新的挑戰,以滿足經濟生活中積極的制度訴求抑或應對消極的行為狀態。
另一方面,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需要妥善的法治舉措。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適時提出“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從制度機制層面要“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保持外資政策穩定、透明、可預期”,“改革涉外投資審批體制”,“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隨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從法治層面上要求“適應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完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促進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是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頂層設計,但其具體的實施路徑則有賴于具體的法治化措施,也就是如何從推進內外統一立法、優化外資準入機制、完善外資監管模式等內容法制化,從而為開放型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完善提高法治保障。由于現行的外商投資法律體系龐雜甚至不乏沖突,內外資雙軌立法、內外資差別待遇、外資企業“超國民待遇”與“次國民待遇”并存等現象屢見不鮮,與全面深化改革、構建新型開放經濟格格不入。因此,外商投資法律的修訂完善不僅必要,更顯緊迫。
此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后多區域、多領域地推進和實施自由貿易區建設戰略,先后批準設立了上海等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不斷探索深化對外開放、建設開放型經濟的新思路、新規律,力圖把握我國對外開放的新要求和經濟全球化的新趨勢。為了解決因法律滯后而帶來的束縛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相繼在2013年8月和2014年12月通過決定,授權國務院在上述自貿區暫停實施“外資三法”規定的部分行政審批事項,改為備案管理。其中,有關上海自貿區授權決定規定,上述改革措施“在3年內試行,對實踐證明可行的,應當修改完善有關法律”。如今大限將至,國家應依據上述授權決定對相關自貿區規定進行評估,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及時將相關制度和經驗轉化為國家法律,以便復制和推廣。
外商投資立法的過渡與體系重塑
外商投資法律制度的修訂與完善,既是我國開放型經濟建設的現實需求,亦應是國民經濟建設進程中外資利用的經驗總結與制度化體現。應該說,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經驗與制度建設,能夠為外商投資立法的優化提供豐富的知識儲備和積淀。但在中國,由于諸多限制或條件約束,修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并不足為奇。“外資三法”的修訂也非例外,早在2014年國家就啟動了外商投資法的修訂工作,但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的自貿區“外資三法”部分暫停實施期限即將到來之際仍未完成外商投資法的修訂工作。因此,為了消除潛在的法制尷尬,全國人大常委會方才智慧地將在中國自貿區內實踐的試點措施上升為法律。即在“外資三法”(實際上,還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中分別增加一條規定:對不涉及國家規定實施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的,將相關審批事項改為備案管理;國家規定的準入特別管理措施由國務院發布或者批準發布。同時要求,重新公布的“外資三法”也將終止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述授權決定的法律效力。
毫無疑問,這一修法決定并非我國外商投資立法轉型的終結,而只是權宜之計。因為這一修法設計并未有效滿足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頂層設計和要求,亦未完全將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所要求的外商投資統一立法、清單管理模式等內容規范化、法制化,因而只能說是為了應對即將到期的授權規定而作出的應對之舉。因此,外商投資修法的工作仍需依舊,尤其是“三法合一”、外商投資統一立法的思路與模式并未改變,也不能改變。相應地,我國仍應以黨的十八以來所確立的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為目標,結合國內自貿區實踐和國際貿易投資條約等因素,加快推進外商投資法律的修訂。
具體來說,我國外商投資法律的修訂應積極貫徹“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的指導方針,將統一規范、清單管理模式納入法治范疇,將三法分立模式重新改造、統一立法并命名為《外國投資法》。在此名之下,重塑外國投資立法的體系并理順其規制范疇,將立法重心聚焦在外國投資的界定標準、準入制度、監管機制、清單管理模式、糾紛解決等方面,而將有關企業注冊登記、治理結構等內容回歸公司法范疇。這實際要求我國外國投資立法應摒棄當下逐案審批制度而轉向實際控制制度,通過清單管理模式加強對外國投資企業的事中事后監管,從而賦予外國投資的充分自由并激發其利用效率;與此同時,為了防止產業損害、維護國家安全,外國投資立法應設立相應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以代替和完善當下僅在《反壟斷法》第31條所規定的外資并購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外國投資法》的制定與頒布,將是我國外商投資立法的重要轉型。但因外商投資在國民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外商投資的治理與監管,亦遠非一部法所能治。《外國投資法》的倡導與制定,僅僅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法治舉措。其制定得科學合理,將有助于我國提高外資利用效果、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其出臺后得以有效的實施,方能實現十八大所提出的“開放型經濟體制”目標、促進經濟增長、提高社會福利。然而,這是一項系統工程,在推進外國投資立法的同時,更需要通過實施《反壟斷法》等市場規制法來維護市場自由,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法治政府建設,以為外國投資提供更好的制度空間和秩序環境,從而真正實現外國投資為我所用、為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