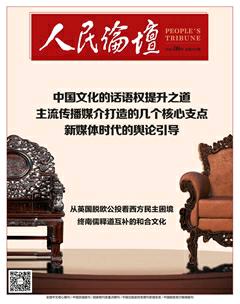微信平臺下隱私權憲法保護
黃明慧
【摘要】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核心是人格尊嚴,屬于憲法范疇的公民權利。在隱私權發展過程中,我國憲法和法律對它均有不同程度的規范,但是也還有待進一步憲法解釋和部門法細化,圍繞著隱私權保護的主題,設計憲法解釋路徑和憲法監督路徑以達致憲法權利保護的理想狀態。
【關鍵詞】微信 憲法 隱私權 憲法路徑 【中圖分類號】D911 【文獻標識碼】A
微信社交平臺正越來越豐富著人們的網絡交流。伴隨著微信不斷拓展事業版圖,微信網絡對公民的憲法權利所產生的雙刃劍效應愈發凸顯:一方面,快捷方便的微信充分體現了《憲法》第35條賦予公民的言論表達自由;另一方面,微信也可能成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侵犯公民隱私權的不當工具。因此,我們在贊許微信帶給人們生活便利的同時,也應當高度重視微信網絡平臺下公民隱私權的憲法保護問題。
微信平臺下隱私權的憲法屬性
研究隱私權的保護應當先明晰其法律性質,以便于我們選擇對應的法律保護措施。我們認為,微信平臺下研究的隱私權應當確定為憲法屬性。
第一,隱私權的核心是公民的人格尊嚴,屬于我國憲法文本規范的公民基本權利內容。微信網民在虛擬空間的訊息交流,由于支持網絡的技術平臺就掌握在有信息網絡行政管理職權的機關、部門手里,存在可以在網民都不知情的情況下任意處理微信網民的隱私可能。也就是說,微信涉及的隱私權已經突破了私法疆域進入憲法調整范圍,如果要恢復受侵害的隱私權只能通過憲法來救濟、保護公民的人格尊嚴。因此,微信空間的公民隱私權應當歸納為憲法基本權利屬性。此外,隱私權的核心之所以是人格尊嚴的保護,原因在于只有國家公權力充分尊重公民的隱私,確保公民能依照自己的真實意愿決定自己的生活和事務,才能在這個社會培養出理解和包容個人多元價值觀的氛圍和法治環境,才能實現社會文明程度持續提升、公民精神追求不斷提高的理想憲法狀態。
第二,隱私權理論與實踐發展至今,其內容已經從民法權利拓展到憲法權利范疇。隱私權作為法律概念第一次出現在《論隱私權》(1890年《哈佛法律評論》)的時候,是用作一種民事權利來解讀的;在1905年后,美國通過一系列法院判例,確認了隱私權屬于一種民事法律權利。到了20世紀,人類社會迎來了互聯網信息和自媒體時代。在復雜的社會競爭與網絡信息的發展背景下,隱私權逐漸適應形勢由民法權利提升為憲法的權利,標志性事件就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65年的判例中,確認了隱私權是憲法范疇的獨立權利。另外,我國法律權利體系是以憲法權利為基礎搭建的,憲法(1982年)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體系(包括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是其他部門法所保護的法律權利的基礎。也就是說,憲法隱私權的內容除了自然人個人生活的私密空間,還規制公民與國家機關、社會組織之間圍繞公民人格尊嚴所發生的憲法法律關系,它涵蓋了民法范疇的隱私權,民事權利的隱私權只是憲法范疇隱私權的具體化。
第三,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本質上已經是一項憲法基本權利,應當依靠憲法公力救濟才能獲得全面的法律保護。現在,隱私權已經成為一項國際社會、多國憲法普遍承認、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也就是說,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本質上已不再是民法意義上消極的、獨處的權利,而是一種由公民積極的、能動地操控支配和利用個人隱私的權利。從憲法的層級來設計微信隱私權保護,可以規范國家、政府和社會組織以及網民的實質言論表達,這樣既能更好促進言論自由,也保護了普通網民的隱私權。因此,隱私權的保護從私法保護級別(防止其他自然人的侵犯)提升至憲法保護的高度(防范、抵御來自國家機關和公權力的侵犯),目的是為國家、政府設置一定的積極作為義務,以強調國家、政府應當主動為保障公民隱私權的落實而采取有效措施;甚至可啟動違憲審查機制來防止、糾正公權力機關侵犯公民隱私權的情形,更好地實現隱私權的憲法保護。綜上,微信網絡環境下的隱私權的法律性質應當是憲法權利。
我國憲法和法律關于隱私權的規制現狀
作為我國法律體系根基的憲法關于隱私權的規定情況。我國憲法文本(1982年)沒有規定“隱私權”條款,但是在《憲法》第33條明示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總原則,接著在《憲法》第38條規定隱私權的核心——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然后又在第40條規定了“……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的內容。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整體,這些憲法文本的規定就是隱私權的憲法基礎,為我國法律保護隱私權奠定了一個理論基礎。
但是,我國憲法沒有進一步列舉公民一般人格權(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名譽權、肖像權等等)的具體內容。另外,由于憲法文本沒有明晰隱私權的具體內容,在實踐中,部門法(如民法、刑法等)在規范隱私權的時候就難免存有是否抵觸上位法的擔憂;而隱私權的受侵害方在尋找法律依據的時候,由于在上位法中找不到根據轉而在下位法查找條文也會擔心究竟是否切中隱私權保護的要害。最后,我國的司法審判慣例是不能直接適用憲法條文作為判決依據的。依據就是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裁判文書引用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的規定》之第4條,這項規定使得隱私權的受侵害方在尋求司法救濟的時候,由于司法判決不能援引上位法的規定而依靠下位法(侵權責任法、刑法)的條款來作出判決,結果顯然是缺乏憲法權威和法律說服力的。這樣的司法審判體制也不利于公民隱私權的全面法律保護。
我國部門法對隱私權的規制狀況。目前各部門法關于隱私權保護的還是缺乏系統、專門的法律規范,都是零散的分布在各個部門法的個別條款中,一是《民法通則》規定了精神性人格權(姓名、肖像、名譽權)沒有規定隱私權條款,但是卻在一系列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對隱私權做了可操作的規定。比如,《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1988年4月)的140條和《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3月)第1條第二款的規定,都明確的提出了“隱私”的法律概念。二是《侵權責任法》(2009年12月)第二條首次規范了“隱私權”,把對隱私權的規范從司法解釋的層面上升為專門法律的層次,也把追究侵犯隱私權的法律責任擴大到普適性的民事侵權責任,這是一次質的飛躍。三是除了民事方面的法律保護,刑法、行政法和社會法領域也散布著關于隱私權保護的規定。如,《刑法》(2011年修正)第245條、252條以及253條的罪名規定,《執業醫師法》(1998年)第22條、《律師法》(2012年修正)第38條、《婦女權益保障法》(2005年修正)第42條和《居民身份證法》(2011年修正)第6條規定,都在獨特的領域貫徹著憲法隱私權的原則,構成一整套的隱私權法律保護體系。此外,互聯網行業法規、規章也有零星的隱私權方面的規定。如,國務院《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2000年9月)第15條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維護互聯網安全的決定》(2000年12月)第4條的規定以及信息產業部《電子認證服務管理辦法》(2009年2月)第20條的規定,都對自媒體(包含微信)的網絡隱私權問題作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規制。
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保護的憲法路徑
微信網絡的虛擬性、訊息傳播的快捷性情況,使得公民的隱私權受侵犯的可能性增大。為了構建誠信安全的微信法治秩序,將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納入憲法的保護刻不容緩。
隱私權保護的憲法解釋路徑。上文提到我國憲法文本欠缺“隱私權”條款,導致我國隱私權保護出現上位法缺位,下位法亟需上層指導的情況。于是有人就認為,隱私權保護就應當先修改憲法,把隱私權的內容增加到憲法文本中。但是,筆者以為憲法修改可以慎重,應當首選憲法解釋的路徑來解決隱私權保護問題。理由是:第一,憲法修改雖然在表面上短平快地滿足了人們把隱私權“寫入憲法”的急切想法,但是,隱私權內涵、外延還會隨著自媒體的迅猛發展衍生出新的內容,所以,憲法文本每一次修改完畢頒布之時就是憲法文本落后于時代腳步之日。因此,與其不停地修改憲法倒不如充分激發憲法解釋的彈性機制,把未列舉的隱私權通過權力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做出法定解釋,實現隱私權內涵、外延的與時俱進。
第二,憲法修改實質上屬于“制憲權”的一種形式轉化,憲法修改,需要再三斟酌、謹慎選擇。如果一部代表全體人民意志的憲法經過法定制憲程序制定實施了,而民意機關(不等于全體人民)通過憲法修改的方式把憲法的內容(有可能是制憲主體堅持的憲法精神)刪除或增加或變更了,那么修改之后的憲法文本是不能完整地體現制憲主體(全體人民)的真實意志的。這樣的憲法修改帶來的后果,有可能是嚴重損害了憲法的權威和尊嚴,也有可能因為頻繁地修改影響了憲法的穩定性,從而破壞了法的安定性,侵蝕了公民的憲法信仰,甚至有可能引發憲法秩序危機。
第三,憲法解釋更有利于實現隱私權保護。憲法解釋路徑符合《憲法》第67條關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規定,契合我國“議行合一”的政治權力體制,運行起來合憲合法,可能遇到的政治體制阻力會比較小,推行起來應該比較順暢,適于通過關于公民隱私權的權威解釋引導司法實務界審理涉及微信空間隱私權的法律糾紛,實現隱私權的憲法保護。具體步驟可以設計為,有權解釋機關(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法定程序,依據憲法文本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原則,推演出隱私權的核心“人格尊嚴”作為評判微信網民的言行是否侵犯其他公民隱私權的標準,并以此憲法解釋為司法審判提供權威參考,最終實現憲法解釋在司法審判中得到援引,達致隱私權的憲法保護效果。
隱私權保護的憲法監督路徑。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動態嬗變過程,可能還會有花樣翻新的侵權形式涌現,因此,隱私權保護不僅要化解來自私域(平等民事主體)的法律糾紛,更需要防御、規范、審查國家公權力(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對隱私權的侵犯;而要規范國家公權力的行為,在人類社會現階段只能啟動憲法監督機制。憲法監督就是有權審查機關依據憲法對國家機關、國家領導人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事業單位、組織、團體的法定職權行為進行合憲性審查,目的是保障憲法的原則和規定得到落實。據此,隱私權的憲法監督路徑應當分三步走:第一步,專門的憲法監督機關對涉及隱私權的普通法律、法規和規章進行合憲性審查,以憲法人權和人格尊嚴的核心價值來評估抽象性法律文件是否侵犯了公民隱私權,然后對違憲的法律文件做出具有效力的處理,主動消弭立法權侵犯公民隱私權的風險;第二步,專門的憲法監督機關審查行政機關對微信自媒體的職權管理行為,規范約束行政機關涉及公民隱私權的具體行政行為,落實隱私權的保障。第三步,專門的憲法監督機關從國家制度層面確保司法權獨立,讓司法機關真正能依照憲法、法律,不受來自其他公權力機關干涉獨立審理隱私權案件,守住公民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關口。
結語
微信平臺下的隱私權保護任重道遠,囿于篇幅,本文只能淺顯地在憲法屬性的隱私權范疇結合我國隱私權憲法、法律規范的狀況提出保護隱私權的憲法路徑。以憲法視角解讀隱私權的保護問題,目的在于為研究和落實公民隱私權奉獻綿薄之力。
(作者單位:嘉應學院政法學院)
【注: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學科共建項目《如何構建憲法實施的司法路徑》階段性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GD14XFX10】
責編/張蕾 美編/楊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