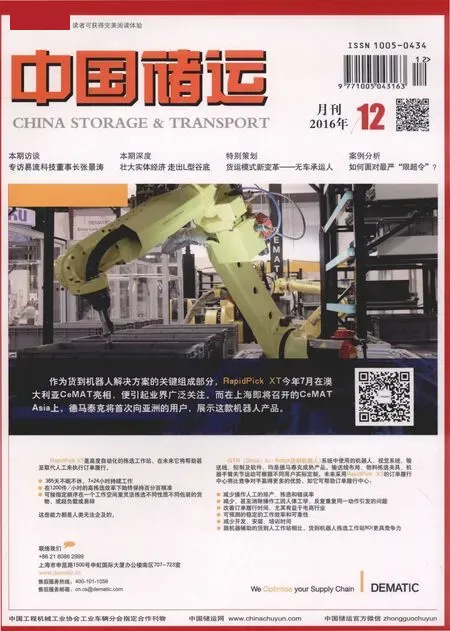無車承運人的前世今生——專訪中國物流采購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任戴定一
文/本刊記者王悅
特別策劃│貨運模式新變革——無車承運人
無車承運人的前世今生——專訪中國物流采購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任戴定一
SPECIAL SCHEMER
文/本刊記者王悅
2016年的10月,無車承運人試點工作的啟動,帶動貨運領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更是給眾多的信息平臺型企業帶來了更多的發展契機。由于業務類型差之毫厘,有人把貨運信息平臺型企業看做是無車承運人的“前世”,升級只在獲得資質之間。眾多平臺都在為了獲得資質而翹首企足。
另一方面,試點工作剛剛啟動,無車承運人制度尚不完善,這種資質是否需要在摸索中建立?需要通過哪些方面的審核,才能獲得所謂的資質?本刊記者帶著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物流采購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任戴定一,請他為讀者揭開疑惑。

貨運信息平臺與無車承運人
平臺屬于商業機構,在一個小范圍、一個專業領域里,客觀地承擔著某種政府過去所承擔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無車承運人是沒有車但能夠承接運輸的業務,具有開具運輸發票的資質。二者之間是從不同角度切入的,平臺可能是無車承運人、也可能不是無車承運人。戴定一指出,“是否具有開具運輸發票的資質,也就是能否跟客戶簽訂運輸合同,是劃分二者的本質區別。”
過去的平臺企業停留在信息的撮合,到一定程度時,企業會發現,再有余力、再有投資也始終無法繼續壯大。因為沒有承擔交易,所以現在的平臺型企業都在向交易方向延伸,只有交易,才能有涉及更多的流程的監管,從而獲得支付等增值的可能性。因此,所有的平臺都在向電子商務的方向發展,但這時企業就碰到一個問題,平臺企業沒有簽訂合同的資質,也就是在平臺上發生交易的資質。然而,如果主體雙方直接產生交易,平臺型企業仍然是提供信息系統的服務商,那么平臺型企業無法獲得實際利潤點。
戴定一強調,“無車承運人政策,實則是解決了行業內‘只想拿好處,不想擔責任’的問題。”平臺型企業必須把自己推出去,只有置身交易環節之中,與雙方都簽訂合同,扮演交易風險的承擔者,通過拼單、湊單和方案設計等方式(例如承接貨主方三單,賣給承運方一單),才能留出利潤空間。這樣的社會分工模式為企業的業務深入發展提供更多機遇。無論是對于客戶,還是對于資源的充分利用,都是一種有效的方式。
無車承運的模式來源于無船承運。海運市場上由于船的運載能力巨大,整船運力的直接交易很難形成,于是產生了中間人,整合零散需求后再集中購買運力。公路貨運也沿襲這樣的模式,一方面是公路貨運需求的碎片化需要整合,另一方面無船承運的模式已經比較成熟,效率的提升和責任的清晰、風險的控制是可以兼顧的。
然而,這一切都還是需要回歸到中間人參與交易和運輸資質兩個方面,也是決定平臺型企業是否能夠升級為無車承運人的關鍵所在。戴定一向記者透露,“以往在這種情況下會衍生出很多灰色經濟。無論是信息平臺還是第三方物流、貨代都會做一些無車承運人的業務,只是不合法或者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獲取運輸發票。這種灰色模式早就存在了,實際造成了行內很多不規范行為的發生。”
同時,戴定一糾正了一個誤區,他強調,“無車承運人不完全屬于‘輕資產’,雖然不屬于運力資產,但無車承運企業必須具有信用保障、責任擔當作背后支持,因此在資產方面還是有一定要求的。
就目前的國內發展情況看來,無車承運人還不是一個確定的完善的政策,仍然處在初步方案的實踐過程中,戴定一認為,“無車承運人實際是要解決合法性的問題,合法性關鍵是兩個字:公平。一方面要順應社會分工,允許無車承運人開展承運業務;另一方面,要保護消費、客戶的權利,不能被皮包公司所蒙騙。在這其中需要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如何化解其中的風險?采取怎樣的法律、制度和監管措施,目前是政府尚不知道的,因此要通過實踐,總結出一個政策,讓它滿足公平的原則,保護相關各方的合法利益。”這并不是提高物流效率,而是要解決實踐中這樣一件事情:雖然是創新,但是很混亂。我們要給它制定一個政策,讓它對各方面來講是公平的。
然而,對于那些沒有得到無車承運人試點資質的平臺企業來講,戴定一認為,平臺不一定只盯著交易這一條路,可以向其他方向發展。他說:“未來平臺的發展是多元化的、不僅涉及運力、貿易、金融、保險、租賃等,可以在一個領域深耕逐漸專業化,不一定以規模取勝。”一旦無車承運人的政策形成,也應該是對社會開放、公平的。
由無船承運到無車承運無車承運人化解風險還面臨哪些問題?
無車承運人的概念是由無船承運人演化而來,船是在國際之間往來的,國際間有著一套近似相同、被公認的制度監管,發展階段較為成熟。
國內無車承運人制度的起步,是否要按照同樣的模式進行尚不確定,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會根據成熟的模式總結出規律性,對無車承運過程中涉及的資金、保險、流程監管、技術等方面做出預測、預判。試點工作就是進行風控和制定監管制約機制。“無規矩不成方圓”。一套完善的無車承運人標準體系,才是規范行業秩序的有力武器。
雖然前方有很多未知,然而劈荊斬棘似乎總是成功路上的主基調。就目前的國內市場而言,無車承運真正的落地還需要面臨解決很多問題。
目前試點工作的方案具有區域分割性,每個省級的推行力度和政策不一定統一。“各諸侯國”間如何建立起共同認可的審批標準,使得無車承運人“通關”無障礙?戴定一舉了一個例子,對于一個具有全國性網絡型的企業來講,總部在浙江,企業獲得總部所屬省市(浙江)審批資質,是否能夠獲得其分公司所在地區(比如河南)的資質,開具發票,仍需在實踐中探索。
還有一直備受爭議的無車承運人的稅收標準如何制定的問題。營改增之后,交通運輸業的增值稅稅率為11%,貨代等物流輔助服務的增值稅稅率為6%。無車承運人具有著中間人的特殊身份,充當交易的橋梁,一邊是客戶,一邊是個體戶司機,究竟該按照哪種標準稅率來征收。戴定一進一步闡釋到,對于客戶企業這端,當然是稅率越高越有利;然而如果無車承運人以貨代身份交易抵扣率低,甚至到末端個體司機可能都拿不到發票,抵扣率不一致的矛盾就會很突出。
決策思維的轉變是解決問題的鑰匙
戴定一說:“我們通常會把物流定位在高效物流的目標上,物流產業本身是追求效率的,但是政府制定政策時應更多關注公平問題、利益均衡的問題,公共政策實現效率思維向公平思維的轉變是關鍵。因為市場在追求效率過程中,就會出現的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政府只有維護市場的公平,市場才會有效率的提升,而不是政府直接解決效率問題。這也是政府與市場的基本定位。
從某種程度上講,政策本身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而是在于多少人可以理解。可以形成共識愿意支持、愿意執行的,就是好政策。如果不能被多數人形成共識,只是一種理念、倡導的所謂正能量,往往是沒有實際作用的,這就是政策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