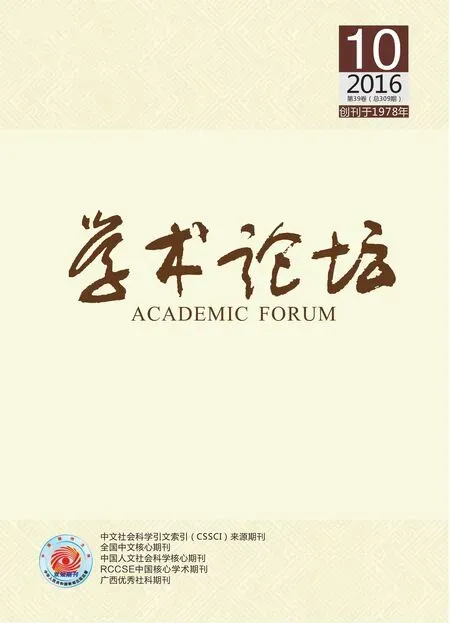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國際比較研究
柯麗菲
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國際比較研究
柯麗菲
文章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框架下,以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為樣本,采用截面數據,構建數量經濟模型,從國際化的視角對影響生產性服務業形成集聚的因素進行了實證研究,并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進行比較。研究表明,知識密集度、信息化水平、國家規模、外商直接投資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正相關;政府規模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負相關;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因素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研究結果可為我國制定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提供參考依據。為推動我國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建設,可從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重視發揮產業關聯效應、提升信息化水平、加大人力資源培養力度、擴大開放吸引外資等方面采取對策。
新經濟地理學;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國際比較
服務經濟時代的到來,生產性服務業(Produc tive Services)作為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和驅動產業升級的新動力、新方向。生產性服務業指的是在經濟生產活動中主要是為了滿足中間需求,而向其他生產性企業或機構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生產性服務的那些經濟產業。西方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已經達到了70%,其中生產性服務業又占到了全部服務業的70%,生產性服務業成為對國民經濟做出最大貢獻的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這一占比要遠低于發達國家,從中國來看,目前生產性服務業在GDP中的比重約為15%左右[1]。
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國發 〔2014〕26號)文件提出,“要堅持集聚發展……因地制宜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在中心城市、制造業集中區域、現代農業產業基地以及有條件的城鎮等區域集聚,實現規模效益和特色發展”[2]。這一提法把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這些影響因素是否存在差異?這些問題在生產性服務業的地位日趨重要的今天,顯得格外重要。
本文在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基礎之上,結合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以部分發達國家(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和發展中國家(中國、巴西、俄羅斯、馬來西亞)為樣本,從國際化的視角,經由國家層面對影響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因素展開探討和驗證,揭示形成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原因,比較各因素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影響程度的差異性,進而可為我國制定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依據。
一、文獻回顧
產業集聚指的是同一個產業在某個特定的區域內具有較高的集中度,產業和資本要素在地理空間內持續集聚的過程。生產商集聚帶來的益處包括,可促進專業化供應商的產生,從而帶來外部規模經濟效應,此外廠商集聚還可促進專業技能的提升以及知識和信息的外溢,從而有助于降低交易成
本和推動創新[3](P56)[4]。
自新古典經濟學時期以來,眾多學者已經開始關注產業集聚的研究,例如Marshall提出了外部經濟理論,他認為引起產業集聚的要素主要包括中間產品的投入、勞動力市場共享、專業化市場這三類[5](P63)。隨后,以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興起促使產業集聚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該理論的核心是將“冰山”運輸成本等空間因素納入到影響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因素中進行分析[5](P67)。至今為止,國內外學術界關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圍繞以下視角來分析。一是從要素的視角進行分析。生產性服務業中人力資源和知識資本的投入比重較大,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表明,一個地區的知識溢出程度和科學技術水平等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其中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Marshall的研究表明,成熟的勞動力市場對產業集聚有積極促進作用[5](P75)。中國學者陳建軍構建回歸模型,驗證了知識溢出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正向影響[6]。劉周洋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在進行區位選擇時,會考慮生產資料要素對其的影響,良好的基礎設施、高層次的人力資源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具有關鍵作用[7]。二是從制度政策的視角進行分析。根據某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一個區域的政府制定的制度與政策會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產生直接影響。例如:Eschenbach以20多個轉型中的國家為樣本進行研究,證明了政府放松對服務業的管制能積極推動服務業的集聚發展[8]。張波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動力機制進行了研究,他認為政府制定的區域發展戰略、制度政策、公共服務體系等制度性因素對該區域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具有重要影響[9]。任英華等學者的研究也證明了政府可以通過頒布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措施和政策來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聚集,包括產業、稅收、金融等政策[10][11]。此外,陳國亮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政府規模對生產性服務業聚集具有負向影響[12][13]。三是從信息化發展的視角進行分析。近年來信息科學與網絡技術在服務業的融合與運用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性服務業的成本,尤其是運輸成本,提升了效率和質量,推動了生產性服務業的迅猛發展,尤其是推動了金融、研發設計、商務服務、物流倉儲等對信息技術的依賴程度較高的產業發展。國內外的學者如陳建軍、任英華、Nunzia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均表明信息化水平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6][10][14]。四是從產業關聯的視角進行分析。作為制造業的中間投入產品,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已經呈現了融合發展的態勢,兩者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劉輝煌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制造業的集聚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5]。Richard驗證了生產性服務業與不同類型制造業的關聯程度存在差異,即生產性服務業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之間的關聯度最強,與資本密集型制造業之間的關聯度稍強,而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關聯度較低[16]。五是從城市規模的角度來分析。Hanson等學者根據城市經濟學理論,驗證了產業空間集聚能帶來外部規模經濟,這有助于城市的發展。產業的集聚導致了人口的集聚,從而促進了城市規模的擴張[17]。武俊奎等學者的研究認為,城市規模對產業區位選擇具有重要影響,當城市規模擴張時,企業更接近市場,獲取市場信息更為便捷,從而有助于降低銷售成本,產業聚集程度會隨之提高[18]。
綜上分析,在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一個區域的知識密集度、政府的制度環境、信息發展水平、制造業集聚、政府規模等是影響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核心要素。
二、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影響因素模型
(一)基礎模型
新經濟地理學在規模經濟條件下聚焦于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與產業集聚,它通過數據模擬等方法來探索經濟活動在地理空間中的運行機制與特征,進而可為經濟決策提供實證依據,這突破了以往傳統的分析思路和方法。新經濟地理學的代表人物Krugman于20世紀90年代構建了中心——外圍(CP)模型,該模型把運輸成本等外生因素納入一般均衡的框架,用于解釋一個區域如何從互不關聯演變成相互關聯,從不平衡發展演變為平衡發展的區域系統。在此基礎上,后來的眾多學者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拓展,其中學者陳國亮在綜合了新古典經濟學、新經濟地理學和城市經濟學等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四維理論分析框架,圍繞“要素、空間、城市、制度”這四大類要素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因素進行探索[13]。本文將借鑒這一分析框架,并結合研究的實際需要進行完善,以部分發達國家(美國、德國、法國、日本)和部分發展中國家(中國、巴西、俄羅斯、馬來西亞)為樣本,對影響產業集聚的各類因素開展研究,提出五個假說進行實證檢驗,進一步揭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成因,以此作為我國制定有利于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有
關政策的依據。
依據該分析框架,本文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函數表示為:
Y(生產性服務業集聚)=Xn(知識因素X1,空間因素X2,城市與人口因素X3,制度因素X4,資本因素X5)
其中:知識因素具體為知識密集度,空間因素具體為信息化水平,城市與人口因素具體為國家規模,制度因素具體為政府規模,資本因素具體為外商直接投資。
(二)研究假設
H1:知識密集度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正相關
H2:信息化水平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正相關
H3:國家規模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正相關
H4:政府規模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負相關
H5:外商直接投資(FDI)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存在正相關
(三)計量方法
構建計量模型的目的在于考察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在樣本國家現實經濟發展中是否具有可行性,本文主要采用線性回歸的方法檢驗各類因素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程度。首先,以H1、H2、H3、H4、H5五個研究假設為變量構建基礎模型(Xi)。然后,選擇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資(FDI)這個控制變量。D.Keeble和L.Nacham認為,經濟全球化推動了服務業集聚的發展[19]。因此本文引入了外商直接投資這一變量,考察它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效應。此外,引入了滯后因變量,可避免模型設置存在遺漏變量的偏誤。
本文采用截面數據對模型進行檢驗,為了避免異方差性給計量結果帶來影響,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估計法(GLS)對計量模型進行修正。此外,為了檢驗模型的穩定性,將樣本區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這兩類分別開展研究。
(四)數據來源和模型設定
結合研究需要,本文選取了中國、俄羅斯、巴西、馬來西亞、美國、德國、法國、日本作為樣本國家,選擇樣本國家2010-2015年的截面數據分別檢驗各個因素在影響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過程中所發揮的效應。結合各國生產性服務業數據可得性的情況,本文研究的生產性服務業包括以下行業:為生產活動提供的研發設計與其他技術服務、貨物運輸倉儲和郵政快遞服務、信息服務、金融服務、節能與環保服務、生產性租賃服務、商務服務、人力資源管理與培訓服務、批發經紀代理服務、生產性支持服務。各行業數據主要來自《國際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世界經濟年鑒》①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年鑒》2011-201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中國統計年鑒》2011-206年(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世界經濟年鑒》(2011-2016)。。
按照計量方法的特點,可構建以下計量模型:

公式(1)(2)中:α0、β0代表常數項,α1、α2、α3、β1、β2、β3、β4代表誤差項,ui表示殘差。
各變量含義:
1.servicei表示第i個國家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水平,本文采用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與全部就業人數的比值來測量該國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程度。
2.service-t表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t期滯后,即第t年的生產性服務業從業人員與全部就業人數的比重。鑒于產業集聚是個長期的動態變化過程,為了客觀描述各影響因素與產業集聚之間持續累積的因果關系,模型引入了滯后因變量,即以2010年各個國家的服務業集聚度為基準,本文選擇滯后5期。
3.FDIi表示第i個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表示全世界生產性服務業平均外商直接投資的存量,fdii表示第i個國家生產性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的流量,本文假設該符號為正值。以2010-2015年為計算期間,第i個國家2010年的FDI存量可表示為:

公式(3)中:fdii2010表示第i個國家201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流量,gi表示第i個國家2010-2015年的人均GDP增長率,α采用6%作為折舊率,2010年以后年份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可采用永續存盤法公式來計算:

4.ZSMJi表示第i個國家每萬人擁有的高校教師數量,:表示全世界國家每萬人擁有的高校教師的平均數量,將兩者的比值用來代表國
家知識密集度。
5.XXHi表示第i個國家的信息化水平,有很多指標可以用于衡量信息化水平,受到數據可得性的限制,本文選擇人均移動電話數量來衡量一國的信息化水平;JYRS表示該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將兩者的比值用于衡量信息化水平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所起的作用。
6.GJRKi表示第i個國家的規模,本文用該國的人口數量來衡量一個國家的規模;表示全世界國家人口數量的平均值,用兩者的比值來衡量國家規模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作用,本文假設兩者關系的預期符號為正值。
7.CZHCi表示第i個國家的非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受數據可得性的影響,本文用政府非公共財政支出來表示政府規模,表示全世界國家非公共財政支出水平的平均值,用兩者的比值來衡量政府規模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本文假設兩者關系的預期符號為負值。
非公共財政支出 (即政府規模)=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科學支出-教育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支出-社會保障補助支出。
三、模型檢驗結果分析
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在信息化水平、城市規模、人力資源數量和結構、市場化程度等都存在較大差距的情況下,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也存在較大差距,本文將樣本國家分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分別加以考察,其中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巴西、馬來西亞,發達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法國和日本。表1報告了模型的回歸結果。
根據上述數值,用MATLAB軟件進行運算,得到模型的系數,運用廣義最小二乘法運算對結果進行修正,最終模型的結果如表1所示。
各個解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表明各個解釋變量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都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滯后因變量的影響系數為正,說明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受到累積循環的因果關系影響較大。

表1 各個影響因素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回歸結果
第一,知識密集度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呈正相關,這表示知識密集度越大,其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推動作用越大。發達國家知識密集度的系數為 0.0001,發展中國家知識密集度的系數為0.0018,這并不是說明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比發展中國家弱勢,而是說明了在發展中國家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比在發達國家增加此類投資更有助于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這也是從另一個視角反映出發達國家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水平比發展中國家高。
第二,信息化水平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呈正相關,這表示信息化水平越高,越有效降低企業成本、提升效益,其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推動作用越大。發展中國家的信息化水平的系數為1.5884,發達國家的信息化水平的系數為2.2754,這表明在發達國家,信息化水平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推動作用大于發展中國家。
第三,國家規模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呈正相關,這表示國家規模越大,其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推動作用越大。發展中國家的國家規模的系數為2.6219,發達國家的國家規模的系數為3.648,可知國家規模增加1個單位,可以提升發展中國家2.6219單位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度,可以提升發達國家3.648個單位的集聚度。這表明在發達國家,國家規模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推動作用大于發展中國家。相比較其他幾個影響因素而言,國家規模這一因素的系數是最大的,這也解釋了生產性服務業容易在國家規模較大的國家進行集聚。
第四,政府規模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呈負相關。發達國家的政府規模的系數為-0.1725,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規模的系數為-4.0334,這表明政府規模增加1個單位可以減少發展中國家生產性服務業4.0334個單位的集聚度,可以減少發達國家生產性服務業0.1725的單位的集聚度。本文采用非公共財政支出水平來表示政府規模,回歸結果表
明:發展中國家非公共財政支出水平對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負向影響程度要大于發達國家,究其原因是由于發達國家市場化程度更高,政府為市場服務的意識更強,從而使發達國家在市場監管、產業準入門檻等方面較發展中國家寬松,發展中國家產業水平總體低于發達國家,因而受到非公共財政支出水平的影響程度也較大。
第五,FDI(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都具有正向作用,但是它對這兩類國家的影響程度不同,FDI更能促進發展中國家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益,因此FDI更傾向于投向市場化程度高、基礎設施完善、人力資本豐富、產業體系完備的發達國家,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FDI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總量和速度都有了大幅提升,進一步推動了發展中國家生產性服務業集聚。
四、研究結論和啟示
新經濟地理因素是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重要因素,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的影響因素模型分析結果驗證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即:知識密集度、信息化水平、國家規模、FDI(外商直接投資)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之間存在正相關;政府規模與生產性服務業集聚之間存在負相關。
在分析了影響因素的基礎上,可為我國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的建設提供以下啟示:
(一)發揮服務型政府的作用,完善市場環境,加強和扶持具有集聚導向的產業形成集群式發展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的改革步伐,減少政府對經濟運行的行政干涉,政府應發揮“催化劑”的作用,進一步完善市場環境,給企業提供高水平的服務,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當產業出現集聚的態勢時,政府可指導這些產業做好集聚發展的規劃,從政策、資金、服務等方面給予扶持,借助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效應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二)重視發揮產業關聯效應,大力發展制造業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
生產性服務業是為制造業提供中間產品的行業,兩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效應和融合態勢,制造業的發展將會引致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近年來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集聚往往呈現出與制造業共同集聚的態勢。由此,從產業關聯的角度出發,應大力推動先進制造業的集聚發展,進而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
(三)加快信息化進程,促進信息化水平的提升
信息化是生產性服務業向價值鏈高端化發展的加速器,信息化水平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可產生“門檻效應”,因此我國要加大生產性服務業中的信息化建設,提升信息化水平,打造優質、高效、安全的網絡環境,為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條件。
(四)推動教育事業發展,加大人力資源培養和儲備力度,提升知識外溢效應
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離不開高素質人力資本的投入,我國的教育事業應加大對生產性服務業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可以通過制定專項的人才培養規劃,為生產性服務業的各個細分行業培養專業素質好、創新能力強、服務意識佳的高層次人才,以人才為核心動力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展。
(五)加大服務業開放程度,優化引資環境,吸引FDI投向中國的生產性服務業
外商直接投資投向我國的生產性服務業,將有助于引入競爭機制,從而提升服務業的效率,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為進一步吸引外資,應持續優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和法律環境,為外資在中國的良性競爭與發展提供保障。此外,我國應把引入外資作為優化生產性服務業產業結構的一個良好契機,做好資金投向引導,引導外資更多地投向以金融、保險、商務服務、新一代信息技術、計算機等為代表的知識型服務業中,從總體上提升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價值鏈。
[1]生產性服務業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極[EB/OL].http:// www.ce.cn/xwzx/gnsz/gdxw/201603/11/t20160311_94-39950.shtm l,2016-03-11.
[2]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指導意見[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8/ 06/content_8955.htm,2014-08-06.
[3]Krugman,Paul,Geography and Trade,Cambridge[M].MA: M IT Press,1991.
[4]Kim,S.Expantion of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Econom ic Activitiesahe Trends in U.S.Regional Manufacturing Structure:1860-1987[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 ics,1995(110).
[5]馬歇爾.經濟學原理[M].朱志泰,陳良璧,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6]陳建軍,陳國亮,黃潔.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來自中國222個城市的經驗證據[J].管理世界,2009(4).[7]劉周洋.廣州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影響因素研究[D].暨南大學,2011.
[8]F Eschenbach,B Hoekman.Services Policy Reform and E-conom ic Grow th in Transition Econom ies,1990-2004[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05(4).
[9]張波.遼寧省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區發展的動力機制及對策研究[J].現代管理科學,2012(3).
[10]任英華,邱碧槐.現代服務業空間集聚特征分析——以湖南省為例[J].經濟地理,2010(3).
[11]王翔.就業吸納、產業集聚與生產者服務業發展[J].財經論叢,2011(1).
[12]劉軍躍,萬侃,鐘開.重慶生產服務業與裝備制造業藕合協調度分析 [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 (信息與管理工程版),2012(4).
[13]陳國亮.新經濟地理學視角下的生產性服務業集聚研究[D].浙江大學,2010.
[14]Nunzia Carbonara.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Geographical C lusters:opportunities and Spread[J].Technovation,2005(25).
[15]劉輝煌,雷艷.中部城市生產性服務業集聚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2(8).
[16]Richard Shearmur,Christel Alvergne.Intrametropolitan P-atterns of High-order Business Service Loc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venteen Sectors in Lle-de-France[J]. U rban Studies,2002(7).
[17]Hanson,G.H,Scale.Econom icsand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y[J].Journal of Econom ic Geography,2015(1).
[18]武俊奎,姜惠敏,王桂新.城市規模擴張對碳排放的影響機制研究——基于產業集聚的視角[J].產經評論,2012(4).
[19]D.Keeble,L.Nacham.W hy Do Business Service Firms Cluster?Small Consultancies,C lustering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London and Southern England[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2002(27).
[20]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際統計年鑒(2010年)[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劉烜顯]
柯麗菲,廣西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高級經濟師,博士,廣西 南寧 530022
F064.2
A
1004-4434(2016)10-004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