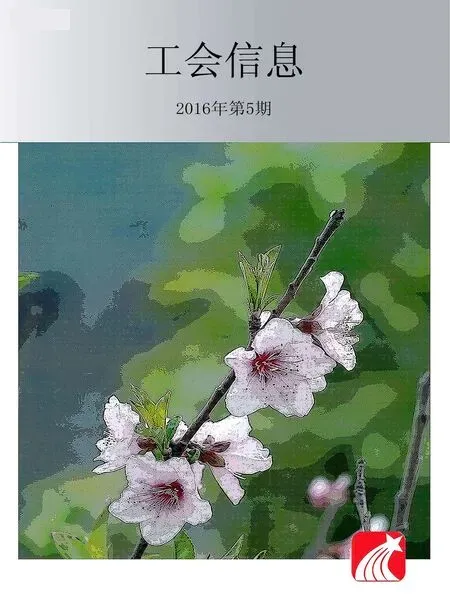儒學大師曾國藩與西學洋務
文/舒彥
儒學大師曾國藩與西學洋務
文/舒彥

曾國藩
曾國藩推行洋務時,雖說已是他的晚年,但他是清朝洋務活動的最早倡導者,也是洋務運動的主要實踐者。曾國藩一生,從理學家到洋務派,從一個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將名相,由治學、修身轉而治軍、治國,從頭到尾走完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過程。
曾國藩是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為什么能夠成為引進西方科技與近代文化的帶頭人呢?為什么能成為洋務運動的倡導者與開創者呢?原因在于:曾國藩作為理學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并非全部屬于封建主義。除了自覺維護封建主義的一面之外,還不自覺地對封建之道有所舍棄,有所改變;尤其是在文化精神上,邁出了由傳統文化走向近代的蹣跚步履。他既不是西方文化不分良莠不分一概拒絕的封建頑固派,也不是不顧中國國情對西方文化一律照搬的所謂“全盤西化”派,而是主張中西文化相結合的“中體西用”論者。曾國藩對中西文化,都是持揚棄態度,對彼此打車長短有個清醒的認識,強烈的民族意識使他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主體地位,而輔以西方文化。曾國藩在高揚“衛道”旗幟的同時,把傳統儒學中的“經世致用”精神發掘出來,形成“義理經濟”合一的新格局,給傳統文化賦予了新的生命力,恢復了其號召士林、維系人心的作用。正是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長短有透徹的了解,他就能夠吸取并發揚傳統文化的精華,能夠引進西方科技和近代文化。
可以說,曾國藩的思想開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轉變。這種變化的基本取向是:從外來文化中汲取營養、推動自身的變革;其核心思想是:師夷長技與整飭自身。曾國藩認為:西方列強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師,一身二任,只有將西方技力內化為中國自身的實力,才能抗拒侵略。用他自己的話來概括,就是:
以忠剛懾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竊制器之術,國恥足興。
從曾國藩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儒學在變,儒學也可以變。如果光從思想本身看,變化是從龔自珍特別是魏源開始的,但是真正付諸行動,或思想的變化直接影響到實際的社會生活,卻與洋務運動的領袖們的言行密不可分。而后,洋務派的實踐卻催化著儒學的變化,“中體西用”學說似成新儒學之端倪。雖未成,卻猶如宋明時期,儒學與佛學融合而成理學。
曾國藩作為晚清重臣,其歷史責任是挽清廷狂瀾于既倒,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矛盾中為當時政權尋求一條新的出路。曾國藩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站在時代潮流的浪尖上,以期引導中國走上現代化之路。在當時,要突破舊有藩籬,引導中國前進,就必須破除傳統觀念中的夷夏界限,既尊重中國舊有的文化傳統的價值,又能充分吸收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和科學創造,使古老的中國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注入生機,煥發青春。就此而論,曾國藩絕不是頑固的守舊派,因為他既看到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精神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又看到西方科學技術也是中國進一步發展所必須倚重的東西,而不應盲目地排斥,相反應當努力學習和掌握。對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曾國藩認為不應作急功近利的理解,否則,雖可使中國得紓一時之憂,有利于中國最直接、最近期的利益,但從長遠的觀點看,中國欲富強,必須學習外國的先進技術,興辦近代工業,只有中國自己的工業基礎獲得充分的發展,才能徹底擺脫外來勢力的壓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期永遠之利。
曾國藩不僅看到了西方的長處,而且敢于承認,敢于學習。因為他不僅是個學者,還是個政治家,學習是為了用以解決統治階級所面臨的政治問題。所以,他借以建功立業的學問主要并不是理學,而是經世之學。他著眼于政府統治階級之最高利益和興衰安危,而不僅僅是一個學派的興旺發達,因而他治學向無門戶之見,對一切有用的知識、學問,都主張全盤接受,融會貫通,“應時切要,擇長而用”,“習洋人之長,以強化自身”。他雖然出于儒者的本質及對清王朝的尊重,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然而卻又不得不說:“獨火器不能及也。”作為泱泱大國的中國備受“外夷”欺凌,原因何在?曾國藩認為,關鍵的原因是中國的武器裝備和軍事技術與外國有著很大的差距。他親眼目睹外國侵略者憑借“輪船之速,洋炮之遠”橫行無忌,只要在中國沿海架上幾門大炮,就可以威逼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而且在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多借洋人之器,洋人之力,亦取得成效,還嘗到了不少甜頭,從而增強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自信心。
曾國藩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外交必與自強緊密結合。他認為要想自強,就必須通洋務、辦洋務。曾國藩談論洋務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則莫過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與同僚賓友的一段談話。《手書日記》載:“與幕僚諸君暢談,眉生言及(夷)務。余以為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禮節之恭倨上著眼。即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艷(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恨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處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日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功剿發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輪舟為下手功夫。”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正確看待外國侵略問題,即懷德棄怨、化敵為友;一是如何應對外國侵略,即自我振作,師夷長技。實際上包含著內政與外交兩個方面的內容,而內政方面又包含整頓吏治與興辦軍工科技兩個要點。于此可見,所謂洋務,是由夷務一詞轉化而來,實際上不僅指外交事務而言,也不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學技術,而是包含著如何對待和處理外國侵略問題的全部政策與策略。
曾國藩早期洋務運動是以興辦近代軍事工業、訓練新式軍隊、培養洋務人才為主要內容。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為了扭轉敵強我弱、被動挨打的困境,曾國藩采用外國軍火,認為:“購買外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1860年底,曾國藩就借助洋兵鎮壓太平軍一事上奏咸豐皇帝,奏折中提到以后可以學習外國技藝、造船制炮,并可收到長久好處。1861年湘軍攻占安慶后,設立安慶內軍械所,制造洋槍洋炮與子彈火藥,次年又試制輪船,并制造出中國第一艘木殼火輪“黃鵠”號,后又試制小火輪船。1862年他又提出購買外國船炮,為救時之第一要務。購來之后,訪求能人巧匠,先演習后試造。“不過一二年,必定成為官民通行之物。”他還提出:“自強之道……其講求之術有三:曰制器、曰學技、曰操兵。”曾國藩的主張得到了恭親王奕訢及李鴻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積極響應。1863年造成“黃鵠”號輪船后,曾國藩為了擴大規模,改進技術設備,以制造更大、更先進的輪船,派容閎赴美國采購機器。1865年,與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總局;容閎回國,將所購機器并入江南制造總局,以后發展為國內最大的兵工廠。1868年曾國藩、李鴻章奏撥專款設立船廠,專門從事新輪船試制工作,將江南制造局遷址擴建,并附設新式學堂和翻譯館,培養洋務人才,使之成為當時國內規模最大、技術設備最好的綜合性軍事工廠。為了解決養輪乏資的問題,他曾提出將新造商輪租給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張,遂成官督商辦與輪船招商局之濫觴。除了積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購買制造先進武器,曾國藩還積極學習外國的練兵、設防之法,力爭做到不打無準備之戰。即使到了晚年,曾國藩還念念不忘練兵大計。他曾經提醒西太后:“兵是必要練的。哪怕一百年不開仗,也須練兵防備。”
曾國藩在實踐中認識到:“講求洋務,為當今第一艱巨之事。”而“洋務之棘手,在于人才之匱乏,人才之罕見,由于事略之不明”。于是他從1867年開始,先后聘請外國教師與中國科學家李善蘭、徐壽等人籌建翻譯館、印書處,介紹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并積極創辦洋務學堂,培養出了一大批外交和科技方面的人才。為了培養居室、尤其是海軍需要的人才,1870年曾國藩同意容閎建議,會同李鴻章奏準派遣四批留學生赴美學習,積極籌措經費,成為中國派遣留學生的首創者。
曾國藩辦洋務,目的是力圖把林則徐、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大膽設想變為現實。雖然他作為理學大師,滿口君臣倫理之道,口口聲聲強調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但是事實上他已經認識到中華文明誠然具有數千年燦爛歷史,可是在世界進步的洪流中已然落后了一大截。曾國藩從意識到落后,進而以實際行動來圖強,使中國邁出了學習西方的第一步。這種變化,對于一個效命于歷來夜郎自大、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王朝的重臣來說,的確十分難能可貴。正是曾國藩及諸多洋務派地方大員的不懈努力,中國才終于邁出了這一大膽而艱難的一步,進而開啟了向西方學習經濟、科技、軍事的新時代,才有了后來的康有為、梁啟超發起的旨在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戊戌變法”,才有了孫中山以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致力實現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偉大社會變革。
曾國藩在興辦軍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體事情并不太多,他的業績既不能與李鴻章相比,甚至不能與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貫主張抵抗外來侵略,有收復新疆之功,故其歷史形象遠比曾國藩為好。然而,無論左宗棠還是李鴻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與影響,都不能與曾國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開風氣之先。第一個上奏提出“師夷智以制船造炮”的是他,第一個早出輪船的是他,第一個派人出洋購買成套“制器之器”的是他,第一個提出“官督商辦”的是他,第一個上奏促成容閎實現派遣留學生計劃的也是他。真可謂: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洋務運動功不可沒;在洋務運動中,曾國藩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