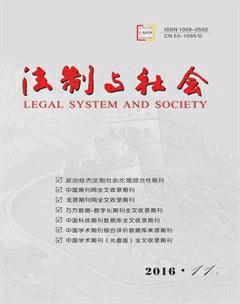獲得救助刑事被害人重訪個案引發的思考
蘇鵬 馬文昌 趙剛
摘 要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實踐中出現少數刑事被害人在獲得救助后,繼續就同一事實向其他機關甚至同一機關再次提出救助要求的重訪現象,應引起檢察機關充分重視。本文認為當前應通過建立統一的救助標準和救助程序,探索多元化救助模式,開展主動救助,聯合救助,注重釋說理等來有效化解此類重信重訪案件。
關鍵詞 刑事被害人 救助 重訪
作者簡介:蘇鵬、馬文昌、趙剛,天津市濱海新區大港人民檢察院。
中圖分類號:D920.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1.321
2009年3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關于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見》后,同年4月28日,最高檢下發了《關于檢察機關貫徹實施〈若干意見〉有關問題的通知》,就檢察機關積極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提出明確的要求,各地檢察機關都在加緊落實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檢察機關開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2年多來,在緩解特困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難,緩和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對立,防止被害人的二次被害和實施報復性犯罪,促使信訪人息訴罷訪和減少申訴上訪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實踐中也發現少數刑事被害人在獲得救助后,繼續就同一事實向其他機關甚至同一機關再次提出救助要求。此類重信重訪案件應引起檢察機關的充分重視。
一、獲得救助刑事被害人重信重訪現象的典型案例
無業人員馮某系某故意傷害致死案件的被害人李某的近親屬,本人無勞動能力,一直依靠被害人扶養。原案被告人劉某系未成年人,2010年5月因故意傷害(致死)案被判處刑罰后,因本人家庭困難,無力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馮某遂因生活無著而陷入困境。2010年9月,在馮某多次到當地檢察機關上訪后,獲得刑事被害人救助款2萬元,并與檢察機關簽訂了息訴罷訪協議。2011年8月,馮某將救助款用盡而又缺乏其他生活來源,本人生活再次陷入困境。2011年9月,馮某到當地法院上訪,稱雖已獲得檢察機關的救助,但最終判決是由法院作出的,所以,法院也應給予馮某相應的救助與補償。法院依法未給予其救助,馮某遂多次到法院和當地政法委鬧訪,此件信訪案也因此成為當地難以解決的重訪重訪案件。
二、獲得救助刑事被害人重信重訪現象的原因分析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國家對因受到特定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或一定范圍的近親屬或其他有扶養關系者(本文中的刑事被害人是廣義概念,包括刑事被害人及其近親屬或與其有扶養關系者),因案件未被偵破或犯罪人無力賠償被害人損失等原因,而由國家根據法定程序,對上述人員給予一定的救助,以維護其最基本的生存權的法律制度。作為一種救助制度,其旨在解決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生活方面的急迫困難,帶有明顯的救急性質,僅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一種補充和完善,國家不可能對被害人因犯罪人侵害造成的全部損失進行全額救助。因國家不是被害人合法權益的直接侵害者,適當救助不等同于全額補助或足額補償,所以被害人在獲得一定救助,其生活困難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后,不應再次以相同事由獲得救助,國家根據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原則也不應給予重復性的救助。但是在實踐中,少數當事人在獲得救助后還會提出進一步的要求,甚至要求重復救助,如本案中的馮某因重復申請救助未果而引發的重信重訪案。出現此類信訪案件的原因,筆者分析:
一是各地各機關在救助標準和程序等問題上不統一,使刑事被害人救助人心理失衡,多方上訪尋求公平。被害人受到傷害后,應該得到多少救助,標準是什么,在什么環節可以救濟,救濟的程序,這些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在試行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到各地標準不同,賠償有多有少,多則上萬,少則幾百,經濟條件好的地區,標準相對高一些,條件稍差的救濟的少一些。有的在訴訟過程沒有結束,就進行了救濟;有的必須在訴訟程序完結后,才可以申請救濟。甚至少數地方司法機關之間在救助標準、救助程序等問題上也存在一些差別,這就使得同樣是被害人,同樣的損害,救助的標準不一致,程序不一致,存在隨意性和差別性,缺乏常態性、規范性和公平性。這就容易使部分刑事被害人救助人在相互比較中產生心理失衡,并通過多方上訪尋求公平。如本案中的馮某受其親友挑唆,認為同類案件外地刑事被害人救助金是4萬元,本地才2萬元,就是要通過所謂 “以訪找齊”。
二是單一的救助金無力從根本上改變特困刑事被害人的生活困境。目前各地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基本上是短暫的或一次性的有限救助,同時刑事被害人救助性質決定了救助的數額也比較有限,而有些符合被救助條件的被害人則是特困人員和弱勢群體,生活非常困難,由于缺乏其他生活來源,救助金成為其主要的或唯一的保障資金,沒有勞動能力的被救助人在坐吃山空后,生活會再次陷入困境。特別是在刑事被害人是家庭的經濟支柱的情況下,因為被害人受到傷害而使這個家庭失去唯一經濟來源的話,那么對這個家庭造成的損害將是長期的,一筆救助資金對這個家庭來說,也許只是杯水車薪,根本無法從源頭上解決被害人及或其家屬經濟來源問題。就本案來說,馮某在花光救助金后,面臨沒有經濟來源的困境,想方設法再次申請救助。即使法院給予其第二次救助,在馮某穩定的生活來源問題沒有最終解決之前,其也可能再到公安機關或其他機關重復申請救助。
三是刑事被害人以重信重訪乃至纏訪鬧訪的方式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力求使補助金額最大化。少數刑事被害人并不是由檢察機關主動給予的救助,而是在信訪以后獲得救助,便認為獲得救助款是重信重訪的結果,少數刑事被害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動機驅使下,為獲得最大的救助抱持“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不健康心態,信“訪”不信“法”,在獲得救助款后以追究司法機關連帶救助責任為由繼續纏訪鬧訪,如本案中的馮某即動輒以“進京訪”為由對當地司法機關和黨政機關施加壓力。
四是少數刑事被害人對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性質不了解,片面理解國家責任。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同于犯罪人賠償制度、保險制度或其他社會救濟方式。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意義在于通過對符合條件的刑事被害人給予物質或其他形式的救助,恢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平復被害人心理,維護被害人最基本的生存條件。而在犯罪人賠償和保險制度中,被害人的損失則往往得到全額或足額的補償,但即使如此,一般也不會得到雙倍或多倍的補償。而少數刑事被害人對救助制度則賦予其遠大于犯罪人賠償或保險制度的預期,無限制地要求國家滿足其主觀性的一切條件。其中少數文化程度低的刑事被害人更是囿于文化素質、道德水準等的限制,一味依賴國家的救助,甚至在經過司法人員多方解釋后仍然不能理解救助性質,還是堅持過高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則重信重訪。如本案中的馮某在重訪過程中就多次揚言,“我現在就是因為政法機關沒有管好犯罪,導致我失去靠山。現在劉家沒有能力養我,法官也不管,我不找法院賠還能找誰?”
三、獲得救助刑事被害人重信重訪現象的治理對策
2012年3月14日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在第2條刑事訴訟法的任務中新增加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同時,該法的很多具體規定,也充分體現了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原則。筆者認為,刑事訴訟法在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權的同時,也應對被害人的權利給予必要的尊重和保障。檢察機關在檢察環節應書面告知刑事被害人應充分運用該法第99條、第100條和第101條的相關規定,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通過自己的訴訟行為來獲得刑事被告人的民事賠償;檢察機關也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的刑事和解和量刑建議程序來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賠償義務人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親自或代為履行賠償義務,最大程度彌補刑事被害人損失。對通過以上程序難以達到賠償目的的,檢察機關和其他救助義務機關等部門要通過進一步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和工作機制來保障刑事被害人獲得國家救助權:
一是必須建立完善的救助程序,形成統一的救助標準、程序。建立國家統一制定《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對救助組織、救助對象、救助條件、救助方式、救助程序、資金來源及其管理等作出明確規定。在《刑事被害人國家救助法》出臺之前,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在本省內制定統一的地方性法規,規范本省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至少實現救助標準統一、救助程序統一。
二是探索多元化救助模式。被害人司法救助不應簡單給錢了事,在發放救助金的同時可以幫助被救助人合理規劃救助金的使用,進行必要的生活技能和理財技術培訓,達到“授人以漁”的效果;而當物質救助不能很好地解決危及被害人及其親屬基本生活時,可結合具體情況,采取其他安置措施,如對那些缺乏穩定生活來源、容易坐吃山空或喪失住所的被害人或其家屬,可聯系社區、勞動和社會保障、民政、福利、養老等部門,幫助解決基本就業、臨時居住、康復治療、福利安置等問題。對無民事行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無監護人或近親屬的,由于受犯罪行為侵害導致無法正常生活、學習的,可聯系基層群眾組織等指定監護人,同時協調相關部門為其解決基本生活、失學輟學等問題。
三是抓好首訪環節,爭取主動救助。實踐中,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往往是在被救助人纏訪鬧訪之后才予以啟動,故滋長了少數刑事被害人“以鬧求助”心理。為避免類似被動情況發生,救助義務機關應轉變工作作風,變被動應付為主動救助,力爭使信訪人的申訴問題在首訪環節得到解決,實現應救早救;四是做好釋法說理,通過溝通聯動形成息訪合力。救助義務機關在救助工作中除向刑事被害人解釋清楚相關法律規定外,還應當向其解釋救助原理,做到情理法的有機結合;同時,救助義務機關在作出救助決定時可邀請其他部門到場,共同宣布,共同與被救助人簽訂息訴罷訪協議。在法律允許且時機適當的情況下,探索由各部門聯合作出救助決定的工作機制。在實施過程中要充分打消被救助人的僥幸和依賴心理,讓其感受到進行救助的主體是國家,而非特定的機關或個人;實踐中,救助義務主體也是救助決定主體,主要是公檢法機關,呈現多元化特征。而實施主體宜是一元化機關,以保持對外的統一性。筆者認為當前宜由司法行政機關充任救助決定的統一實施機構,公檢法機關可以將救助決定交由司法行政機關統一負責對刑事被害人發放救助金,處理救助申訴。一個窗口對外可以有效防止政出多門,防止給少數刑事被害人重復申請救助金以可乘之機,減少因此引導的申訴重訪現象。
參考文獻:
[1]陳彬.由救助走向補償——論刑事被害人救濟路徑的選擇.中國法學.2009(2).
[2]麻國安.被害人援助論.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3]閆繼勇.山東省部門聯合發布辦法救助刑事被害人.http : //www. chinacourt.org/html/article/200912/31/388907.shtml.
[4]劉金林.救助刑事被害人:一枝一葉總關情.檢察日報.2010-03-05(3).
[5]陳彬,等.刑事被害人救濟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