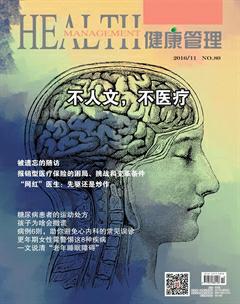病例6則,助你避免心內科的常見誤診!
在臨床實踐中,誤診是難以避免的,尤其是當醫生面對有多種合并癥的高齡患者時。這在有心臟癥狀和體征的患者中也很普遍。來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與奇卡羅內心臟病預防中心的心臟病學家Michael J. Blaha總結了他遇到的6個誤診病例。
病例1:停用他汀
52歲白人男性,有明顯高血脂、代謝綜合征,冠脈鈣化評分為180(年齡、性別、種族占到91%),服用阿托伐他汀40 mg/天。一年后,患者在運動后出現輕度肌肉痙攣與記憶困難。隨訪期間反復進行血液檢查。即便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水平下降了40%,其肝酶水平依然輕度升高(天冬氨酸轉氨酶 46 U/L,丙氨酸轉氨酶 51 U/L)。肌酸激酶水平正常。
患者要求再次評估冠脈鈣化評分,結果為210。此時患者認為他汀無效,要求停藥。醫生擔心的則是他汀的肝臟毒性與潛在中樞神經系統毒性,但不相信肌肉痙攣是他汀相關肌肉毒性的結果。因此他認為患者是他汀不耐受人群,并停用了他汀。
真正與他汀相關的肌病
該診斷過程中有若干錯誤。代謝綜合征患者肝酶輕度升高的最可能原因是非酒精性脂肪性肝。他汀毒性很少見,服用他汀的患者無需行常規肝酶檢測。肝酶輕度升高但穩定的患者可繼續使用他汀。
肌酸激酶正常無法排除他汀肌病的可能性。盡管我們并不清楚該患者是否有他汀相關肌肉癥狀,但是可以考慮暫時停用他汀或換用其他種類的他汀(例如瑞舒伐他汀)。他汀相關中樞神經系統疾病似乎非常罕見。大規模的優質meta分析并未發現他汀的短期不良認知反應,長期研究顯示服用他汀或可降低癡呆風險。
他汀不能降低冠脈鈣化評分。掃描能夠顯示斑塊的鈣化部分,而他汀只能減少斑塊的脂質部分。多項研究一致顯示,他汀會增加鈣化評分。通過減少斑塊的低衰減部分,他汀似乎增加了斑塊的鈣密度。傳統的Agatston鈣化評分可隨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冠脈鈣化評分不應該用于他汀有效性的評估。
病例2:術前心臟“清除”
67歲男性骨關節炎患者,高血壓控制良好,存在左束支阻滯及單支病變冠心病。三年前,患者發生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NSTEMI),右冠脈植入藥物涂層支架,之后接受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治療。患者經常慢跑,未出現心血管相關癥狀,無胸痛、勞力性呼吸急促或心衰癥狀。負荷檢查結果為陰性。
患者將行右全膝置換手術,需術前檢查,故行負荷超聲心動圖。按照Bruce方案運動8分鐘,達到10 METS峰值運動量,仍無胸痛。然而,其心電圖提示外側壁導聯有2 mm ST段壓低,負荷超聲心動圖提示可能存在負荷誘導的前間壁運動異常。最終患者轉診至導管室。
負荷測試的作用
該病例中有若干診斷錯誤,原因可能是對負荷測試在穩定性冠心病中的作用理解不足。無癥狀冠心病患者每年行負荷測試并無效果。COURAGE研究表明,穩定性冠心病患者負荷測試后行血運重建的效果并不優于最佳藥物治療。
該無癥狀患者經常運動,故可能無需術前負荷測試。負荷測試對于明確是否需要繼續使用氯吡格雷并無特殊作用——該患者可能無法從延長雙抗治療(12~18個月以上)中獲益。
該病例的負荷測試結果可能被過度解讀。患者沒有癥狀,運動能力良好。其心電圖改變的原因可能是左束支阻滯。負荷超聲心動圖中前間壁異常的原因可能是左室不同步相關的左束支阻滯。轉診導管室可能導致不必要的血運重建及后續雙抗治療,致使全膝置換手術被推遲。
病例3:不恰當抗凝
58歲女性肥胖患者,有長期高血壓、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及輕度HFpEF。近期行膽囊手術后就診,因術后恢復期出現快速房顫(AF),但12小時內消失。在出院后康復期間,患者曾兩次發生自限性房顫。每次發作時均可感受到心悸,患者在過去兩年中多次出現這種心悸。治療中心員工建議她向醫生咨詢是否應該使用血液稀釋劑。心電圖提示患者需要抗凝治療,還提示左室肥厚,但竇性節律正常。最終患者未接受華法林治療。
心電圖正常就無需抗凝?
患者有陣發性房顫,可能早已存在。盡管圍術期治療發現了房顫,但它可能無法完全歸因于外科手術,因為康復期間也有多次發作。患者心源性卒中風險很高,有多個房顫相關卒中風險因素。患者肥胖,有長期高血壓、左室肥厚、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及HFpEF。CHA2DS2-VASc評分為3,提示每年的卒中、短暫性腦缺血發作或其他系統性栓塞風險為4.6%。
根據當前心律決定是否啟動抗凝的情況很常見,但處理并不恰當。即使該患者的24小時霍爾特監測結果為陰性,但不使用抗凝藥是不恰當的。華法林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患者擔心INR監測問題,可考慮新型口服抗凝藥物。
病例4:流感惹的禍
60歲男性,有多種心血管風險因素,近期急診負荷測試結果陰性,有低燒及流感癥狀。在過去的2年中,患者曾發生上腹部燒灼疼痛、咳嗽及呼吸急促。胸部X射線檢查提示雙側浸潤,故啟動阿奇霉素治療。
第二天患者因呼吸急促惡化再次就診。再行胸部X射線與心電圖檢查,胸部射線檢查發現穩定性浸潤,無病灶整合(focal consolidation);心電圖提示小Q波、II、III及AVF導聯中ST段輕度抬高。自動計算機心電圖解讀未突出這些改變。但因癥狀惡化,患者接受了7天的莫西沙星治療。
病毒性疾病與心肌梗死
該患者的病毒性疾病觸發了下壁心肌梗死(MI),還有進展性心衰。很多心梗患者并無胸痛表現,例如右側冠狀動脈梗死可能表現為上腹疼痛(可能被誤診為胃腸道疾病)。
初始檢查中有胸部X射線檢查,但無心電圖與肌鈣蛋白,因為患者近期的負荷測試為陰性。負荷測試發現了混合性阻塞性冠心病,但它們不能預測無血流限制性病變何時破裂。基礎醫療與醫院門診中有時會遇到這種情況,這些地方的呼吸道感染很常見,但心梗卻少見。心衰患者常被處以抗生素治療。
第二次就診時,心電圖提示Q波及輕微ST段抬高,符合下壁心梗標準。前一天的心電圖可能已經出現了缺血性改變。如果能夠意識到病毒性感染可能引發心梗且下壁缺血可能偽裝成燒心或惡心,再加以密切的心電圖檢查,就可預防這類情況。
病例5:心動過速與肌鈣蛋白評估
72歲男性,接受降壓與降脂治療,因胰腺腫塊行惠普爾手術。該手術較為復雜,且該患者發展為室上性心動過速及持續性低血壓(需靜滴去甲腎上腺素以維持血壓)。在外科重癥監護病房中,心電圖提示竇性心動過速,心率100 bpm,無相關ST段或T波改變。肌鈣蛋白T水平為0.68 mg/dL。
患者被予以阿司匹林治療并靜滴肝素。醫生就患者是否需要啟動β受體阻滯劑、氯吡格雷或導管室進行了會診。與此同時,患者發生了明顯的腹部出血,被送至手術室行腹部沖洗。
Ⅰ型與Ⅱ型心梗
Ⅰ型心梗與Ⅱ型心梗很容易被混淆。Ⅰ型心梗是由冠脈斑塊破裂及后續的血栓形成通路(急性冠脈綜合征病理機制)激活引起。相反,Ⅱ型心梗是由心肌血氧供需失衡所致,并無斑塊破裂——例如明顯的血流動力學應激。Ⅰ型心梗需進行抗血小板與抗凝治療,Ⅱ型心梗則常需保守治療,例如逆轉固有的血流動力學應激。
患者曾進行復雜的手術,后發生心律失常及低血壓(需加壓素)。血流動力學應激及去甲腎上腺素所致的潛在血管痙攣可能會造成輕度的心肌損傷。該病例不可能是Ⅰ型心梗,因其心電圖結果正常。如果及早的精確診斷Ⅱ型NSTEMI,則可以預防外科手術出血。
病例6:起始于暈厥
78歲男性,有高血壓、高血脂及右束支阻滯病史。5年前的超聲心動圖檢查提示輕度的左室肥厚、輕度左心房擴張及中度的主動脈狹窄。
近期的門診就診提示患者血壓難以控制。他將其輕度疲勞歸因于衰老。在最近的歐洲旅行中,患者發生了暈厥,但未尋求醫學治療。最后一次就診時患者血壓為180/82 mmHg,心率55 bpm。患者有嚴重的收縮期噴射性雜音;然而,該雜音短于以往就診時雜音,其S2心音更弱。心電圖提示竇性心動過緩,伴一度心臟阻滯、右束支傳導阻滯及左前分支傳導阻滯。患者啟用了另一種降壓藥。一周之后,患者再次出現暈厥,送至急診時有輕度呼吸困難。
不祥的征兆
患者有嚴重的癥狀性主動脈狹窄,在疾病早期可能并無癥狀。隨著疾病的進展,患者常會出現癥狀,且血壓開始升高。
主動脈狹窄患者出現暈厥是種不祥的征兆,但暈厥事件可能被錯誤的歸咎于其他問題,例如脫水或尿路感染。主動脈狹窄患者的暈厥可能是由嚴重或危急的病變瓣膜引起,也可能是由高度心臟阻滯的發展所致(該患者有三度傳導阻滯)。體檢結果也與嚴重主動脈狹窄特征一致。
定期的超聲心動圖檢查有助于識別正在進展的瓣膜疾病,中度或嚴重主動脈狹窄患者發生暈厥后需再次評估瓣膜疾病的嚴重程度,并定期進行超聲心動圖檢查(1~2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