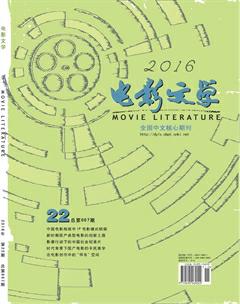保羅·托馬斯·安德森電影的人文性分析
[摘要]美國新銳導演兼編劇、制片人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盡管拍攝的故事長片并不多,但是卻以一個獨立電影人的身份獲得了好萊塢新一代大師的美譽。安德森的電影也從來沒有被納入主流商業(yè)電影的行列之中,安德森更加類似于一名人文主義者,社會問題、人類的道德與本性等均是安德森電影關注的主題。文章從電影對文學著作的深層開掘,《圣經》元素與對人性惡的探討,電影對西方社會精神病癥的關切三方面,分析安德森電影的人文氣質。
[關鍵詞]保羅·托馬斯·安德森;電影;人文氣質
美國近年來異軍突起的青年新銳導演兼編劇、制片人保羅·托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1970—)盡管拍攝的故事長片并不多,但是卻以一個獨立電影人的身份獲得了好萊塢新一代大師的美譽。[1]早在高中階段,安德森就在短片《大炮王迪哥傳》(The Dirk Diggler Story,1988)中展現(xiàn)了自己的電影才華,而在進入紐約大學的電影系后,安德森則很快輟學,隨后以自學成才的方式接近影壇。盡管安德森并沒有接受過嚴格的常規(guī)學院教育,但這并不影響其憑借著電影之中深厚的才華成為好萊塢新生代導演群體中的中堅力量。安德森的電影也從來沒有被納入主流商業(yè)電影的行列之中,安德森更加類似于一名人文主義者,社會問題、人類的道德與本性等均是安德森電影關注的主題。在非商業(yè)電影苦苦求索的今天,安德森所灌注在電影之中的人文氣質對于其他電影人可以說是極有借鑒意義的。
一、對文學著作的深層開掘
對文學著作進行改編是保障電影之中人文氣質的重要方式。一部分出自大家之手的文學著作之所以能夠廣為流傳,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原作者賦予作品的,能夠震撼讀者心靈的哲理情思。而電影導演對文學著作的改編過程也就是與原作者進行心靈對話的過程,一旦導演能夠對作品進行有深度的開掘,那么電影和文學將勢必在人文情懷上取得令人稱道的化學反應。
這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改編自著名“隱士”作家托馬斯·品欽的同名小說的《性本惡》(Inherent vice,2014),值得一提的是,這也是品欽第一部被改編為電影的作品,安德森幾乎無法找到合適的參照對象。但是安德森對于原著精髓的精準把握依然使得該片獲得了第87屆奧斯卡的最佳改編劇本提名。小說誕生于2009年,此時已到晚年的品欽相比起早年《萬有引力之虹》的時代已經更傾向于做一次私人化的寫作。小說套用了一個類似于錢德勒通俗偵探小說的表層結構,甚至在人物和情節(jié)的設定上也與錢德勒小說有著頗多雷同之處。但是品欽卻無意使用破案這一懸念故事來吸引讀者,給讀者提供淺薄的閱讀快感,以至于整個故事的情節(jié)十分松散,故事最終也沒有真相大白。一言以蔽之,品欽原著與典型偵探小說之間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關系,品欽的本意是借用偵探小說的故事來給觀眾展開一幅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加州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眾生相,只是由于小說的亦莊亦諧(如充斥著大量的黃色笑話、惡俗的雙關語、下流的俚語等),因此讀者很少能夠進入到品欽原著的深層。
而安德森很好地領悟到了這一點,首先,安德森利用了電影影像化敘事的優(yōu)勢,將品欽用文字所未能完全傳達出來的社會風貌貼切地展現(xiàn)在觀眾的面前。例如,在洛杉磯這個光怪陸離的“后現(xiàn)代城市”外表之下游蕩的是對于毒品、濫交和“革命”有著如饑似渴向往的嬉皮士青年,在房地產業(yè)的惡性發(fā)展之中逐漸老無所依的邊緣人物(墨西哥裔、黑人等),包括國家機器運作之中的種種黑幕等。電影之中的罪惡源頭實際上并不是簡單的地產開發(fā)商、戒毒中心和販毒團伙,甚至也不能簡單地歸結于政府,而更應該探尋至人們本性之中的貪婪和自私,只是這樣的物欲在六七十年代的洛杉磯被釋放得尤為明顯。[2]而主人公多克則是一個吸毒成癮,帶有嬉皮士做派,經常隨意地穿著拖鞋的私人偵探,但是他身上又并非沒有某種理想主義的閃光,不然他也不會應前女友的委托調查案件,這些都讓即使并非成長于電影中特定時代和地點的觀眾也能對故事背景有著比較全面的認知。
其次,在對電影進行改編時,安德森為了將小說之中某些帶有幻想意味的描寫落到實處(如人在吸毒之后產生的諸多幻覺),還參考了大量其他黑色電影,如羅伯特·奧特曼的《漫長的告別》,霍華德·霍克斯的《夜長夢多》和羅伯特·奧爾德里奇的《死吻》等,使畫面富有沖擊力。對于改編《性本惡》,安德森毫不掩飾自己對于品欽作品的熱愛,聲稱比閱讀品欽作品更為愉悅的事情就是再讀一遍,并且每次讀品欽的書都能有新的體會。在這種興趣的驅動之下,安德森才得以最終將近四百頁的小說轉化為一百余頁的劇本,可以說,安德森電影之中的人文深度是無法脫離他對文學著作的熱愛的。
二、《圣經》元素與對人性惡的探討
《圣經》對于西方文化有著至關重要的根基地位,大量經典的文學作品都從《圣經》的哺育中誕生,如威廉·福克納的《押沙龍,押沙龍!》等更是相當于對《圣經》故事在新時代背景之下的原型借用改寫。失去了對《圣經》的了解,那么在探尋西方文化時則必然存在隔靴搔癢的遺憾。而在娛樂性和商業(yè)性更強的電影作品之中,導演們卻較少借用《圣經》典故,一來電影敘事上的深度并非大多數(shù)導演所關注的目標,越來越多的電影正在技術進步的浪潮之中追求著對觀眾視覺上的吸引而非思想上的叩問;二來當前西方社會的基督教信仰仍然處于逐步被瓦解的低潮時期,發(fā)生于20世紀的多次人類災難使人們很難再從傳統(tǒng)宗教的信仰廢墟之中找到繼續(xù)篤信上帝的力量。然而《圣經》本身的經典并不在于單純對基督教信仰系統(tǒng)中各種概念或道德規(guī)范的闡釋,其中所包孕的種種小故事依然閃耀著人文主義的光輝。而安德森就屬于能夠大膽而巧妙地在自己的電影中啟用《圣經》故事中的母題的導演之一,這樣的嘗試也使得他的電影充滿耐人尋味的人文氣質。
以讓安德森獲得了柏林銀熊獎的《血色將至》(There Will Be Blood,又譯作“血色黑金”,2007)為例,電影實際上就帶有非常明顯的《圣經》的影子。電影題名之中的“血”便有多重含義,在《圣經·出埃及記》之中,原文就提到“埃及到處都是血色將至的景象”,血既可以視作圣子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之后流出的,能夠赦免罪人之罪的鮮血,也可以指被殺之人從地里向上帝哀告,詛咒這片土地的血。在電影中,主人公丹尼爾·普萊恩維尤是一個銀礦工,因為意外獲得了石油信息而飛黃騰達成為石油大亨。在油田他結識了假冒他兄弟的混混亨利,即使二人并非血脈上的真兄弟,但亨利與丹尼爾之間并非沒有情誼,然而丹尼爾卻在知道真相后殺死了亨利。而這僅僅是唯利是圖的丹尼爾所犯下罪孽的其中之一,油田在噴涌出“黑金”的同時也如同受了詛咒,讓丹尼爾在乎的人一個個離他而去。《圣經·創(chuàng)世紀》之中該隱在田間殺死亞伯之后,面對耶和華的質問,他隱瞞罪行,佯裝不知,而耶和華則表示亞伯的血流到了地里,這片土地就受了詛咒,該隱終將被這血反噬。這個手足相殘的故事便是丹尼爾殺人的原型。除此之外,亞伯因為在兩個兒子之間心存偏見,最后引狼入室,把家傳土地賣給了石油大亨,丹尼爾的兒子成年后反過來對付自己的父親等,也都在《圣經》之中能夠找到對應的典故。
從《血色將至》開始,人們開始明晰了安德森電影的特色,即在保證電影形式上的美學標準時還在內容上具備著豐富的人文氣質。[3]由此,這位一開始處于邊緣地位的青年導演很快便能夠躋身好萊塢主流場域之中,成為當代為數(shù)不多的能同時在商業(yè)和藝術領域都獲得成功的“70后”導演之一。
三、對西方社會精神病癥的關切
安德森本人的父親是一名成人電臺節(jié)目的主持人,并且有著收藏黃色影碟的癖好。這一點深刻地影響了安德森日后的電影創(chuàng)作,他雖然自幼便觀摩大量黃色電影,深知成人對于此類感官刺激的迷戀,但在其成年后,他的電影卻帶有一種“反色情”的禁欲傾向,前面所提及的帶有宗教意味的電影便是其中一例,并且安德森還有意識地將父親的經歷以及色情電影之中的敘事、母題等等運用在非色情電影之中。如其最先對電影進行嘗試的《大炮王迪哥傳》中就以“偽紀錄片”的形式跟蹤拍攝了一個色情電影劇組的工作日常。盡管劇情是虛構的,但是安德森卻把他們的言談舉止拍攝得惟妙惟肖,這可以視作是其將電影本身與色情題材的首次結合。又如在《木蘭花》(Magnolia,1999)中,主人公吉米就是一個電視節(jié)目的主持人,他和兒子弗蘭克·麥基之間的父子情也是電影之中的重要線索,而打扮頹廢的麥基本人就是一個黃色節(jié)目的主持人,他給觀眾留下的最深刻印象便是對色情話題的侃侃而談。從熱衷于“窺淫”的父親身上,安德森所接受到的并不僅僅是對色情的思索,還有著一種對整個社會出現(xiàn)精神病癥的意識。在安德森所成長的整個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都面臨著信仰缺失、欲望泛濫的弊病,水門事件等的出現(xiàn)更是讓人們面臨著嚴重的精神危機,對于社會產生了質疑感和虛無感。在這樣的氛圍之下進入到電影領域的安德森開始運用電影這一載體來表達對種種社會現(xiàn)象的關心,而電影本身的故事性則被安德森置于次要位置。[4]
安德森的處女作《賭城風云》(Hard Eight,1996),對安德森的電影生涯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安德森一方面由于票房僅有二十余萬美元而被制片廠開除,另一方面又獲得戛納電影節(jié)的另眼相待,而處于悲喜交加之中,世界開始見識了安德森的電影氣質,如在形式上明星陣容、長鏡頭的運用等;而在內涵上,安德森則表現(xiàn)出了令人無法忽視的對社會病癥的犀利揭露。悉尼槍殺約翰的父親,間接導致了約翰的潦倒,而悉尼選擇對約翰的救贖方式是帶他到賭城中以賭博來虛度光陰;而在悉尼的罪行面臨著即將被吉米揭發(fā)的危險時,原本打算洗心革面的悉尼卻再次舉起了槍。直到電影的結尾,悉尼始終沒有能夠償還自己犯下的罪孽。安德森揭示出人類盡管有向善的意愿,但是很容易為內心的自私所困擾。
又如在安德森自編自導的《不羈夜》(Boogie Nights,1997)中, 故事也同樣發(fā)生在20世紀70年代,此時色情片正在美國大行其道。色情片導演杰克就依靠著這一工作獲得了帶泳池的豪宅;原本認為能夠賺錢養(yǎng)活自己就已經足夠了不起的德克,因為成了色情片明星而春風得意;而從事色情片制作這一行業(yè)的人們在物質上獲取極大滿足的同時也往往有著難以為外人道的私生活。以攝影指導為例,他本人每天都要面對各種情色畫面,看似已經麻木不仁,而他的妻子又是一名色情片的女明星,她每天都要在片里片外與丈夫之外的男人進行著瘋狂的、真假莫辨的性愛,這樣的生活終于有一天壓垮了攝影指導,致使他失去了理智開槍殺妻。“Boogie”本身就有搖擺的含義,劇中的人均在肉欲、金錢、良知、人性等中搖擺掙扎。可以說,安德森并非有意為當前西方社會所出現(xiàn)的群體性的精神病癥開出一劑良方,但是他卻關注著,并且善意地提示著處于現(xiàn)代語境之下的人們所面臨的精神困境或危機。其電影中的內核始終是以人為本的。
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的電影或是取材于著名文學大家的作品,或是對《圣經》之中的原型故事進行改寫,保證了電影的人文品位和思想境界。在電影中,安德森直面人類在不同情況下所面臨的悲劇或困境,體現(xiàn)著一種具有擔當感的精神,并期待著當代人可以獲得心靈的復蘇。一言以蔽之,安德森的電影盡管還稱不上臻于化境,但完全可以被認為是目前非商業(yè)電影中的典范。
[參考文獻]
[1] 張愛華.感悟美國“X世代”電影美國新銳電影人研究[J].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7(03).
[2] 安東尼·雷恩,陳薇薇.《性本惡》:光怪陸離的70年代[J].電影世界,2015(01).
[3] 張勇.保羅·托馬斯·安德森:反諷敘事、反差修辭與見證影像[J].當代電影,2013(11).
[4] 焦雅萍.保羅·托馬斯·安德森電影中人物的邊緣性[J].電影文學,2014(06).
[作者簡介] 景艷(1981—),女,河南三門峽人,碩士,鄭州旅游職業(yè)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涉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