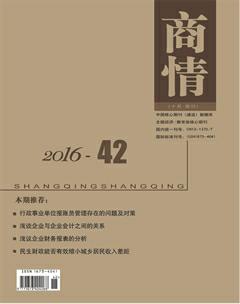維特悲劇命運的再思考
趙前明 劉文斐
【摘要】維特的性格是特殊的,帶有狂飆突進時期的敏感、脆弱、幻想、激情和感傷;“維特式的人生”,不只屬于維特一人,而是當時社會和文學中一代青年的共相,是18世紀德國和歐洲青年普遍的一種人生狀態。
【關鍵詞】維特 性格 人生悲劇 意義
《少年維特之煩惱》圍繞著維特與綠蒂的愛情這條情節主線,展示了社會生活的廣闊畫面,體現了狂飆突進時期德國青年維特敏感、脆弱、幻想、激情、傷感的人格及其悲劇的一生。
一、維特的性格
歌德筆下的少年維特有著典型的“狂飆突進運動”的時代色彩,又有著敏感脆弱自尊多情的個性特征。“性格就是命運”,維特的悲劇命運和他的性格緊緊聯系在一起。
1.維特的性格是當時的“狂飆人格”的具體表現。
維特的性格是激進熱烈的,表現在反抗一切束縛以伸張自我的精神。維特的時代,“自然”是一個熱門話題。早在十八世紀中葉,盧梭目睹私有制產生以來,人類創造的財富和精神文明壓抑了人的發展,人的貪婪和欲望使人逐漸背離了自然、樸素和美好的本性。他認為人類最美好的狀態是自然狀態,因此,他強調人必須“順乎自然”,呼吁“返回自然”。維特是青年歌德的影子,歌德是狂飆突進運動的一名主將,狂飆突進運動使歌德經歷了一次資產階級文化運動,接受了先進的思想,有著出眾的才能,高尚的情操,奔放的激情,遠大的抱負,新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代表著一代覺醒中的德國知識青年。
2.維特是一個從根基上動搖了的心靈。
他是一個浪漫主義的心理傾訴者,是個幻想感傷又脆弱易斷的悲劇形象。維特對自然的無限崇仰,淋漓盡致,不僅表現著青年歌德本人的世界觀、宗教觀、社會觀、道德觀、審美觀等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曲折的反映了新型資產階級變革者對現實的要求。因為,拿“自然”的尺度來衡量,當時的社會制度、宗教信仰、法律道德、教育文化乃至生活習俗等等,沒有哪一樣是要得的,沒有哪一樣可以繼續存在下去。他的追求是一種幻想,但本質上卻帶有一種感傷。他帶著強烈的感傷主義情調,他一味強調心靈感受,愛天然、愛自由、愛真性情、愛美麗的幻想。維特雖然是一個熱情純潔、絕頂聰明的少年,性格類似少年歌德,但是我們可以看出他更多的則是多感、更溫柔、更軟弱些,他的情感過于纖細,性格過于脆弱,他的對世界的好與壞或者光明與慘暗,都是他自己心靈的反射,注定他人格根性上的悲觀,這樣一顆易碎的心是不能長存于這個堅硬冷酷的世界的。
維特的性格不是他一個人的性格,而是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激進、感傷情懷。
二、維特命運悲劇的原因
維特對自由平等地位的追求、感傷脆弱的個性及愛情憧憬與社會等級制度間的矛盾,造成了他悲劇的一生,最終維特不得不采用自己的方式去尋求屬于自己的現實。
1.維特的悲劇是其愛情與道義沖突下的結局。綠蒂不僅僅是維特的戀人,她幾乎是維特全部理想的化身,美的代表。綠蒂不僅僅是他的愛人,也已經成為他心靈的攀附對象和避難所。他對她的愛是熾熱的、忘我的,然而卻多少有些偏離了愛的真義,這是一種非理性的、變態的愛,最后的結果不是毀滅他人,就是毀滅自己。與其說他愛的是綠蒂,不如說他愛的是他自己,千方百計地要從對異性的征服中證明自我存在的價值。正因為如此,在理性的藩籬面前,維特的內心才會產生如此復雜的糾葛和深沉的苦痛。當意識到自己難以被綠蒂接納時,維特選擇了現實;當現實把他拒絕了的時候,他又回到了綠蒂身邊,而終究得不到愛人的事實又使維特變得愈加瘋狂。當綠蒂宣布了他的夢想之幻滅,維特全部的人生希望、青春的熱情、生活的勇氣都被一道摧毀,從而只得以極端的方式——自殺來表露對現實的反抗。
2.維特的悲劇是其個性和社會存在的巨大差距造成的。18世紀的德國,青年的精神和生活正受到嚴重壓抑和摧殘,思想苦悶,渴望擺脫封建束縛,但又缺乏斗爭的力量,看不到出路,普遍存在消極、頹廢的情緒。維特盡管開始覺醒,但他的精神上仍免不了留有時代和階級的烙印——新興資產階級在反對封建主義斗爭中的局限性和軟弱性。他既對現實感到憤懣和憎惡,不愿在黑暗的環境中忍辱偷生。煩躁、焦慮轉為苦痛和憂慮,對社會完全絕望,最后決定用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向罪惡的封建制度發出最強烈的譴責和抗議,他發覺自己毫無出路,對前途再也沒有抱任何希望,就這樣,封建社會的不合理制度、舊秩序、陋習、偏見和壓力奪取了一個有為青年的生命。德國資產階級無力根據本階級的利益改變現實,歌德甚至宣稱“滿懷憤慨,不顧一切,以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脫離塵世,到為得計。這種病態的情感,使他們面對鄙俗的社會現實更加軟弱無力。”在經歷一系列挫折以后,維特覺得自己的夢非常縹緲,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實現,因而選擇以死抗爭。
3.維特的悲劇是其人格與世界發生沖突的結果。維特是追求自由平等的,是自尊的。他熱情奔放,獨立不羈,不愿受任何清規戒律的束縛,所以不是循規蹈矩,理智冷靜,善于克制自己感情和欲望的市民類型。維特曾用著事業上的發展來擺脫愛情的失望造成的心靈的創傷,因而他到公使館供職,以一展自己的聰明才智。但是當時德國社會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處處因循守舊、虛文俗禮,公使對標新立異的維特很是反感,周圍的那些人一心追逐等級地位。受盡屈辱的維特非常憤怒,難怪他要發出哀嘆:“最令我惱火的是市民的可悲處境”。封建階級為了企圖永遠保持它們的既得利益,鼓吹尊卑有別,把封建等級制度看作是天經地義,不容改變,在那樣的社會里,容不下資產階級實現其“個性解放”、“感情自由”和“全面的發展人性的自然本性”的理想。維特是個富于自我意識的市民青年,不甘心對人俯首帖耳,自認低人一等,結果處處碰壁。歌德曾談到維特說“看看‘維特時代我們會發現它與一般世界文化進程無關,而與每個人的個人生涯有關,個人生來就有自由本能,卻必須使自己適應沉浮世界的狹隘限制”。
維特的死既有社會的責任,又有階級的局限。楊武能說“貴族階級的歧視和壓迫,曾使維特憤懣不平,一度想‘抓起到來刺破自己的胸膛,以抒積郁的話;那么,對市民社會的厭惡和失望,更令他痛心疾首,真的‘提早結束了生命的旅程”,誠如盧納恰爾斯基在為紀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作的報告中指出“歌德的生命快結束的時候,他已開始看出資產階級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內在矛盾”《維特》更加揭示了個性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維特以及同時代的所有青年的進步青年的煩惱和苦悶,都產生于這種矛盾中。正如恩格斯所說:“維特建立了最偉大的批判的功績”,維特的形象蘊含了十八世紀下半葉德國社會的現實和時代啟蒙兒的矛盾,絕非是一個人的特性,而是體現了一代人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