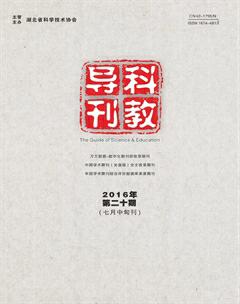關于“基本信念”的思考
趙國鋒
摘要 在知識論中,基礎主義者認為,我們的信念總體中存在著一種地位特殊的信念,即“基本信念”。而美國哲學家約翰·波洛克則認為,我們根本就不需要擁有這種基本信念。然而,在對波洛克的論證過程進行細致分析之后,我們就可以發現:其實,波洛克并不是在否定基本信念,而只是在對基本信念進行一種新的解釋而已。他只是在用自己的“基本信念”來取代“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而且,由于面臨著“所與神話”的困境,這種‘取代”也是不成功的。
關鍵詞 基本信念 認識后退問題 所與
中圖分類號:N0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j.cnki.kjdkz.2016.07.059
按照基礎主義的認識辯護理論,我們的信念存在著基本信念和非基本信念之分,其中,基本信念不需要辯護,而非基本信念是由基本信念來辯護的。這是基礎主義辯護理論的基本觀點。由于此理論的核心就在于“基本信念”這個概念,所以,幾乎所有針對基礎主義的批判也都指向了這個概念。其中,美國哲學家約翰·波洛克就認為,所謂的“基本信念”對于我們來說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們根本就不需要這樣一種特殊的信念。
1不必要的“基本信念”
對于究竟何為基本信念,基礎主義者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但是,他們都認為,基本信念是一種“不需要辯護”的信念。那么,又該如何理解“不需要辯護”的信念呢?波洛克指出,“不需要辯護”的信念就是“自我辯護”的信念。那么,什么是“自我辯護”呢?對于這個概念,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認為,“自我辯護”的信念就是“無需矯正地得到辯護的”信念。而對于一個人s來說,一個信念p是無需矯正地得到辯護的信念,當且僅當,只要s持有這個信念p,那么,信念p就是得到辯護的,即使s沒有任何獨立的理由。另一種解釋認為,“自我辯護”的信念就是得到“初始辯護的”信念。而對于一個人s來說,一個信念p是得到初始辯護的信念,當且僅當,只要s持有信念p,并且沒有任何獨立的否定性理由,那么,信念p就是得到辯護的。
波洛克認為,無論在上述哪一種意義上理解“基本信念”,“基本信念”對于我們來說都是不必要的。我們根本不需要基本信念。這是為什么呢?為了解釋這一點,我們需要先來看一下,基礎主義者為什么認為“基本信念”是必要的?而這個問題是與“認識后退問題”密切相關的。“認識后退問題”一般被表述為一個相應的論證,即“認識后退的論證”。這個論證可以簡述如下:
在為某一個信念P1提供辯護的時候,我們一般都認為,能夠為信念P1提供辯護的一定也是一個信念。假設,為信念P1提供辯護的是信念P2,那么,我們就可以說,是信念P2辯護了信念P1,但是,信念P2要想真正實現對信念P1的辯護,它自身也必須是個得到辯護的信念。而為信念P2辯護的也一定是某個信念P3,而信念P3要想真正實現對信念P2的辯護,它自身又需要另外某個信念P4來辯護。同理,信念P4又需要信念P5的辯護……以此類推,對于信念P1的辯護就會形成一個鏈條。而如果一個人S想獲得一個得到辯護的信念P1,那么就必然要存在一個信念Pn,此信念是不需要其它信念的辯護的,而是“自我辯護”的。這就是基本信念。所以,基礎主義者認為,“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是必需的,否則,我們的任何信念都將得不到辯護。
但是,波洛克認為,在上述這種論證中蘊含著一種叫做“信念假設”的理論,即“一個認知者的信念的可辨護性僅僅是由她所持有的信念來決定的。除了信念,沒有什么可以決定辯護。”按照這種理論,我們所有的信念的理由也都必定是一個信念。只能是信念才能成為信念的理由,才能為信念辯護。而波洛克認為,“信念假設”完全是錯誤的。他指出,能夠為一個信念提供辯護的事實上的確不必非要是一個信念。這是由認識辯護的本質決定的。在他看來,認識辯護是一種“程序辯護”,而程序辯護表現為一種程序規范。程序規范是一種描述程序知識的規范。正是依賴于程序知識,程序規范在指導我們的行為時才不需要我們形成相應的命題和信念。這就意味著,認識辯護和認識規范所考量的因素都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些指導我們的行為卻不要求我們對其形成相應信念”的因素。換句話說,所有而且只有這樣的因素才能有助于我們在認知中遵循認識規范,從而為我們的信念提供認識辯護。而這種因素對于我們來說就是“可直接訪問”的因素。我們在認知中“可直接訪問”的因素就是我們在認知中的所有內在狀態,這些內在狀態不僅包括信念狀態,還包括知覺狀態和記憶狀態等。只要是一種內在狀態就能成為認知規范的考量因素,就可以為信念提供認識辯護。所以,任何一種內在狀態都可以成為信念的理由,從而為信念辯護。也正是基于此論斷,波洛克提出了自己的認識辯護理論,即“直接實在論”。按照這種理論,即使一種信念(物理信念)不需要其它信念的辯護,也并不是“自我辯護”的,而是可以由其他某種非信念的內在狀態來辯護的,比如,知覺狀態或記憶狀態等。所以,在波洛克看來,基本信念完全是不必要的。
2基本信念真的是不必要的嗎?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基礎主義者之所以需要這種“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為了解決“認識后退的問題”。如果我們在沒有這種“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解決“認識后退的問題”,那么,我們似乎就完全沒有必要再去尋求這種“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了。那么,在沒有這種“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的情況下,波洛克能夠解決“認識后退問題”嗎?
在波洛克看來,所謂的“基本信念”雖然不需要其它信念的辯護,但也不是自我辯護的,而是由其它某種非信念的東西來辯護的,比如“知覺狀態”。我們可以看到,波洛克的解決方式是將認識后退的終點向前推到了非信念的知覺狀態。問題是,這種知覺狀態能夠終止認識辯護的后退嗎?塞拉斯認為,這是不可以的,因為這種能夠為信念提供辯護的知覺狀態完全是一種神話,即“所與的神話”。在塞拉斯看來,這種知覺狀態混淆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1)作為一種認知狀態的知覺狀態;(2)作為一種純粹的物理刺激的知覺狀態。其中,只有在第一種意義上的知覺狀態才能進入“理由的邏輯空間”,也就是“辯護了以及能夠辯護某人之所言的邏輯空間”,從而才能作為辯護信念的理由,但是,由于它自己也是一種認知狀態,所以,它也需要其他理由的辯護。如此一來,它就無法終止認識辯護的無窮后退。而作為一種純粹的物理刺激的知覺狀態是無法為信念提供辯護的,因為它根本無法進入“理由的邏輯空間”。按照麥克道威爾的話來說,它處于“自然的邏輯空間”。所以,波洛克的“知覺狀態”如果只是一種純粹的物理刺激,那么,它就無法為信念提供辯護,而如果它是一種認知狀態,它雖然可以為信念提供辯護,但其自身也需要辯護。由此,它就無法解決“認識后退問題”。邦久對這種兩難困境有較為經典的表述,他說,這種知覺狀態“如果被解釋為認知性的,那么,它們就能夠提供辯護,但同時其自身也需要辯護;如果它們是非認知性的,那么,它們就不需要辯護,但顯然也無法提供辯護。歸根結底,這就是為什么認識上的所與是一個神話的原因。”如果所與真的只是一種神話,那么,波洛克的策略就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無法將基本信念的辯護最終訴諸非信念的知覺狀態。這樣一來,波洛克就無法用自己的“基本信念”去取代“自我辯護”意義上的基本信念了。
3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當波洛克主張“基本信念”是不必要的時候,他其實并不是在否定基本信念,而只不過是對基本信念進行了一種新的解釋而己。也就是說,他只是用一種新的“基本信念”取代了那種“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而己。如果這種“取代”是成功的話,那么,這也只是證明了:“自我辯護”的基本信念是不必要的。然而,即使僅僅就這一點而言,波洛克也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