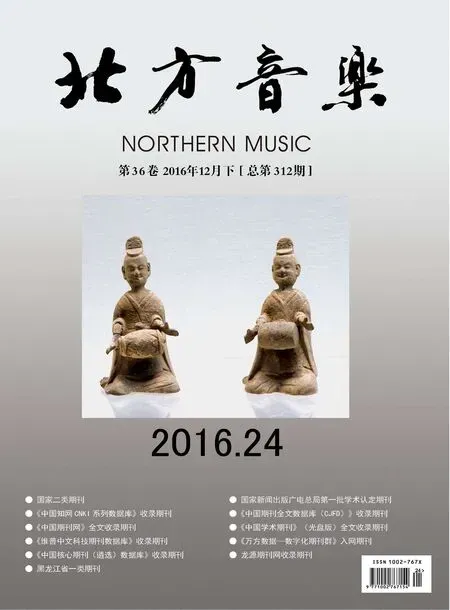節拍重音移位在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中的運用研究
偶瀟瀟
(合肥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安徽 合肥 230001)
節拍重音移位在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中的運用研究
偶瀟瀟
(合肥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安徽 合肥 230001)
約翰奈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5.7-1897.4.3),是19世紀歐洲浪漫派音樂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他一生中僅創作了一部小提琴協奏曲,即《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本文從節拍重音移位的角度針對此曲進行詳細分析,驗證當時勃拉姆斯在創作技法上的創新之處,從而豐富實際創作中的技法,拓展作曲思維。
勃拉姆斯;《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節拍重音移位;創新
一、節拍重音移位的概念及分類
“音樂是時間的藝術”[1],而節拍則將時間做長短相同的有規律的劃分。這種劃分最基本的手段是通過小節完成的,每一小節的第一拍為節拍重音,是節拍結構的重要特征之一,強調了節拍運動的規律性,與之相對的節奏重音則可以存在與一組節奏中的任意處,它的多變性和靈活性就可能會使樂曲中原有節拍的規律性遭到破壞甚至重組,從而產生節拍重音的移位。作為19世紀歐洲浪漫派音樂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在勃拉姆斯的作品中,節拍移位的類型基本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用重音或重新組合音型等方法來破壞既定的節拍,產生與既定節拍不同的節拍模式;仍然運用既定的節拍模式,由于破壞原有的強弱格式,造成重新劃分小節線的聽覺效果;旋律和其他聲部不在相同的節拍模式中。[2]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是勃拉姆斯成熟時期的代表作,可以說節拍移位已經成為他創作手法中的主要特征之一,他甚至將以上幾種類型混合在一起同時出現。
二、節拍重音移位在《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中的運用分析
節拍重音的移位所造成的節拍的模糊性是勃拉姆斯對于古典音樂結構形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的革新。作為一名學者型作曲家,勃拉姆斯特別仰慕貝多芬的作品。這首《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就被很多人認為在多處與貝多芬的同名曲有相似之處,但是在貝多芬的作品中,節拍重音的移位雖然已有所呈現,可持續的時間通常都很短,并且只在局部借用其張力展現內在的激情,而勃拉姆斯的音樂中,尤其是成熟時期的作品中,對于節拍重音的移位,他的處理和前輩相比則更冷靜,更合乎邏輯。
下面我們就通過譜例來加以印證。
譜例1

例1是第三樂章118-223小節的音樂片段,第三樂章的基礎節拍是2/4,在第120小節改換為3/4。在經過兩小節三拍子“強-弱-弱”的抒情演繹之后,作者通過改變四個十六分音符原有的組合形式,并重新標記上新的強音記號,變成每一拍都是強音,使得柔緩的三拍子一下子又轉換到激動的一拍子上。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里運用的是第一類型的手法。
與此同時,這里還出現了第三類型的手法,下方的樂隊聲部仍然按照3/4的節拍規律進行著,只是為了突出獨奏聲部的重音,在近乎相對應的地方做休止處理。
音型的重新組合以及重音的強調標記使得這種橫向上的節拍移位變的清晰明朗。而縱向上與樂隊之間造成的節拍重音的交錯又讓音樂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既使作品在三拍子的基礎上抒情、柔和,與之前強烈、奔放的二拍子形成鮮明對比,又增加了旋律的動感。
第二類型導致的節拍重音的移位則具體表現為利用連續的切分節奏造成節拍的模糊感。
譜例2

上例是第一樂章262-267小節的音樂片段,節拍是3/4拍,其中262-265小節的小提琴獨奏聲部就連續的運用了包括跨小節在內的切分節奏。構成切分節奏最主要的要素就是強拍位置上的音符時值要短于弱拍上的音符時值,從而削弱強拍位置上音符的節奏重音,并強調隨后而至的弱拍位置音符的力度。而連續的切分節奏強化了這種倒置的重音形式,從而使節拍重音發生移位并打破了固有節拍的韻律。與此同時下方的樂隊聲部卻分化為兩大陣營,一方面小提琴組仍然堅持著三拍子特有的節拍構成做十六分音符的重復性演奏,另一方面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又伴隨著獨奏小提琴節奏的律動,利用切分節奏不斷強化著旋律聲部的節拍重音位移。這種聲部之間的沖突恰恰呼應了展開部旋律中所帶有的動蕩不安的情緒。
勃拉姆斯對于節拍重音移位的手法不僅更為復雜,他運用這一手法所構建音樂的位置和前人相比也更為重要。
譜例3

例3是第一樂章第二呈示部副部主題206-223小節的音樂片段。
獨奏小提琴聲部通過弓法上的變化以及重音記號的標記,使得音樂在2/4的重音規律下流動,而此時的樂隊聲部則仍然維持在3/4的節拍律動下,在第214小節主題旋律又在第一小提琴聲部和中提琴聲部得到重復并和獨奏小提琴聲部相互交替,從而使得節拍重音的移位變的更為復雜化。相對較長時間的規律性的節拍重音移位,可以形成新節拍,與其他聲部共同構成了多節拍。
通過此例我們不難看出,利用這種手法在相對重要的主題段落中對音樂進行拓展,這在古典主義時期還尚不多見,而此時的節拍重音的移位已成為主題發展的一種手法。起到了拓展了主題發展空間,模糊段落之間界限的作用。
安徽省教育廳質量工程項目“音樂教育專業教學團隊”(項目編號:2015jxtd054)階段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