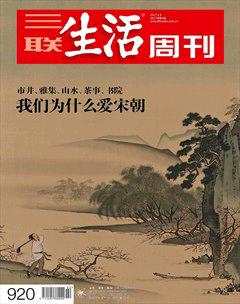顯影
德琨若魚+謝馭飛
白天一陣暴曬,黃昏時下了場暴雨,夜里站在高樓上看遠處的大橋,橋燈和車燈額外剔透,偶爾破空地傳來幾聲掃興的汽車喇叭車,讓D從沉思中回了回神。這是座長江上游的小山城,沿著江岸是山,山上疊著房子,都是江景房,人人都住在山上。D第一次順江而下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看過三峽,在船尾發呆看浪花的時候,總希望江里有條躲避不及的傻魚被浪花翻出來。
“整理郵箱發現很久以前的這封信,我想你……”短消息的告知聲讓D從橋上收回視線,今天是她的生日。早就跟家里人說好不過生日啦,這幾年倒是客戶把生日記得很牢,準時準點地發祝賀信息,提醒D:“你又老了一歲,該保養了,該買保險啦……祝你生日快樂!”因為是陌生人,也就不喜不惱。但他還記得D的電話號碼:“生日快樂……你是我一輩子的念想。”找個借口,才可以發條短信,生日不是重點,“念想”比“想念”更刻骨嗎?“謝謝。”D很快回復了,她是他的初戀,但他不是。他教會她洗膠片,配顯影液、定影液,在暗袋里把相機里的膠卷取出來繞進顯影罐里。暗袋有兩只袖子,他們把四只手都伸進去,他手把手地教她拆和裝,把膠片繞到軌道里是難點,她總是有些惱,便在暗袋里掐他的手。洗出來的底片有些漏光,光從暗袋的袖子里鉆進去了,好歹,她是學會了。只是依賴性太強,曝光時總問他,今天的日光該開多大的光圈、曝光速度多少呀?
有一天他不在身邊,她拍的那些照片都灰蒙蒙的,他說曝光過度了,顯影液也配稀了。后來,她故意不讓他在身邊,他送來的那些膠卷也不想拍了,藏到鞋盒子里,暗袋的袖子完全松了,不縫補的話就漏光;再后來,膠片過時了,她買了臺數碼相機,再不用問他光圈、快門速度了,也不再見他了。他還當著那個攝影社團的社長,教一些文藝青年拍照、洗膠片。在校園的銀杏樹下看到他教社團的小姑娘拍照,孱弱、蒼白,是在暗房里待久了不見陽光的脆弱感,亮黃的銀杏葉落了一地,反光到他臉上倒有些生氣勃勃。那天晚上,他在暗房里喝了她配的顯影液,還好,她配稀了。她到醫院里看他時有些反胃,用力掐了掐他的手,“疼嗎?”“疼。”“傻嗎?”“不傻。”
因為這個沉重的負擔她選擇了離開這座城市,逆流回到了長江上游那座山城。走的時候書、被子都不要了,仔細地用避光紙把他送的未拍的膠卷裹好:柯達、樂凱,保質期5年。現在,這些膠卷還放在冰箱里,已經15年了。D拍了一卷,在暗袋里摸索了好久,才把膠片纏繞到罐里的軌道中,洗出來,剛好。配的顯影液濃度剛好,曝光時間也剛好,膠片保存得也剛好。D放眼望夜幕下的山城,白天的曝光、黃昏的暴雨顯影,現在正好是透視膠片的時候,日子都被定影下來了,這個生日,謝謝他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