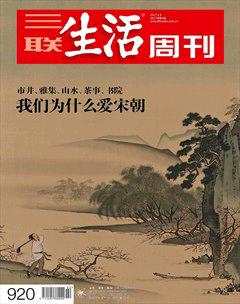固執默克爾:慷慨的代價
徐菁菁
放棄接受難民的政策,顯然不是默克爾的選擇;但堅持,則更是一場漫長甚至慘烈的戰斗。
轉折?
盧卡斯·烏爾班(Lukasz Urban)載著裝滿25噸鋼材的貨車一路從意大利都林駛向柏林。他將在柏林卸貨,完成圣誕假期前的最后一項工作,踏上返回家鄉波蘭羅茲諾沃(Roznowo)的旅程。2016年12月19日上午,盧卡斯抵達柏林。下午14點,他在柏林倉庫附近的一家烤肉店休息了一會兒。15點左右,盧卡斯和妻子通了電話。他聽上去心情愉快,他說,由于他提前一天抵達到了柏林,倉庫第二天才能卸貨,他得在柏林逗留一個晚上。可是到16點左右,運輸公司老板阿雷爾·祖拉夫斯基(Ariel Zurawski)卻發現他打不通盧卡斯的電話了。貨車上裝載的GPS系統每10分鐘向祖拉夫斯基匯報一次貨車的動向。祖拉夫斯基發現,15點40分左右,車輛的行動開始變得十分奇怪。它始終在一個小范圍的區域不停地前后移動,好像是有人在學車,絕不像是擁有十幾年駕駛經驗的盧卡斯的所作所為。半小時后,車輛停止不動了。直到晚上19點40分,貨車再次發動,并向著柏林市中心駛去。
這個晚上,德國總理默克爾正在出席一場為慶祝“種族融合”而舉行的活動,她在講話里談到多元化和對抗歧視:“我們共同生活在多元化之中。正是多元化讓我們更加富有,而非更加貧窮。”她表彰那些服務于難民的志愿者,鼓勵他們“保持開放與公正”,“如果事情的發展和你料想的不同,也不要讓它碾碎你的信念”。
與此同時,人群聚集在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的廣場上。威廉皇帝紀念教堂位于柏林最主要的購物區選帝侯大街的核心地段,它由戰爭損毀的殘缺部分和戰后新建的現代主義建筑兩部分組成,是德國戰后重建和反思戰爭的象征。教堂周邊的廣場,是游人、街頭藝術家和紀念品商販的天堂。圣誕節來臨之際,廣場變身柏林最大的圣誕市場之一。20點左右,盧卡斯的貨車出現在了廣場上。車輛先是沿著圣誕市場繞行了一周,接著它以每小時60多公里的時速,從東向西高速沖進市場,碾壓過攤位和游人。
現場目擊者說,卡車司機“有著東歐面孔”。事后,人們在貨車的乘客座位上發現了盧卡斯的尸體。警方的調查顯示,在恐怖襲擊發動之時,盧卡斯仍然活著。他曾試圖從恐怖分子手中奪回方向盤,這解釋了貨車沖向市場時為何行進得歪歪扭扭。盧卡斯身負數刀,最后,一顆子彈射入了他的頭部。人們相信,如果不是他最后時刻的努力,貨車對人群的沖撞極有可能造成更大的傷害。包括盧卡斯在內,威廉皇帝紀念教堂見證了12人的死亡和50余人的受傷,他們來自至少8個不同的國家。
20日,默克爾一身黑衣,發表了簡短的電視講話。她將貨車沖撞事件定性為恐怖襲擊。罕見地,她直接在講話中提到了襲擊者的難民身份:“我知道,如果我們證實這一行為是由在德國尋求保護和庇護的難民進行的,我們大家都將感到十分難過。”不幸的是,人們很快知道,襲擊的執行者突尼斯人阿尼斯·阿姆里斯(Anis Amris)確實是以難民身份進入德國的。
過去一年里,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去年7月中下旬,德國在一周內接連發生了4起暴力襲擊案件。7月18日,一名17歲的阿富汗裔男子在維爾茨堡附近的一列火車上持斧襲擊乘客,造成4人受傷,其中3人傷勢嚴重。7月22日傍晚,慕尼黑市中心以北大約10公里的奧林匹亞購物中心發生槍擊案,一名德國和伊朗雙重國籍的18歲男子槍殺9人后自殺身亡。7月24日晚上,在安斯巴赫市中心一家餐廳,一名27歲的敘利亞男子在試圖進入巴伐利亞小鎮舉行的露天音樂會未果后引爆炸彈身亡,同時造成12人受傷,這是德國多年以來的首次自殺式爆炸事件。同一天,一名來自敘利亞的21歲難民在羅伊特林根市一處公交車站砍死1名孕婦、砍傷2人后被捕。
而這些事件的沖擊力均不及柏林恐襲。雖然“伊斯蘭國”組織宣稱對火車上砍人事件負責,但當時德國警方認定,4起案件均沒有明顯的政治訴求,也沒有縝密的犯罪計劃,與發生在法國和比利時的恐襲案有本質區別。24日上午的敘利亞難民砍人事件源自“口角紛爭”。慕尼黑槍擊案的案犯生于慕尼黑,從小在慕尼黑長大。而且幾乎每個作案人都有患“精神疾病”的可能。在安斯巴赫發動自殺式爆炸的敘利亞男子曾因自殺未遂而兩度入院治療。而慕尼黑槍擊案案犯接受過精神病和藥物治療。雖然一些人懷疑,這些調查結論是官方在刻意削弱暴力案件中的“極端宗教”和“難民”因素,但事實上,在德國社會的主流層面,無論是政府、媒體還是民眾,都表現出了驚人的冷靜和團結。除了極右翼黨派新選擇黨之外,德國政客和媒體在談論上述4起暴力襲擊案件時都小心翼翼地避開了“恐怖主義”和“反恐戰爭”這些詞語。
阿尼斯·阿姆里斯不同。2015年11月起,他就被列入德國安全機構內部一份由549人組成的“危險分子”名單。他被證實曾與德國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阿布·瓦拉有聯系,后者被視為極端組織在德國的頭號人物,為“伊斯蘭國”招募武裝人員。這意味著,默克爾受到這樣的指責將難以為自己辯解:正是她的開放性難民政策使恐怖組織得以在德國展開殺戮。這一次,默克爾會改變嗎?
誰的錯?
過去一年里,有兩次,人們以為嗅到默克爾“認錯”的信號。2016年9月,柏林地方選舉落下帷幕。她所領導的執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嘗到了歷史性敗績,不僅與聯合執政的社會民主黨失掉多數席位,其得票率更跌至“二戰”后最低水平。默克爾在選舉的第二天說,執政黨和政府需要努力做得更好,因為過去一些年里在難民政策上“并不是每件事都做得對”。12月6日,默克爾在基督教民主聯盟黨代表大會上的黨首競選演講中,一改此前不置可否的態度,談到穆斯林面紗問題。“我們要在人際交流中露出臉來,因此全臉面紗是不合適的,應該在所有法律可行的場合予以禁止。它不屬于我們的國家。”
但是,如果仔細審視默克爾的言行,她并非真的認為自己錯了。對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爭議主要集中于兩點:2015年的8月25日,她是否應當宣布不再按照《都柏林規則》把入境的敘利亞籍避難申請者遣送至他們進入的第一個歐盟國家?德國是否應當在接納難民的人數上不設上限?
默克爾9月的表態被許多媒體斷章取義。她確實說過“寧愿時光倒流”,但她的完整表述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寧愿時光倒流到很多很多年前,這樣我、聯邦政府以及負有責任的各方能更好地為此(難民危機)做好準備。2015年夏秋之際,我們更像是毫無準備地遇上了這場危機。”她說自己曾經以為《都柏林協定》能夠解決德國所面臨的難民壓力,“但事與愿違”。換句話說,默克爾認為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各方沒有為難民危機的到來做好準備,而不是是否應當接受難民潮的挑戰。她甚至重申了接納難民的道德意義:“我絕對確信,當我們從這段艱難的階段走出來時,將比走入這個階段時變得更好。只要我們不是鐵石心腸,那么我們變成什么樣,德國就會變成什么樣。”
如何理解默克爾的“頑固”?如果建立一個坐標體系,厘清默克爾難民政策在德國歷史和歐洲現實兩個維度上的位置,則會有一些紛擾輿論之外的發現。
“慷慨”并不是默克爾的一貫態度。“二戰”結束后,聯邦德國在起草《基本法》時,制定了一條不加限制的避難條款:“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享有避難權。”這成為德國難民政策的基本原則。1988至1992年,蘇聯鐵幕落下、柏林墻倒塌和南斯拉夫戰爭爆發導致來自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的避難申請迅速增長。為應對這股潮流,1993年《避難妥協法》生效。新的避難條款在《基本法》第16條上增添了新的條款,對避難權進行限制。《避難妥協法》第一個核心是“第三國條例”,即如果難民經過歐共體國家或者《日內瓦公約》和《歐洲人權公約》適用的“安全第三國”,則不得在德國申請避難。由于德國處于歐洲中部,被稱為歐洲的十字路口,所有相鄰的國家都屬于“安全第三國”,因此按照這項條款的要求,幾乎沒有一個避難申請者能夠不經過安全第三國通過陸路到達德國。
2005年11月22日,默克爾正式成為德國總理。從她就任到2015年8月,德國對申請避難者的管理事實上在不斷收緊,也談不上所謂慷慨。多年來,能夠依據《基本法》第16條獲得政治避難權的申請避難者人數比例僅在1%左右。2014年德國政府修改了法律,在德國停留3個月后,申請避難者方可擁有在德國范圍內自由活動的權利。2015年,德國政府規定,申請避難者在申請審核期間的活動區域限制在特定州或城市,如違反規定,將必須繳納一定的罰金,嚴重者將面臨刑事懲罰。2013年前,申請避難者每月從德國政府那里獲得225歐元的補貼,其中大部分是以實物或者購物券的形式支付的。直到2012年7月18日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德國申請避難者的待遇低于該國最低生活標準,不符合憲法中關于人權的規定之后,德國政府才通過過渡性規定將庇護尋求者的補貼提高到350歐元左右。從申請避難者的人數來說,德國毫無疑問是歐盟國家中申請避難者最重要的目標國。但若考慮到本國居民人數,德國并不總是歐洲國家中負擔最重的國家。2013年,平均每1000個瑞典居民中有5.7個申請避難者,德國則是1.6個,位于歐盟國家中的第10位。
默克爾生長在東德,柏林墻轟然倒塌那年,西德鄰居不計前嫌,接納她的一家。2015年8月的那個節點,許多人相信情感和道德是左右默克爾決策的主要原因,但這并不是無懈可擊的解釋。就在7月15日,默克爾在與一群中學生錄制“生活在德國”電視節目時,一個名叫里姆的巴勒斯坦裔女孩對她說,她一家人為等德國的永久居留權等了4年,父親作為焊接工的臨時簽證已經到期,一家人將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她在德國求學的愿望也將泡湯。“你是個特別好的人,但你要知道,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難民營里可有成千上萬的人,要是我們說聲‘你們都過來吧,到時候我們可控制不了局面。”默克爾說。那個時候,里姆的眼淚讓不少德國政客和德國人都在互聯網上批評默克爾的冷漠無情。
若回到8月當時的情景,決策的思量可能復雜得多。對于彼時的默克爾來說,她在那個決定性時刻回答的問題,也許不只是德國如何對待難民,而是德國在歐洲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2015年初,地中海接連發生的沉船事故使得有關難民問題的討論呈現白熱化狀態的時候,歐盟委員會提出了防御方案,包括以增加歐盟邊境管理局的人力與資金和擴大搜救范圍為主的“十點計劃”,并提出各成員國應承擔相應責任,接受有約束力的“難民配額”。在6月的歐盟首腦峰會上,各國在防御問題方面達成一致意見,但在“難民配額”問題上爭執不下,當時,德國并未在該問題上做出更為積極的努力。
然而局勢發展的速度超過了預期。2015年,敘利亞內戰進入第四年,許多敘利亞人已經徹底對戰爭的終結失去耐心和信心。無論是在敘利亞國內還是在周邊國家的難民營,人們的生計都越來越艱難,進入歐洲避難成為一場沒有什么可失去的冒險。
多年來,除了德國國內的法規,將德國與難民潮阻隔開來的屏障是歐盟的《都柏林公約》。根據該協議,難民在進入歐盟的第一個國家進行難民申請登記,該成員國負責對難民身份的核實和甄別,難民沒有權利選擇自己想去的歐盟國家,德國警察只要搞清難民是從哪國入的歐盟,就可以將難民遣返回最初入境國。然而,僅2015年7月一個月,歐洲各國邊境就截獲10.75萬名難民,數量達2014年同期的3倍。僅在7月8日一天,德國聯邦警察就發現了超過1000名非法入境者。這些數字都說明一點:在罕見的難民潮面前,《都柏林公約》已經形同虛設,歐盟原有的難民處理機制失效。事實上,此次柏林襲擊事件的制造者阿尼斯·阿姆里斯在2015年6月就進入了德國。
2015年7月,大批難民滯留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火車站,在充滿尿液氣味的地下通道挨過一夜又一夜。一個死結產生了:難民們絕無離開歐洲的可能,匈牙利也絕無接納他們的可能。而其他歐洲國家則忙于相互指責:英國指責法國沒有負起監管非法移民的責任,致使大量非法移民通過連接兩國的海底隧道偷渡至英國,法國批評意大利和希臘放任難民在歐洲流竄,意大利和希臘又把矛頭對準西歐和北歐富裕國家,不滿它們袖手旁觀。歐盟的共識管理機制已經停擺。
7月,匈牙利總理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向歐盟領導人提出了一個問題:“申根還是通道?”他的意思是,他打算為難民開辟一條去德國的通道。歐爾班得到的回答是“不”,《都柏林公約》不可違背。然后他又提出:“那么我們需要一堵圍墻。”害怕丟失人道主義歐洲精神的布魯塞爾再次回應說:不要圍墻。歐爾班沒有把布魯塞爾無解回應放在心上。消息傳出來,一堵封閉巴爾干路線的圍墻在9月就要修好,恐慌促使更多的人踏上了奔赴歐洲的征程。
8月21日,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署表示,凡是來自敘利亞的避難申請者,將不必再遵守《都柏林公約》,德國不再根據公約的要求,審核他們此前是否從另一個成員國進入歐盟,并因此將他們遣返回該成員國。接著,8月23日德國薩克森州小鎮海德瑙攻擊難民營事件、8月27日奧地利貨車發現70多具難民尸體,以及9月3日小男孩艾蘭尸曝沙灘,接二連三的慘劇進一步將默克爾逼到了墻角。9月5日,她與奧地利、匈牙利領導人達成一致意見,允許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進入德國。
德國《明鏡》周刊描述難民潮抵達時的情形。手持“感謝你,德國”標語的難民與手持“歡迎你,難民”標語的德國人相聚在一起。這一情景代表了許多德國人夢寐以求的德國形象。整個國家陷入一種道德優越感帶來的狂喜之中,這種喜悅甚至能夠與2006年德國國家隊奪取世界杯冠軍相提并論。
以德國的角度看來,恰恰是德國的慷慨,使得歐盟這個價值共同體免于因拒絕難民而在國際社會喪失信譽。作為歐洲的領導者,德國人奔赴了他們不得不奔赴的戰場,然而這勢必是一場慘烈的戰斗。
措手不及
事實上,德國在2015年9月13日就重新引入了邊界控制。巴爾干路線也很快被封閉。10月初,聯邦國防軍被允許在沒有人員傷亡的情況下,直接銷毀地中海區域“蛇頭”的船只。此前,他們只被允許搜救難民及探查“蛇頭”信息。10月中旬,聯邦議院和聯邦參議院先后通過了“避難一攬子法案”,包括進一步區別對待有無避難權的難民。西巴爾干國家被評級為“安全國家”,來自這些地區的避難者不會在德國獲得難民身份,對于這些難民,德國將壓縮其社會福利給付,并將其直接驅逐出境。聯邦內政部在10月21日決定對敘利亞難民重新適用《都柏林公約》中規定的程序。2015年,有超過100萬難民進入德國。2016年,盡管默克爾仍拒絕為接難民數字定上限,但截至9月,來到德國尋求避難資格的難民也只有不到30萬人。
然而正如默克爾在2016年9月的反思,德國的危險“是毫無準備地遇上了這場危機”。總理也承認,自己的那句名言“Wir schaffen das(我們可以搞定)”,成了“一個簡單的口號,幾乎只是一個空洞的公式”。2015年8月18日的一次會議上,內政部長托馬斯·德邁齊埃預計將有超過80萬難民進入德國,“挑戰之巨大前所未有”,“國家的避難和接收系統很有可能崩潰”。事實上,系統早已經失靈。2015年5月,由于涌入德國的難民人數巨大,警方不得不放棄了記錄每位難民全部十根手指指紋的做法,而且他們也弄不清這些難民從哪兒來,要到哪兒去。
柏林恐怖襲擊案件的偵破再一次證明了德國在應對難民與防范恐怖襲擊問題上缺乏必要的經驗和部署。2016年12月19日案發后,柏林警方迅速逮捕了一名嫌疑人。這名23歲的巴基斯坦難民正因害怕被當作嫌疑人而逃離案發現場。柏林警方搜查了他居住的難民營,分析了他的手機。該巴基斯坦男子身上并沒有射擊殘留物,也沒有搏斗痕跡,但直到法醫證據顯示該男子并沒有在貨車里待過,警方才意識到真正的兇手可能已經逃之夭夭。接著,就在肇事貨車司機座位下面,警方發現了真正的兇手遺落的身份證件,這時候距離事件發生已經過去了差不多20多個小時,兇手依然持械在逃。直到23日,嫌犯阿姆里斯在米蘭火車站外被警方擊斃時,德國方面還以為阿姆里斯躲藏在柏林或者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一帶,一直都集中在這兩個區域進行搜索。
阿尼斯·阿姆里斯身份的曝光更讓人大跌眼鏡。阿姆里斯在突尼斯曾因搶劫被判5年監禁。2011年,他進入意大利,先是被安置在西西里島一個未成年難民收容所。在此期間,他因損壞他人財物、縱火等行為,被法庭判處4年監禁。因在監獄服刑期間有暴力行為,2015年初獲釋后的阿姆里斯被意大利方面遣送出境,但因意大利與突尼斯當局產生分歧,遣返計劃受阻。阿姆里斯此后輾轉前往德國。他先是在北威州小城艾梅里希的一處難民收容所落腳,此后一直在北威州和柏林兩地活動,至少使用過12個不同姓名和3個不同的國籍。
阿姆里斯的個人Facebook主頁上非常明顯地顯示了他的極端主義傾向。2015年11月起,阿姆里斯因與德國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阿布·瓦拉有聯系,被列入德國安全機構內部一份由549人組成的“危險分子”名單。此外,美國也在2015年將阿姆里斯列入禁止入境名單。事實上,阿姆里斯從去年3月起就受到警方監視,但有關懷疑沒有得到進一步證實,因此對他的監視措施于9月終止了。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早在去年6月,阿姆里斯向德國政府申請政治避難就被正式拒絕,并被要求限期離境。北威州內政部長耶戈爾表示,由于阿姆里斯沒有合法旅行證件,德國政府沒有辦法按照合法流程把他遣返回突尼斯,所以只好把他繼續留在國內。而就是柏林慘案發生后的第三天,突尼斯當局為阿姆里斯提供的旅行證件終于送抵德國。
代價
雖然人們當時并不清楚殺手的身份,但柏林襲擊發生后的一個小時,右翼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fD)的領軍人物之一馬庫斯·普雷策爾(Marcus Pretzell)就在Twitter上宣布:“這些人都是默克爾害死的!”不幸的是,后來的調查證明了他對殺手身份的推測。新選擇黨的宣言是“勇于面對真相”(Mut zur Wahrheit),這回的互聯網投機再一次為它贏得了直言不諱的聲譽。
3年前,一位名叫柏恩德·盧克(Bernd Lucke)的經濟學教授創立了新選擇黨(AfD)。盧克是一名自由保守派、樸實的加爾文主義者,他反對共同貨幣歐元,抵抗歐元區經濟危機下利用公共資金拯救銀行和負債歐元國的行動。但后來,弗勞克·佩特里(Frauke Petry)領銜的民族保守派、右翼民粹主義派將柏恩德·盧克擠出了權力圈。弗勞克·佩特里最著名的口號是“伊斯蘭不屬于德國”,她甚至曾經放言緊急情況下必須在邊境使用射擊武器制止難民。
去年9月的柏林地方選舉,新選擇黨贏得了14.2%的選票,盡管沒有實現它在選前喊出的20%的目標,但也足以讓它在首都站穩腳跟。新選擇黨已在德國16個地區議會中的10個擁有席位,以目前的情勢,它很有可能在今年秋天的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中邁過5%的得票率門檻,成為“二戰”以后成功躋身德國國會的首個名副其實的右翼政黨。
毫無疑問,新選擇黨的崛起得益于“德國式恐懼”。2016年3月的福索民調(Forsa Institut)結果顯示,59%的德國民眾對于恐怖襲擊的威脅表示不安,52%的德國人對于難民潮產生恐懼情緒,72%的德國民眾認為德國政客并不了解難民危機為民眾帶來的不安與恐懼。這種恐懼還來自對難民爭奪社會福利資源的擔憂。科隆經濟研究所預計,2015~2017年安置難民以及融入課程的費用接近560億歐元,每名難民平均每年花費為1.5萬歐元。歐債危機后德國貧困人口比例雖有所下降,但人數始終超過1100萬。德國長期失業者享受“哈爾茨四”救濟金,每月獲得404歐元現金補貼,且報銷房租及取暖費用,難民救助消耗的費用已然超過對德國人的社會救濟金。
默克爾付出的政治成本是顯而易見的。基民盟在地方選舉中的得票大幅度下滑。在執政聯盟內部,基民盟的姐妹黨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亞州長澤霍夫多次呼吁政府設定本年度進入德國的難民數量,甚至威脅要將聯邦政府告上法庭。
但目前,并沒有證據顯示默克爾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英國《金融時報》一位資深專欄作家說,他曾問過一位英國資深政治人物,默克爾式的“開門”難民政策在英國能堅持多久,對方回答說:“不到24小時。”很顯然,默克爾的頑固建立在“穩定”之上。
德國發行量最大的日報《圖片報》(Bild)去年11月21日所做的最新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17年德國大選的候選人中,默克爾仍擁有55%的支持率。這并不奇怪,在地方選舉中,綠黨在巴登-符騰堡州獲得了30%的得票率,綠黨州長克萊詩曼(Winfried Kretschmann)公開支持默克爾的難民政策,由于過于熱衷于支持默克爾,號稱每日都為默克爾的健康祈禱,德國媒體給克萊詩曼起了“默克爾的追星族”的稱號。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獲勝的社會黨人德萊爾(Malu Dreyer)也是默克爾難民政策的支持者。這都意味著默克爾能夠獲得大量跨黨派的支持。
去年12月6日基督教民主聯盟舉行代表大會,默克爾以89.5%的得票率再度成功連任。在她長達80分鐘的演講中,在場的1000名基民盟黨員多次長時間鼓掌,最長的一次起立鼓掌持續時間超過11分鐘。德國電視二臺“政治晴雨表”民意調查在11月25日公布的結果也顯示,64%的受訪者支持默克爾謀求連任總理的決定。德國政壇并未涌現出足以對默克爾提出強有力挑戰的政治新星。
對于默克爾來說,未來的最深刻挑戰可能并不是當選連任,而是如何面對德國變得日益斑駁且難以捉摸的政治光譜。
“二戰”后的德國政治以穩定著稱,德國政治代表的兩大支柱是基督教民主聯盟(與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一起)和社會民主黨。幾十年來,兩個政黨分別代表左翼和右翼政治,分享80%的選票,其規模大小足夠應對危機,也是達成共識和妥協的擔保者。親商的自由民主黨和環保主義的綠黨則是政治格局善意的補充,而且很容易團結。在傳媒領域,也存在左右兩個陣營。由記者扮演的看門人角色過濾掉了仇恨、陰謀論等負面信息,使政治辯論更加溫和,更有建設性。這些都是德國政治妥協得以實現,國家正常運轉的條件。
德國《明鏡》周刊編輯德克·庫博威特評論說,在難民危機的沖擊下,德國的這種穩定性正在被碾碎。很多德國人不再認可國家的政黨格局。有些曾經一直都支持社民黨或綠黨的人,現在成了默克爾的鐵桿“粉絲”。而另一些一直支持基民黨的人卻在呼吁她下臺,以維持真正的基督教德國。而以新選擇黨為代表的德國右翼民粹主義則打破了德國政治的右半部分,它們受益于互聯網,引領著傳統政治場域之外的互聯網上的排外主義潮流,使得政治的對立更為尖銳和難以調和。
一種更為危險的潛流藏于其中。去年9月的地方選舉中,柏林的結果并不是最讓默克爾擔憂的。9月4日,默克爾在自己的選區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遭遇了一次難堪的挫敗。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國東北部波羅的海沿岸的一個以鄉村為主的地區,新選擇黨一舉拿下20.8%的選票,將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擠到了第三位。這次選舉后,默克爾一反常態,對這個右翼政黨發表了指名道姓的打壓性言論。她在聯邦議會演講時呼吁德國政壇主流政黨團結起來對抗民粹主義并贏回選民的信任。她警告說,新選擇黨勢力上升“對于這座大廈里的所有人都是一種威脅”。她還要求主流政黨的領導人不要將精力花在謀求針對彼此的“細微優勢”上,這顯然是在批評執政聯盟內部的社會民主黨和巴伐利亞州基督教社會聯盟一些帶有各自政治訴求的同政府唱反調的主張。
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國的一個縮影。在安置難民人數最多的巴伐利亞州,基社盟以明顯優勢贏得州議會選舉。而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其實并沒有多少穆斯林難民和移民,也不是恐怖襲擊風險大的地區。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位置閉塞,據說當年俾斯麥曾開玩笑說,如果世界末日到來,他將會搬到梅克倫堡去住,因為災難要過50年才會抵達那里。梅克倫堡-前波莫瑞州和巴伐利亞州的差別客觀上代表了東西德的差別。新選擇黨在前東德地區的異軍突起格外顯著,在原東德各州的選舉中,它大都以得票雙位數的驕人成績進入議會。
選票顯示出東西德在一個重要問題上從未彌合的分歧:究竟什么是德國?新選擇黨公開宣稱支持“德意志主導文化”(Deutsche Leitkultur),強調“德意志”身份認同。去年5月,新選擇黨甚至將黨綱當中一個小節的標題直接改寫為“伊斯蘭教不屬于德國”。這些主張,在德國政治中都曾是不可言說的禁區。
“二戰”后,德國憲法堅決消解“族群民族主義”,強調基于法權意義而非血統、文化的公民身份。兩德統一以來,聯邦德國在社會建設各方面全面摒棄一切有“納粹性”的做法,以至于社會各界提及“國民性格”“民族文化”相關話題時都諱莫如深。學校不升國旗、國慶日低調慶祝、公共言論中對“種族”“族群”概念也十分謹慎。政治家都回避意識形態方面的討論和動員,而是著眼于具體的政策細節。默克爾的傳記作者斯蒂凡·柯內琉斯曾說,對默克爾來說,所謂自由,首先意味著不受意識形態桎梏。有一次,默克爾在電視節目上被問及“德國”這個詞會讓她想起什么,她的回答是:“精美、擋風的窗戶。”
但這種傳統是基于西德的。西德主動地、有意識地放棄許多“德國”的特性,取而代之以多元主義與人道主義等價值認同。1990年的兩德統一,解決了認同哪一個德國的問題,但卻沒有在認同上達成一致。
德國東部的發展與西部經歷了完全不同的過程。首先在如何理解和對待納粹德國的歷史這個問題上,東西德有本質的區別。民主德國的領導層在納粹時期都是堅定的反法西斯戰士,對于他們而言,德國不存在贖罪的問題。統一社會黨領導把民族社會主義的罪責歸結到“一小撮”法西斯分子頭上,而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對東德地區的納粹頭目進行了鎮壓,用迅速培養起來的干部取代有污點的老一輩官僚,同時宣布,“大多數”德國人民是受蒙蔽的,因而是無辜的。這樣一來,東德并沒有開展罪責與集體罪責的大討論,并不存在對于“民族”的清算和規避。1989年東德民眾反抗昂納克政權時提出的口號是“我們是一個民族”,從這一點就可以解讀出東德民眾的民族觀。事實上,兩德統一后,德國東部的排外情緒一直十分強烈。
今天的德國,東西之間差異依然非常明顯。2015年,西部每戶家庭平均凈資產為15.3萬歐元,東部家庭為11萬歐元。統計顯示,德國平均每500個富人中僅6個生活在東部地區。大約四分之三的東部人沒有參加宗教社團,這與西部的情況幾乎相反。無論在政治還是在經濟上,西德都占據統治性地位。不得不說,新選擇黨的崛起是東德人在動蕩的局勢中釋放的信號。
目前看來,以穩定和沉著著稱的默克爾依然可能采取以不變應萬變的姿態。她可能會在一些枝節問題做出讓步——她將推動加快對尋求庇護者的處理過程,遣送更多未被認定難民資格的人,她還將允許基民盟做出象征性姿態,比如禁止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場所穿著伊斯蘭罩袍,但她并不可能放棄她對德國價值的堅持。默克爾為2017年德國大選準備的競選綱領提出了“安全”和“不做實驗”。“不做實驗”是戰后第一任聯邦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最早提出的。他認為德國人從來都不缺思想和點子,更加不缺把各種日新月異的點子付諸實行的人;但是從1848年革命到俾斯麥,從魏瑪共和國到納粹德國,矗立在柏林的勃蘭登堡門見證了各種思潮的激烈碰撞,不同時期的不同抉擇讓德國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戰后聯邦德國采用的黑、紅、黃三色國旗仿佛回歸到1848年革命者們的最原始訴求:統一、公正、自由。
問題是,默克爾的穩健是否能夠抵擋德國政壇日益活躍的挑唆性言論和有目的的打破禁忌。2014年,新選擇黨曾經晉身德國東部三州議會。但隨著危機的回落,它的支持率在全德范圍內并無起色。此次難民危機之際,民調顯示,真正信奉選擇黨政治綱領的民眾也不占據多數。觀察三州選情可知,選擇黨在薩安州的選票中只有27%認同其政治綱領,而64%的選民是基于對其他政黨的不滿而投票給選擇黨,巴符州由基民盟流失至選擇黨陣營的選民中有75%是對現行的難民政策感到失望。全德來看,認為選擇黨有助于解決聯邦州難民問題的民眾只有13%,而79%的人不認為選擇黨有能力解決危機。
默克爾最大的威脅不是新選擇黨而是恐怖主義。對恐怖主義襲擊,她無法做出任何擔保。她只能期望,在未來還有可能發生的襲擊中,德國人能夠一如既往地保持理性,拒絕仇外主義的反穆斯林論調,接受他們為多元主義和人道主義付出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