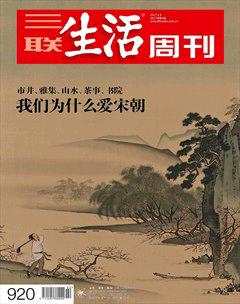依然要思考80年代
孫若茜
以甘陽為核心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是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談及當時就不能繞開的關鍵一節。他們在當時拋出的關于“古今中西之爭”的思考延續至今。
“80年代似乎已經是一個非常遙遠的時代。80年代的‘文化熱在今天的人看來或許不可思議:‘文化是什么?這虛無縹緲的東西有什么可討論的?不以經濟為中心,卻以文化為中心,足見80年代的人是多么迂腐、可笑、不現代!但不管怎樣,持續近4年(1985~1988)的‘80年代文化熱已經成為中國歷史意識的一部分,而對許多參與者而言,80年代不但是一個充滿青春激情的年代,而且也是一個純真素樸、較少算計之心的年代。”
2006年,甘陽選編的《中國當代文化意識》(1988),這本反映了“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在80年代期間思想、文化傾向的書再版時,身為主編的他,在“再版前言”中寫下了以上一段文字。如今又十年,甘陽所說的“遙遠”變得更加遙遠,而作為中國歷史意識一部分的“文化熱”,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產生且將持續產生著影響,不止之于參與者。
以甘陽為核心的編委會,正是那場由時代引發的“文化熱”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談及80年代就不能繞開的一節。據回憶,編委會成立時,并沒有隆重的儀式或會議,日常的工作里也沒留下什么如今可拿來回顧的記錄一類的東西,相比其他在當時就已經預見自己將要進入歷史的學術團體來說,他們實在缺少那種自己即將或準備創造歷史的意識,只是自發地在做自己喜歡,剛好朋友們也喜歡的事情。但是,他們在當時拋出的關于“古今中西之爭”的思考,為拓寬視野出版的批量西方學術經典譯著,至今也依然在幫助我們拓寬認識的疆界。
更為重要的是,編委會的甘陽、劉小楓、陳來等核心成員們,今天還在持續地做著推動通識教育、編輯叢書等等學術組織工作,這使得我們在他們身上所能見到的思想的改變或延展,不止于他們各自的30年,更是變化中的思想界的30年。
編委會成立“每個人都在讀海德格爾”
1982年,甘陽開始在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讀研究生。畢業后,他被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現代外國哲學室。正是80年代“文化熱”掀起之時,社科院一些人準備籌辦一個雜志,找他當主編。雖然他們彼此間不大認識,但那時候,甘陽翻譯的卡西爾的《人論》已經出版。對于甘陽年紀的人來說,能在當時出書已經非常不容易,更何況是一本一年內就印了24萬本的暢銷書,幾乎是當時哲學書里印量最大的——這使他在圈中早已小有名氣。
甘陽應了下來,構想著雜志將以西方哲學、文化為中心,并打算命名為“中國與世界”,一個一眼就能看出主編心氣有多高的名字。李澤厚建議加上“文化”二字,就成了后來的“文化:中國與世界”。而這時候甘陽發現,他和那些找他當主編的人構想完全不同。于是,最初的班底還沒有正式啟用,就被他給解散了。接下來,他拉了一幫自己的兄弟,形成了編委會,成員基本都是在北大讀書期間的同學和朋友以及工作后的同事,北大外哲所的陳嘉映、王慶節、王煒,哲學系的劉小楓、陳來,社科院哲學所現代外國哲學室的蘇國勛、趙越勝、徐友漁、周國平……甘陽在北大和社科院之間拉起了一張網,而這張網使得編委會成立以后最明顯的特點是,現代外國哲學方面極為突出。
在這張網絡之下,大家幾乎都有共同的讀書背景,因而形成了一個思考和討論問題的核心域界。1986年,劉小楓出版了《詩化哲學》,這本在其碩士論文基礎上擴充成書的作品,雖然當時并沒有劃歸在編委會的叢書里,但卻極具代表性地勾勒出了這一點。“(這本書)某種意義上包含了好多人共同的關切,比如說他最后一章談馬爾庫塞,這是趙越勝專門研究的。他在里面談的卡西爾部分和我有關系,談馬丁·布伯和陳維剛有關系。他那個書里面有一個mood,海德格爾是中心。”甘陽曾在2005年與查建英的訪談里說,“從北大外哲所開始到編委會,實際上我現在想起來,可以稱作‘對現代性的詩意批判,基本上是一個非常詩歌性的東西。小楓這本書是比較可以反映很多人討論問題的這個域。”
海德格爾是中心,當時整個編委會都在讀他,他吊起了他們的全部精力。“沒有一個人能像海德格爾那樣吸引我們,薩特沒有地位,尼采就是低的!”那時候他們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牽絆,北大外哲所里有大量的外文書可以閱讀。成天在持續的爭論中,是一個高度密集的輿論場,什么戀愛一類的話題,根本就是沒有必要的低級談資。海德格爾給當時國內哲學界帶來的沖擊是難以想象的,他的思想所達到的深度和籠罩的廣度,“顛覆所有以前科班出身的學西方哲學的人所學到的東西”。“我的一個直接感覺是,他和西方的東西完全不一樣,他是另外一個西方。”因為哲學,他們視自己站在文化的頂峰,因為海德格爾,他們意識到自己正站在哲學的最高峰。
為什么大家都那么愛海德格爾?這個并不容易簡單地解釋。海德格爾與中國的相關性,在今天也依然是學者有興趣去論述的話題。就80年代而言,甘陽提到文化人的文化虛榮。“因為難,所以要讀。”“一年之內完全不知道他在講什么!”另外可以歸結在直覺,是知性的吸引,直覺地一把抓住了他。而直覺依賴的又是什么?換言之,甘陽談到所謂討論問題的“域”,具體從何構建而來?他說,比如他們在下鄉時都讀過《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翻譯的席勒的《審美教育書簡》。從席勒到馬爾庫塞都在批判資本主義,從海德格爾一直到德里達,都在這一條線上——他們所讀的西學實際上都是批判西方現代性,批判西方工業文明的。他們最為關心的,最感興趣的問題也在于此。
如果還要問為什么?或要向前追溯到他們在“文革”中及大學以前讀的書,普希金、拜倫……那時候大家都是文學青年,所向往和追求的是一個詩意的世界。或再向前,追溯到先天性的、內在的文人氣質,決定了一個人或一群人所喜歡的東西并非偶然。
“它的文化意義大于它的學術意義”
編委會還在醞釀時,參與其中的陳嘉映、王慶節已經翻譯了《存在與時間》,杜小真和陳宣良也翻譯了《存在與虛無》,但出版都不太順利。正是因為這種不順利,讓最初只打算做一個雜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有了自己搞叢書的想法。這想法恰好與在1986年正式恢復獨立建制的三聯書店一拍即合,叢書就此確定了出版陣地。
以系列劃分,編委會所做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和“《文化:中國與世界》集刊”都由三聯書店出版。前兩者以譯介為主,編委會制定了龐大的翻譯規劃,并將具體的書目落實到具體的人,制定好交稿日期。這是一個龐大的工作量。
從1986年的《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到陸陸續續出版的《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小說的興起》《在約伯的天平上》……編委會組織出版了50余種現代西方經典著作。如果像今天這樣以數字論英雄,《悲劇的誕生》和《存在與時間》《存在與虛無》當時的印數都在10萬以上,且全部賣空,在今天也是不可思議的。至今,它們依然是中國學界的必讀書目。
“這些好像很深的西方著作,不只是給那些‘外字頭專業,世界歷史或者西方哲學領域的學者、博士生看的,而是通過他們,給整個學術界、知識界來看,提升整體的學術水平和文化素質,這是非常重要的。它的文化意義要大于它的學術意義。”陳來說,“西方思想學術的引進,是全面徹底地提升中國學術水平和質量的根本性的基礎。從70年代來講,我們的學術研究之所以與世界有差距,就是因為長期的封閉,在研究方法、視野方面都是封閉性的,不了解這些東西。”
他以自己研究中國文化為例,所作著述中一部分以中國研究中國,比如涉及文史考證的研究,但另一部分,就要通過對西方的研究回看中國了。1991年,他的著作《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出版,將中國對王陽明哲學的研究從當時落后于世界水平,提升到了引領世界的前沿位置。“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除了對王陽明哲學內在的了解以外,那時候我把所有翻譯的這些西方著作,重要的這些典籍,在寫書的過程當中都全部吸收了。沒有這么多的西方哲學的吸收,沒有這套書,不可能使我的書寫達到那個水平。”傅偉勛當時對《有無之境》的評價,即80年代文化熱的一個結晶。陳來說:“我參與的不多,但是我受惠不少。”1986年底到1988年夏天,他身在美國,沒有更多地進入編委會最初的活躍階段。當時密切參與這些編譯工作的編委會成員們幾乎達成共識,他們最初得到的回報則是:“我們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不管在什么時候,這都是能讓人極為羨慕的。
對譯著的規劃和遴選本身就是一種表達。這項工作一直延續至編委會星散,延續至今。90年代以后,甘陽與劉小楓共同或單獨主編了“經典與解釋”“西學源流”“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等多套人文學術叢書,提出了重新認識中國、西方、古典,以及重新認識現代的方向。“因為我們以往形成的對西方的看法,以及根據這種對西方的看法而又反過來形成的對中國的看法,有許多有必要加以重新檢討。”
劉小楓說,80年代時,中國對于西方的認識僅僅是一個開始,當時所做的叢書僅限于西方現代,要認識完整的西方,必須將古典的東西也拿出來,而他如今所做的工作正是在填補這個巨大的空白。“慢慢地會在教育上起到一些作用。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本科生、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到中學或者其他教學教書,他們會在上課的時候談到這些書,這樣慢慢就會看到教育和以前不一樣。就是為中國的學者積累一些最基本的學術的東西。”
近十幾年來,甘陽在國內的高校推進通識教育,想要讓大學擺脫現有的學科建制,而恢復其本應有的樣貌,通過中西經典的育授,傳遞出更純粹的人文精神,實際上,正是與繼續編纂叢書的目的一樣,甚至是以更為直接的方式在延續他們于80年代的工作和理想。
編委會另外兩個叢書系列:一是“集刊”,是編委會成員的重要思想陣地,由“中國文化研究”“西方文化研究”“比較文化研究”“文化學基本理論”這幾個專題為討論對象,發表各年齡層學者們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有大量的讀者,因此也是首印時就擁有3萬冊之多的驚人數字。在今天,這同樣是難以想象的。雖然前后只發刊五期,但它于當時的影響巨大。此外,編委會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研究叢書”,主要收錄青年學者們原創的著作,蘇國勛、劉小楓、陳平原、夏曉虹、汪暉、杜小真、錢理群、趙園、梁治平等人最初的重要著作都在其中。
“80年代的問題在我心里從來都沒有放掉過”
以當時“文化熱”的程度可以想見,“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在當時積極發聲的學術團體。同時有一定規模的,還有以金觀濤為核心人物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以及“中國文化書院”。前者是通過編譯的形式,向大學生介紹當代西方社會科學方法、理論及思潮,重點放在了提倡科學精神;后者以弘揚固有的文化傳統為宗旨,進行一些文化活動。
三個學術團體的面向和路徑各不相同。陳來曾在1987年撰文《思想出路三動向》刊發在臺灣的《當代》雜志上,將它們各自思想上的取向、成果及所達到的影響力進行了清楚的剖析和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文化:中國與世界”的影響可能會占比較主要的地位。他同時指出:“從目前來看,‘文化:中國與世界的文化取向較偏于西方文化,而且帶有某種反傳統的色彩。”這是在極力追求客觀的評價,甚至在語調上保持平實。相比之下,在甘陽當年一度提出“繼承發揚傳統的最強勁手段恰恰就是反傳統”的說法之后,編委會被廣泛賦予的標簽是“全盤西化”。陳來在文中表示出一種理解:“國家的強盛是知識分子的首要關切,強烈否定民族文化傳統正是基于急迫要求復興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這種心理幾乎支配著‘五四到今天的每一代青年知識分子。”他指出“青年知識分子迫切要求現代化導致了反傳統情緒”,并且預言“隨著文化體驗的加深”,“反傳統意向可能會逐步減弱,走向較為圓熟的境地”。
1988年,甘陽在為《中國當代文化意識》寫下的“初版前言”中對于有關傳統問題上的思想和矛盾做出了表白:“盡管‘反傳統確實是當時青年一代的基本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主張把傳統文化統統扔光,更不意味著我們這代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就沒有任何感情瓜葛。相反,我們實際上在當時就相當清醒地意識到,‘倫理本位的文化(傳統文化)必然是更富人情味的,知識本位的文化(現代文化)則必須削弱人情味……也因此,現代人幾乎必然懷有一種若有所失的失落感。換言之,我們對于傳統文化,不但有否定的、批判的一面,同時也有肯定的、留戀的一面,同樣,對于‘現代社會,我們不僅有向往、渴求的一面,同時也有一種深深的疑慮和不安之感。”
甘陽將陳來的《思想出路三動向》一文收錄在這本用以對“文化熱”或說“文化反思”進行階段性總結的全書末尾,使其承擔起最終的概括和平衡全書觀點的角色。而甘陽將那段時期定性為:“不成熟的過渡性時代下面所流動著的一般‘意識及其所蘊涵著的可能趨向。”
編委會的取向或情緒的整個過程的終結點,是1994年的“人文精神討論”。而作為一個自發組織的學術團體,實則在進入90年代,在已經改變的社會氣質下,編委會早就逐漸分化為一個個的小圈子,直至星散。但是,他們所提的問題,依然在繼續。
2000年,當甘陽再次對80年代的文化熱進行回顧時,他在《十年來的中國知識場域》中寫道:“文化討論的中心問題是所謂中西文化問題……中西文化問題的思考和討論乃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積習,它由近世西學東漸以來就必然出現,而且在今后仍將長期糾纏中國知識分子。”
2005年,他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題目是《三種傳統的融合與中華文明的復興》,后被歸結為“通三統”。其中提到,21世紀最大的問題是要重新去認識中國,重新認識整個傳統中國的歷史文明對現代中國的奠基性,“要檢討我們以前對自己對中國的看法”,因為中國漫長的獨特文明傳統對于中國的現代發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顯然,這是他對80年代文化討論的核心問題再度的重新審視。
“80年代的問題在我心里從來都沒有放掉過。”甘陽認為,“回顧80年代,不是要懷舊,而是要通過80年代重新回到晚清以來的基本問題意識,這就是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古典文明與現代文明的關系問題。”換句話說,“古今中西之爭”在今天依然是文化討論的核心問題。“中國人必須拉長歷史視野,反復思考這個大問題,因為這仍然是我們的基本生存論境遇。”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
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 知識界內頻繁的討論與對話形成高度密集的輿論場 。圖為哲學家周國平(左二)和陳嘉映(右一)在北京(攝于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