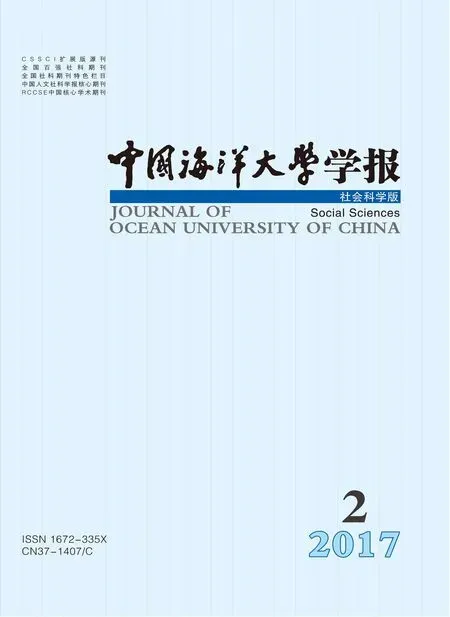更路簿的歷史性研究
——基于歷史學的研究視角
劉國良 趙 贇 曾超蓮
(1.海南大學 法學院,海南 海口 570228;2.德國波恩大學 法學院,德國 波恩 D53012)
更路簿的歷史性研究
——基于歷史學的研究視角
劉國良 趙 贇1曾超蓮
(1.海南大學 法學院,海南 海口 570228;2.德國波恩大學 法學院,德國 波恩 D53012)
近幾年更路薄研究一直方興未艾,然而在其研究方法上與其研究思路上一直存在著爭議。客觀上講,更路簿的研究必然是建立在歷史本體論的基礎之上,其目的是研究更路簿本身所擁有的歷史性價值。因此,這種歷史性價值的研究目標決定了研究者首先在更路簿的分類上必然區分出兩種脈絡,即漁人更路簿和文人更路簿。因為兩者所承載的歷史性價值不同,前者所承載的是漁人的耕海歷史性經驗;而后者所承載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國家疆域意識與海洋領土的祖宗所有權意識。其次是更路簿的研究方式必然要求對更路簿本身進行一種歷史性解釋。第三,對圍繞著更路簿所形成的文獻資料堅持以歷史文獻價值論。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決定了我們對今天所留存的更路簿所形成的態度,即更路薄是一種歷史性文化與生產生活的記錄。而這種歷史性文化、生產、生活恰好被本文理解為耕海性文化、耕海性生產與生活。通過對更路薄的歷史性解讀,我們完全有理由得出:中華民族的耕海文明程度遠遠高于西方地中海文明,中國對海洋的意識完全是建立在海洋疆土意識之上的,而與西方地中海的路橋通道意識截然相反的。
漁人更路薄;文人更路簿;歷史性研究;祖宗所有權意識
梁啟超先生在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當中首先論述了何謂史的問題,在他看來,史首先建立在記述人類社會整體變遷的本體與其所表現的現象,這種本體與現象被梁啟超先生稱之為體相,而記述的對象不僅僅局限于本族本民族的社會變遷,而更應該包含其他民族及人類整體的社會變遷。這種強調本身一方面注定了梁啟超先生所關注不是僅僅中國自己的社會變遷,而關注人類整體的社會變遷,顯然其關注的視野宏大,即人類整體視野;另一方面注定了其所記述的對象具有多元性,而這種多元性記述的存在注定了后續的方法論問題,即必須透過多元社會變遷的比較而發現其中的共性與個性,并梳理出未來發展的規律性軌跡。其次是探求社會變遷的體相的發生的原因,這些原因包含著內因和外因,有直接原因有間接原因,有正向的直接關系,有負向的直接原因,而所有這些梁啟超稱之為為因果關系。第三是對史的關注目的,必須具備能夠為現代的普通人的活動可資借鑒,[1](P900)即梁啟超所說的資鑒,此乃史的機能主義。正如梁啟超所言:“史者何?記述人類社會賡續活動之體相,校其總成績,求得其因果關系,以為現代一般人活動之資鑒者也。”[2](P1)
從文化的視角看,文化本身的屬性就是歷史性,因此,對于文化的研究必須建立在歷史性研究基礎之上的。同樣,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發現到的漁人更路簿一樣要從歷史性文化的角度去探尋其內在的規律和產生的真正原因。因為在探究更路簿的目的不是為了僅僅說明、描述漁人的如何出海捕魚的起源、演變和發展,這些僅僅是對更路簿進行歷史性研究的一種預演或者是一種預備階段,即更路簿的歷史性說明或描述階段,而真要進行歷史性研究必須在歷史性說明階段之后繼續對更路薄進行歷史性解釋。這種歷史性解釋不僅僅包含著對更路薄的產生進行剖析其真正原因;同時,更要解析出究竟是何種因素推動、影響更路簿的演變和發展。在這個階段才開始其解釋性研究,其終極目標是求得真正的原因、求得蘊含于更路薄之中的真正的價值;而這種真正價值就體現在經驗性價值與科學性價值。因此,對更路簿的歷史性研究的方法體現在:
首先,如何完成更路薄的歷史研究?在這個問題上,研究者本人必須清楚的是,研究者本人究竟應該嘗試著做些什么?研究者本人要確定所從事的這項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研究者選擇歷史分析的方法其目標是什么?這個問題從哲學的角度講,是指這項整體性智識活動的本體論或是研究者的范疇論,所以可以將這個問題稱之為更路薄研究的歷史本體論。
其次,研究者透過對更路薄所從事的整體性智識性活動將產生的意義是什么?在這個問題上,所要關注的是這一系列的整體性智識活動對于更路薄的經驗性價值和科學性價值的發掘上所具有的意義。這個問題從價值性的角度講,就是該項研究是否具有實踐性價值,即更路薄研究的歷史價值論。
第三,是對更路薄所進行的歷史性解釋這個問題上,所關注的是對歷史性解釋(historical explanation)方法從概念角度予以界定,故這個問題又可以稱之為研究方法的概念論。[3]這種概念論對于研究者本人來將具有重要的價值,它就像大海航道中的燈塔,指引研究者的所有整體性智識活動繼續前進的方向,即更路薄研究的歷史性解釋。
第四是對更路薄的文獻資料所進行的哲學性思考問題,這個問題既涉及到更路薄的歷史性文獻資料,也涉及到現實性的漁人耕海捕魚資料。這里的哲學性思考問題所指向的是對更路薄的研究資料本身所蘊含的知識論、運用的概念和方法論等知識體系。由于更路薄文獻資料的不同必然產生不同的哲學問題,這種問題涉及到研究者本人所選用的知識論、運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如此,該問題所涉及的是更路薄文獻價值決定論問題,即更路薄研究的歷史文獻價值論。
綜上所述,更路薄的歷史性研究既涉及到研究者本人的思維上,又涉及到研究路徑和方法上,甚至最終由于更路薄的文獻資料價值的不同決定了研究者所選取的知識論、運用概念和方法論的不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更路薄的歷史性研究,絕對不是僅僅停留在對漁人耕海性生產生活所完成的歷史性記述和描述;相反,它融合了研究本體論、研究實踐論、研究概念論和文獻價值論于一身的綜合性、多維度、系統性的智識性活動。同時從歷史性研究的產生和發展的角度講,歷史性研究本身又具有一定的歷史變遷性和歷史融合性特征。
一、更路薄研究的歷史本體論
在更路薄研究過程中,我們所要關心的不僅僅是歷史性航海本身,而更要關心的是整個民族的行動(action),即我們所言的我國漁人在千百年的歷史進程當中所從事的耕海性生產性活動。這種耕海性生產活動本身是那種基于自由的、且理性的漁人透過這種耕海性活動來表達其內在的想法和意志(will),即在他們的祖宗海當中從事著海洋性領土的耕種。在這種海洋領土的耕種當中,既蘊含著我們中華民族對這片海洋所表現出來的祖宗觀念,同時也蘊含著中華民族對這塊海洋性領土所擁有的海洋領土所有權意識。因此,我們對于更路簿的研究的最終的目標,就是通過我們對更路薄本身所蘊含的祖宗海觀念與海洋領土所有權意識相結合提煉出我中華民族海洋的祖宗所有權意識,期望以此來帶動對整體中華民族的海洋文明、文化的發生或者發展研究。在海洋文明、文化的研究中,我們不僅需要知道過去發生什么事情和發現為什么會發生這樣事情在其本質上是一樣的。諸如《詩經·商頌玄鳥》中記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4](P380)《周禮·夏官司馬第四大司馬》記載著:“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5](P650)這些文人通過這些詩、書、史的方式,以輯錄的手法來彰顯國家疆域意識的產生與國家疆域的范圍,輯錄著國家海洋文明的誕生、傳承和發展。顯然,這種文人更路薄的輯錄手法與漁人的更路薄在其表現手法上是不同的。
我們研究者對這些輯錄的追問的目的顯然是停留在我中華民族的先祖們對其所提出主張的動機上,我們的華夏祖先所要表達的顯然是一種海疆意識。對于我們今天的研究者而言,我們華夏先祖們所提出這種主張顯然是代表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心中所想所盼,是一種內在的意圖或內在的意志,海疆意識的主張根據我們中華民族的內在意圖或者內在意志所產生的能動性(agency)而發生,所以這種不是發生于外在的漁人耕海性活動的其他事物,相反它是完全蘊含在漁人耕海性活動本身的內部事實;恰恰是這種事實才構成了我們中華民族海疆意識產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研究者對更路薄研究的核心點不僅停留在文人更路薄對海疆意識的產生和發展所著的輯錄;同時,我們還要借助于我們研究者透過文字對漁人的耕海性生產生活進行文理解釋使得這種內在的推動事實-海疆意識,能夠予以外顯;后者僅僅是需要透過文字或者繪畫圖像及其他相關物資將該事件的發生予以描述予以說明,并告知人們在哪里什么時間真正的發生了什么事情。顯然,前者是透過一種內在事實的解釋最終讓人們理解;而后者僅僅是透過一種描述、一種說明而完成向人們告知。但是,不管是說明還是解釋都是基于兩個事實即內在的原因事實和外在的發生事實,而沒有運用其他規則進行評價和論證。顯然這一點非常明確地區分出歷史性解釋、歷史性說明與科學的本質區別。
二、更路薄研究的歷史價值論
(一)祖宗海的祖宗觀念性價值
客觀意義上講,從更路簿所記錄、輯錄出的內容非常直觀的說明了我國漁民在征服南海和控制南海所表現出的智慧和能力。也正是從這種能力和智慧的角度上說,我國的海洋文明是一種農耕耕海文明,這種文明與西方地中海的路橋通道文明在文明程度上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因為我們的農耕耕海文明是指代漁民在海洋中的各個島礁礁盤下面發掘魚類資源、并在島礁礁盤之下從事養殖這些活動的一種農耕文明。而西方地中海海洋文明僅僅將海洋作為一種陸橋通道,[6]在海洋中僅僅從事的捕魚和撿拾采集貝類琥珀,并沒有從事養殖工作。在其海中金槍魚、鰻魚、鯨魚的捕獲僅僅是作為陸地資源減少的一種補充,并不成為與土地種植并行的海洋種植。
因此,早期海洋成其為資源則體現在海洋能夠為鏈接各個陸地提供一種便捷的水上交通,這種交通在人類早期相對于陸路交通而言是便利、便捷和快速;另外一個在于海洋養育著眾多的魚、蝦、貝類等,這類資源能夠彌補陸地資源不足或者減少的損失。而對于這類資源的開發,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個條件是智力型條件;一個條件是工具性條件。前者體現在海洋意識、海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以及整體掌控海洋能力;而后者體現在造船和駕船。在海洋掌控能力上,既表現在海洋航路的開發與利用,又有海洋航行危險危機的預防和控制。在今天我們說南海是我們的祖宗海,那一定是告訴世人,我們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已經完全掌控了整個南海,并且我們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對南海的資源進行開發利用了。我們今天的中國漁民往返于南海,尤其是南沙群島的目的不是為了捕魚,不是為了掠奪,而是為了回家,回到祖宗之地、祖宗之海。那里是中國漁民的祖先居住地,那里的水包容著我們的祖先,那里的魚尤其是大魚可能是我們祖先的化身,因此中國南海漁民一直保留著自己的祖訓,即到南海的南沙群島不能吃那里的魚,實在迫不得已的情況只能吃小魚,否則將受到祖宗的懲罰,要么是生病,要么是被巨浪吞噬。南海漁民祭祖的時間是不同于內地的清明,而是選擇在每年的冬至,屆時中國海南漁民尤其是以瓊海潭門、文昌漁民為主的漁民會出海,其目的不是為了捕魚,而是為了能夠到南海西沙群島南沙群島海域祭拜自己的先祖們,緬懷他們為開辟南海航路所作出的巨大奉獻,為維護南海的和平與安寧以及南海航路安全所做的歷史功績。因此從這個角度講,南海航路的產生,南海航路的安全和維護是建立在海南歷代漁民所做的奉獻基礎上,這種奉獻既有海南漁民先祖所做的歷史奉獻,也有現代漁民所做的奉獻。
(二)耕海性生產生活的歷史經驗性價值
更路薄作為航路開辟的歷史性載體,這種載體根據其經驗的不同來源又名《定羅經針位》、《西南沙更簿》、《順風得利》、《注明東、北海更路簿》、《去西、南沙的水路簿》等,是海南漁民祖祖輩輩傳抄的小冊子,被譽為“中國南海航路開辟與航行寶典”。更路簿是千百年來中國先祖為開辟南海航路和維護南海航路而自發形成的,由中國海南漁民自編自用的南海航路開發、維護與航海針經,也是中華民族耕海智慧的集成者,不僅為我中華民族開辟了新的生存空間和道路,也為世界人民的國際文化貿易交往奠定了堅實基礎。而這些均體現在更路簿的歷史傳承。在傅寅所著的《禹貢說斷》中描述了在上古三皇五帝時期,我們華夏先祖就已經開始對海島就已經明確界定了,諸如在《禹貢說斷》卷一記載:“島夷卉服,孔氏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唐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服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為之冀州云島夷皮服。”同樣還記載:“島夷皮服,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算術所云海島絕邈不可踐量是也。”[7](P180)同樣,在漢朝孔安國所著的傳經唐朝的孔穎達注疏的《尚書正義》卷六禹貢第一篇中記載:“島夷皮服,海曲謂之島,島是海中之山,傳云“海曲謂之島”,謂其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島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8](P630)
(三)更路簿的科學性價值
不管是漁人更路簿,還是文人更路簿其基本的功能就是傳承中華海洋文化。這種文化不同于其他海洋海盜文化的根本之處就在于它是農耕文明的一種。
首先,通過文人更路簿和漁人更路簿,都可以證明我國商朝在夏朝的朦朧國家疆域意識的基礎上,發展出王畿陸地疆土和四海兆域海洋疆土意識。并開始了對國家疆域進行細化,嘗試著確定國家疆域的界限。在周朝之后,整個華夏大地上形成了華夷一體化的王畿陸地疆域觀念,這種觀念為中華多民族國家疆域的劃分確定了陸地基礎。隨著王畿陸地疆域的確定后,西周同時也在開始拓展海洋疆土,即在繼承夏朝和商朝的四海兆域海洋疆土意識的基礎上,明確了四海兆域的海洋疆域的界限。從此,華夏海洋疆土在南部區域拓展至南海。這種富有四海的國家疆域意識,很顯然是很明確的告知我們這種國家疆域包含著陸地疆土和海洋疆土。
其次,我國自從夏朝后荒即位以后,開始從事耕海性生產生活。諸如在《古本竹書紀年》的夏紀中記載:“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賓于河,命九東狩于海,獲大鳥。”《北堂書鈔》卷八九禮儀部《紀年》曰:“后荒即位,元年,以玄璧賓于河,狩于海,獲大魚。”《初學記》卷一三禮部上《紀年》曰:“后芒即位,元年,以玄圭賓于河,東狩于海,獲大魚。后芒陟位,五十八年。”[9](P10)而這種耕海性生產、生活一直持續不間斷地延續到今天。
第三,我國漁民自從商代以來,就已經開始逐步探索、利用天文定向、地文定位、季風和潮汐導航等技術。而恰恰是這些技術的應用證明了我國漁民有能力、有智慧的占有海洋,并且在幾千年來一直占有和控制著整個海洋。并且在其占有和控制的過程中,也為南海、東海航行確立了技術法則,這些法則就是我們漁民一直遵守并有效執行的更時歷法和針經更路的航程定位法,這兩部法在過去的整個歷史當中一直成為國際公認的法則。
三、更路薄研究的歷史性解釋
歷史學家認為:自然的進程可以被適當地描述成為某種事件的時間性排序,顯然這是歷史性描述或說明的根本所在;但是歷史解釋卻不盡然,歷史解釋不僅僅關涉到事件的時間進程,更重要的是要關注行為的進程。這種行為進程不僅包含著外在舉止的,更包含著推動舉止的內在思想過程(process of thought)的組成,這種思想過程恰好是構成了歷史性解釋的核心要素,因為他們要從這個過程當中尋找出原因。[10](P215)因此,此時我們研究者通過對更路薄的耕海性生產生活的解讀,其根本是透過在自己內心之中對這種思想過程進行重新思考來發現自己的心得體驗。諸如,更路簿的本質屬性,海洋生存經驗之法的具體體現。蒼茫的天空、閃亮的日月星辰、來去不可捉摸的風雨雷電,這一切似乎就在每一位泛舟于大海的人們身邊,卻又離人們那么遠,充盈著無限的神秘。在神秘之中又蘊含著無數個自然之法。人類要想穿透這無限的神秘,認識到其中的法之內涵,只有從長期的生存實踐觀測起步,才能有望取得突破。中國古代先民們,在天象的觀測與記錄上表現出超群出眾的才能與毅力。而在海洋之中對于天象的觀測與留存上則體現出更大的智慧。由于海洋生活于風雨飄搖之中,不可能像陸地上靜靜的觀測并以文字將其所觀測到的現象予以表述記錄,此時他們只能講其留存于腦海的記憶當中。每一種記憶都是深刻的,因為每一個記憶都蘊含著血淚。因此,更路簿的產生不僅僅是一種記憶,一種命名,更是一種經驗積累。這些積累使之成為擁有一系列世界之最的天象記錄——最早、最豐富、最為連續、最具準確性,成為世界天文歷法史上獨一無二的珍貴寶庫。同時這種經驗之法的歷法者不是伏羲之王法,而是廣大海洋漁民將伏羲式所“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的王法與地理、海洋以至勞動人民的海洋生存經驗都納入到海洋實際的生存經驗之中。[11](P1100)并且這種經驗之法在海洋實際生存之中得到不斷的完善的生活之法。所以說更路簿的功能不僅僅是表時間,更重要的功能是規范漁民在茫茫大海之中如何生存、如何應用,而時間的表述只是海洋生存必備的一個工具。
顯然,我們研究者最期望嘗試著尋找出漁人耕海活動內心的真實思想過程或真實的想法或者是什么真實的原因推動他們決定這樣做。顯然,這就要求我們研究者要設身處地的情況來推動自己的思考。研究者對這個思想過程的重新思考的過程稱之為思想的歷史,所有的在思考者思考之前發生的事情都可以稱之為事件,而對事件的思考都可以稱之為歷史,即都是歷史學家們在心中對過去思想過程的重新思考,或者是是一種思考的重新再現。
四、更路薄研究的歷史文獻價值論
在現實的國際學術界存在一種理論,認為作為主權主張的關鍵性證據是以正式出版的國家地圖為主要證據;[12](P27)而在地圖的制作上普遍認為中國的地圖制作晚于西方,甚至認為中國是典型的重陸輕海的國家。一方面這些觀點建立在對我國的文化歷史不理解的基礎而成的,另外一方面是一種國際學術霸權對中國海洋文化的一種蔑視。在這些問題的核心在于東西方海洋文化在其理念層面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而這種差異性的直接體現就是我國一直以來存在著地理志與西方的地圖直接的差異。[13](P141)中華民族對于海洋的記錄都是通過國家地理志來實現的;在其實現的技術層面上看,國家地理志是由國家具有專業文學素養的文人通過語言文字的方式將海的地理位置、水文等客觀狀況進行簡潔明了的方式進行語言性描述。從地理志描述性質而言,國家地理志的語言描述是國家性質的,是歷史性傳統的,是一種經驗性、理性的方式。從地理志描述的目的而言,其同語言描述的方式一方面是為了將先前所產生的理念、意識和觀念予以闡述并向世人告知,并期望傳承于后世之人;另外一方面是將先前所積攢的經驗性、理性的生產、生活方式予以文字性表述,以便于流傳。通過對地理志的解讀將會對讀者在其認識上獲取足夠的歷史性經驗,同時文字的描述更使后人能夠進行理性思考和追思仙人的偉大理念和功績,并成為后世人的楷模,由此產生了以史為鑒的思考模式。最后,這種國家地理志對于海外之萬邦所產生的效果體現在,強化中國國家疆域的文化自信心,同時也對起到了,教化萬邦,其他邦國透過學習我的文字文化也就認同接受中國的國家經驗、接受中國國家農耕文明,接受中國的國家疆域主張,遵守中國國家海洋疆土規則。因此,我國的國家地理志中的海洋絕對不是簡單的一種標示,相反它更是中國國家為海洋制定的規則。顯然,上述問題產生根源在于我們對歷史文獻的價值認識上產生的分歧。這種分歧必然要求我們今天的學者在研究更路簿問題上,一定要堅持更路簿文獻資料的歷史文獻價值論。
結語
任何對更路薄所做的解釋,其終極目標都是在當下對過去的、歷史性的、已經發生的、并且也在一直持續性發生的活動首先經由描述或說明,進而通過對其內在的核心內涵進行重新思考而形成的思想,最終將所形成的思想帶入到現實生活當下,期望以推己及人、設身處地的詮釋出一種真實的原因解釋。并最終將這種連接著過去和現在的處境與兩個不同思考這的思考完全呈現給他人進行比較以期望最終達到他人的理解。因此,在歷史學家看來,過去的事情事件只不過是某個人在過去的某段時間里所做的思考過程,而今天多這個人的思考過程進行重新思考、重新展現的活動就是歷史。歷史學家們可以自己重新思考的所有想法,都是為了使他能給在過去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能夠認識其整體的全貌。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除了思想活動以外的所有事物都不能稱之為歷史。人類理性是歷史學家唯一感興趣的要素。在這些歷史學家看來,孟德斯鳩在解讀國家與文化的差異問題上,顯然是對國家和文化的本質性特征沒有達到真正的認識。盡管孟德斯鳩認為氣候與地理是造成國家和文化差異的一種原因。顯然這種理解完全沒有參照人類理性的思考路徑去思考、去解釋歷史。顯然,這種思考歷史的方式其本質是完全是一種自然歷史或者人類學。在這種研究當中,其關注的是自然因素,而非關注的制度(institution)因素,[10](P78-79;218)其最終的結論往往是人類理性作用的產生和發展完完全全是基于自然因素而產生的,即基于氣候因素、地理環境因素而在自然的選擇和淘汰當中產生和發展。同樣,在自然歷史學或人類學學家看來,任何一種文化與它所處的自然環境有著直接的密切聯系。[14]人類學或者自然歷史學觀點在文化的發展同自然地理環境存在著關聯性,但卻不是完完全全地決定關系,相反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的本質特征并非由環境因素所決定的。這種文化特征來源于人類主動的從環境獲得的某種或某些啟發;同樣人的發展也不是完全的被動的受環境或者文化的影響,而是主動從環境或者文化當中獲取某種啟發。正是由于人類與環境,人與環境或文化之間的主動或者被動關系決定了他將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即純粹的自然人還是歷史性人。顯然,兩類研究方法的差異就在與強調根源性(Emphasis in original)的不同。[15]
[1] 令狐德棻.周書·列傳蕭詧[M].北京:中華書局,1971(2014.8重印).猶借鑒,可資借鑒。“藉聽眾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明。周書卷四十八,列傳第四十,第900頁。
[2]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2.
[3] Hempel,C.: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Journal of Philosophy,1942,(39):35-48.
[4] 王秀梅.詩經[M].北京:中華書局,2015.
[5] 徐正英,常佩雨.周禮[M].北京:中華書局,2014.
[6] (英)簡·麥金托什.探尋史前歐洲文明[M].劉衍鋼、張元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7] 傅寅.禹貢說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8] (漢)孔安國、(唐)孔穎達.尚書正義[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 方詩銘,王修齡校注.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 Collingwood,R.G.:The idea of Histor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
[11] (后晉)沈昫:后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2] 譚廣濂.從圓方到經緯: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M].香港:中華書局,2010.
[13] 譚廣濂.淺談中國古代宇宙觀與地圖繪圖史[C].從圓方到經緯: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藏珍[Z].香港:中華書局,2010.
[14] White M.: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 March 23, 1967:29.
[15] Dray W.:Law and Explanation i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責任編輯:鞠德峰
A Historical Research ofGenglubuBased on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u Guoliang1Zhao Yun1Zeng Chaolian2
(1. School of Law, Hainan University, Heikou 570228, China; 2. School of Law, Bonn University, Bonn D53012, Germany)
In recent years, the research ofGenglubuhas been developing more and more prosperous, but there has been controversy in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ideas. Objectively speaking, the research ofGenglubu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ntology, and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study its historical valu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target determines that researchers must first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Genglubu: fishermen'sGenglubuand scholars'Genglubu.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wo kinds ofGenglubuis distinct; the former record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fisherman in cultivating the sea, and the latter the territor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hol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ancestor ownership consciousness of the marine territory. Secondly, the research methods require that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be made ofGenglubuitself. Thirdly,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literature derived fromGenglubuwith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value. Our attitude towards today's survivingGenglubuis determined by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i.e.Genglubuis the record of historical 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is just regarded as the cul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of cultivating the sea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Genglubu, we have every reason to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ese nation's cultivating sea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and contrary to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road and bridge in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China's awareness of the oceans is entirely based on the awareness of the maritime territories.
fishermen'sGenglubu; scholar'sGenglubu; historical study; the ancestor ownership consciousness
2016-12-02
中國法學會規劃研究課題“南海海洋劃界中的歷史性證據體系研究”(CLS2015C64)階段性成果
劉國良(1973- ),男,遼寧鳳城人,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2011計劃司法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南方基地研究員,博士,主要從事法律哲學、犯罪學、法律史學研究.
D509
A
1672-335X(2017)02-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