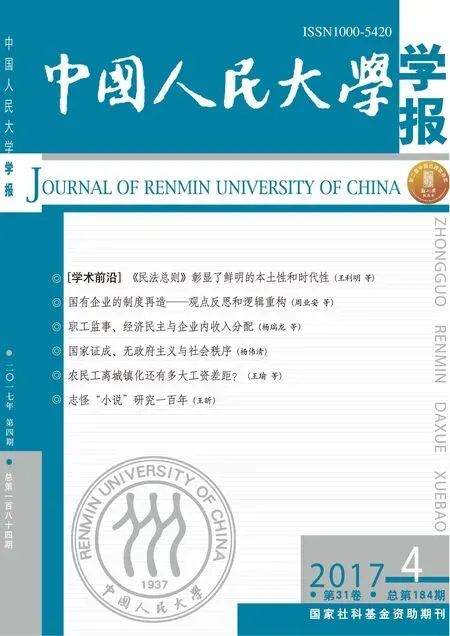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趨勢分析
孟 鑫
西方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趨勢分析
孟 鑫
新社會運動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已經(jīng)成為一種塑造西方社會的重要力量,走向制度化是其發(fā)展趨勢之一。社會運動制度化實質(zhì)上是國家的體制構建目標和社會運動的訴求目標互動博弈的產(chǎn)物。這一過程既改造了社會運動,也對國家體制和社會危機管理機制產(chǎn)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從近半個世紀的發(fā)展歷程來看,制度化趨勢并沒有改變西方新社會運動的抗議屬性和變革目標,它仍然是西方發(fā)達國家中最具有社會主義特征的變革力量。
新社會運動;國家體制;制度化;趨勢
20世紀中后期,西方發(fā)達國家中社會公眾的政治革命意識逐漸消退,以社會改造為目標的新社會運動漸次興起。這種不同于傳統(tǒng)工人運動的新社會運動“主要是指西方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fā)生的學生運動、女權運動、生態(tài)運動、宗教運動、反核和平運動、動物保護運動、同性戀維權運動、少數(shù)族裔的民權運動等”[1](P3)。從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到2011年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均屬于此范疇。其共同特征是社會群體自下而上、通過非制度化方式表達不滿和抗議,力圖推動社會改革和社會變遷。事實上,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各種社會運動以及伴隨其后發(fā)生的社會變革此起彼伏,從未間斷。新社會運動貫穿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整個發(fā)展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一部當代西方社會發(fā)展史就是一部新社會運動史。
新社會運動與政治革命有相同的一面,它也是一種通過集體行動來促進社會變遷的行為方式;但與政治革命不同的是,新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目標是社會改造,其在激烈性和對抗性上遠低于政治革命。盡管如此,在發(fā)達國家政治革命逐漸消弭的背景下,新社會運動成為替代政治革命促進資本主義制度產(chǎn)生變遷進而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推動者。作為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具代表性的社會抗議形式,它已經(jīng)成為一種塑造西方社會的重要力量。新社會運動在當前也遭遇了發(fā)展困境,擺脫這種困境需要做出新的判斷和抉擇。按照目前的發(fā)展趨勢看,新社會運動可能會走向制度化、組織化、非暴力化和全球化等。
一、新社會運動制度化
新社會運動制度化需要兩個前提:一是運動主體雖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己力量,但其對現(xiàn)有制度仍有一定程度的認同;二是國家制度雖然對各種社會運動意在抵制,但在法律層面仍有一定程度的容納。究其本質(zhì),這一制度化趨勢是各種社會運動與政治體制博弈的結果。
(一)社會運動的制度化
學術界對“制度”的認識有一定差異。道格拉斯·C·諾斯認為:“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guī)則,或者更規(guī)范地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系的約束。從而,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經(jīng)濟領域里交換的激勵。”[2](P51)亨廷頓認為:“制度就是穩(wěn)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發(fā)生的行為模式。”[3](P3)“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wěn)定性的一種進程。”[4](P12)總體上看,學術界對“制度化”的認識是基本一致的:“是群體和組織的社會生活從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認可的固定化的模式轉化的過程,是整個社會生活規(guī)范化、有序化的變遷過程,它表示個人、組織行為符合社會規(guī)范的程度以及過程,表現(xiàn)為社會組織由非正式系統(tǒng)發(fā)展到正式系統(tǒng)、社會制度從不健全到健全的過程。”[5](P387)也就是說,“制度化”的內(nèi)涵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行為、組織或機制從不穩(wěn)定到相對穩(wěn)定、從非正式到正式的演變過程;二是行為、組織或機制的運行方式、存在方式被已有社會體制逐漸接納并認可的過程。就社會運動的制度化來說,一方面,對于社會運動參與者,這種接納和認可,將會使不確定的運動方式轉化為可預期的運動模式,進而降低了參與者為尋求新的參與渠道和表達方式而付出更多代價的風險,同時也降低了參與者運用制度外途徑進行社會運動的風險。另一方面,對于現(xiàn)有政治體制,這種制度化可以減緩社會運動沖擊,了解社會矛盾狀況,擴展社會階層基礎。總的看來,如果能夠實現(xiàn)社會運動的制度化,無論是對公民還是對政府而言都可以降低實現(xiàn)目標的代價和成本。
根據(jù)法國社會學家梅耶的分析,社會運動制度化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常規(guī)化。無論是運動參與者還是制度保護者都有各自熟悉的“劇本”(script)可為遵循,并且都能夠采用已經(jīng)熟練的行動模式,對自身選擇的潛在危險及其他可能有預期判斷。第二,包容及邊緣化。那些愿意遵守常規(guī)運動模式的抗議者將會獲得在制度體制內(nèi)進行交流的機會和路徑,反之則不然。第三,吸納。抗議者選擇通過維持常規(guī)政治系統(tǒng)的方式來實現(xiàn)其訴求。
社會運動的目標是否具有長期性,直接影響到它是否愿意走向制度化這一結果。那些不以制度更迭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往往是希望在短期內(nèi)對現(xiàn)有制度或體制產(chǎn)生預期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化就不僅僅是國家制度和體制結構對社會運動的規(guī)制與吸納,它也實現(xiàn)了運動參與主體對制度或體制產(chǎn)生預期影響的運動目標。而那些以制度深層改革甚至制度更迭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往往會遭遇現(xiàn)有政治體制的強力抵制,它們最初也會抵制制度化趨勢,但是,如果在可預見的時期內(nèi)無法實現(xiàn)長遠目標,為保存實力,延續(xù)影響,它們往往不得不接受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因為這是有利于長遠目標實現(xiàn)的戰(zhàn)略選擇。在生態(tài)運動、女權運動中都出現(xiàn)了這種為了長遠目標的實現(xiàn)而與國家體制合作的情況。
另外,社會運動能否出現(xiàn)制度化的結果還與某個國家的下列情況相關:一是國家政體的性質(zhì)。一個國家采用民主體制或中央集權的組織形式將會影響到這個國家應對社會運動的能力和方式。二是國家的階層結構以及種族、民族關系。這些因素會直接影響到社會運動制度化實踐路徑的具體走向和方式。三是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系。包括政治體制與公民互動的歷史、運動組織與政府之間的互動程度等。以上因素在不同側面和不同階段會對社會運動能否被制度化產(chǎn)生較強影響。
社會運動走向制度化經(jīng)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主要表現(xiàn)在:第一,19世紀中后期的工人運動根本不存在制度化的可能。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階級矛盾尖銳,這一時期的歐洲工人反抗運動猛烈而頻繁,運動目標明確而堅定,旨在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革命,推翻資產(chǎn)階級政權,這一階段的抗議行動大多數(shù)采取暴力手段,其自身也堅決抵制被制度化。第二,20世紀初期出現(xiàn)了社會運動制度化的可能和跡象。隨著英、法、美等國改革政治體制,公民政治權利不斷擴大。政治環(huán)境的改變促使社會抗議運動的行動方式逐漸轉型,社會運動的手段和形式有了較大的調(diào)整,更多地選擇非暴力形式作為抗議手段,這一變化為社會運動制度化提供了可能性,但這一時期還沒有出現(xiàn)真正的社會運動制度化。第三,20世紀中后期進入新社會運動階段以后才逐漸出現(xiàn)社會運動制度化的趨勢。西方主要國家不斷進行政治體制改良,階級矛盾緩和,階層結構改變,以中產(chǎn)階層為主體的社會運動的宗旨和目標發(fā)生了較大變化,政治革命性目標逐漸消弭,生活價值性目標凸顯,鑒于此,代表國家制度的法律條文和行政規(guī)定對社會抗議運動的容納力有所提高,政府對游行示威、公開集會等表達或抗議行動的接受度也有所提高,運動參與者與政府的關系也在發(fā)生變化,社會運動制度化成為一種可能降低國家和公眾成本的雙贏選擇。查爾斯·蒂利在《社會運動:1768—2004》一書中,通過對一些西方國家社會運動發(fā)展史的深入研究,從另一個側面展示了社會運動形式的變化歷程,進而揭示出新社會運動在發(fā)展中自身運動形式逐漸被體制和制度影響的過程。
(二)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
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是在幾種復雜力量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一方面,它自身不斷努力在現(xiàn)有體制內(nèi)促進社會變遷,制度化是其現(xiàn)實選擇之一;另一方面,現(xiàn)有體制如果認為這種制度化有利于緩和社會危機和矛盾,也會努力促進其走向制度化。新社會運動本身并沒有抵制這種制度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于制度化的運行模式。這種制度化主要包含三方面內(nèi)容:
第一,對現(xiàn)有體制的一定認同。新社會運動對現(xiàn)政權的沖擊程度顯然小于之前任何形式的革命,包括傳統(tǒng)工人運動。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反倒對現(xiàn)存社會制度的改良變遷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世紀60年代的青年學生運動、70年代的民權運動、80年代的生態(tài)運動、90年代的反全球化運動以及21世紀初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這些社會抗議運動如果發(fā)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極有可能會演變成為政治革命,而在西方國家的現(xiàn)有制度體系下,這些運動雖仍保持著一定的社會沖擊力和相當大的社會影響,但大多數(shù)運動最終都以和平收場,而執(zhí)政者卻通過社會運動的爆發(fā)和運行過程,更多地發(fā)現(xiàn)執(zhí)政漏洞,完善執(zhí)政方式。這一切都使新社會運動演變成為改造現(xiàn)有體制和制度的原動力之一。
第二,促使現(xiàn)有制度增強對運動的容納度。實際上,社會運動制度化就是各種社會運動被吸納進國家制度框架中,在此過程中各種運動在組織結構、行動方式等方面與現(xiàn)有體制產(chǎn)生一定融合,這一過程也是促使現(xiàn)有制度本身不斷調(diào)整、增強對社會運動的容納力的過程。在英、美、法、德等國,隨著暴力運動逐步減少,國家在法律和制度層面逐步接納非暴力的運動形式,一些運動形式也被社會大眾所采納和接受,社會運動最終成為社會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
第三,運動形式逐漸走向預期化。社會大眾對運動形式、運動主題、運動影響甚至政府的反應都形成一定的預期,運動形式的常規(guī)性展示過程和政府的常規(guī)性應對模式,已經(jīng)被社會公眾所采納和接受。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符合馬克·G·朱格尼和佛羅倫薩·帕西對社會運動制度化的界定:第一,社會運動與國家政黨進行溝通博弈,使其允許社會運動進行信息傳播、見解發(fā)布以及政策建議等活動;第二,整合后的社會運動被賦予一些執(zhí)行政策的權責;第三,通過代表和授權,社會運動進行決策和實施活動。[6](P81-107)也就是說,社會運動的制度化一般會通過博弈、整合以及實施三個階段得以實現(xiàn)。
二、新社會運動制度化趨勢的現(xiàn)實展現(xiàn)
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趨勢主要體現(xiàn)在運動的表現(xiàn)形式、組織過程,以及運動與體制的互動走向常規(guī)化和模式化等方面。
(一)運動形式趨于規(guī)范化
從新社會運動的發(fā)展歷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雖然各種運動主題不同、參與群體各異、運動方式獨具匠心,但是,諸多類別的社會運動經(jīng)過多年發(fā)展后,逐步具有了“常備劇目庫”。此劇目庫中包括很多可選“劇本”,諸如“為特定目標組成的專項協(xié)會和聯(lián)盟、公開會議、依法游行、集會、示威、請愿等政治行為方式的隨機組合”[7](P4)。即使是驟然發(fā)生的抗議運動,大多數(shù)都是采用了劇目庫中的備用模式,社會運動從以往的不可預期狀態(tài)轉化為可預期模式。因此,新社會運動出現(xiàn)“制度化的重要標志是集體行動方式發(fā)生了變化”[8](P172),其典型表現(xiàn)是各種社會運動的運動方式正在趨向規(guī)范化。經(jīng)過幾十年的運動實踐,運動參與者在運動開始之前往往會對抗議活動的發(fā)展軌跡和運動模式做出一定的研判,在訴求目標、運動過程和活動結果方面會有一定的預期,而且傾向于采用多年形成的相對穩(wěn)定和相對規(guī)范的運動模式。
(二)運動組織傾向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
一方面,一些社會運動所涉及領域的專業(yè)性較強,如生態(tài)運動和反核抗議運動等,各領域的專業(yè)人員和資深人員時常會扮演運動理念的提出者或實踐問題的發(fā)現(xiàn)者的角色。這些人員的參與使抗議活動的發(fā)起和組織不像傳統(tǒng)工人運動那樣高度團體化和組織化,但專業(yè)化色彩更為突出。因為他們的學識理念、職業(yè)素養(yǎng)對活動主題和活動過程有較大影響,而且,他們身份職業(yè)的體制化和專業(yè)化,也使得一些社會運動體制化、專業(yè)化傾向明顯。
另一方面,隨著政府對社會運動進行規(guī)范管理的要求越來越高,各種規(guī)定越來越細化,為了適應這種變化,使各種類別社會運動的組織更為高效,運行更為有效,這些要求已經(jīng)促使社會運動的組織行為有了職業(yè)化的趨勢,在美、法、德等發(fā)達國家出現(xiàn)了全職的社會運動經(jīng)理人和組織者,他們?yōu)閷崿F(xiàn)抗議活動的目標提供劇本化的策劃和組織,各類運動主體往往會在他們的運動策劃下參與行動。這些因素都使新社會運動具有更強的專業(yè)化和職業(yè)化特征。
(三)運動與體制互動走向模式化
各國政府的相關政策和法律一般會要求各種社會運動按照規(guī)定程序進行報備。這些規(guī)定改變了運動與體制的關系,使運動成為體制存在狀態(tài)的一部分。報備后的社會運動與體制之間形成了新的互動模式。政府和運動參與者之間正在逐漸相互容納并逐漸相互適應。由于新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常常會選擇組織化程度較低的方式,抗議活動的凝聚力較差,破壞力相對較小,因此,警方所采取的應對方式較為寬容,所以,抗議者與警方之間發(fā)生激烈沖突的可能性較小,二者之間爆發(fā)暴力對抗的概率相比傳統(tǒng)工人運動較低。另外,運動所造成影響的可預測性,也使得警方的預判能力提高,危機管理能力隨之加強。近些年,在反全球化、抗議氣候變化及抗議金融危機運動中,也偶爾會發(fā)生抗議者與警方的沖突,但是大規(guī)模極端暴力的沖突數(shù)量正在減少。
總的看來,新社會運動之所以會形成制度化趨勢,是因為“社會運動自有其制度化的基礎條件。實際上,社會運動是和政黨、利益集團類似的政治參與形式。只不過,政黨和利益集團的組織性更強,其所代表的人群更加明確。而社會運動所代表的人群也許更加多元。回想歷史上政黨和利益集團也曾被視為政治不穩(wěn)定因素,但最終都被納入制度化的軌道而成為常態(tài)參政機制”[9]。
雖然走向制度化是新社會運動發(fā)展的趨勢之一,而且近些年來在發(fā)達國家各種社會運動制度化現(xiàn)象頻頻出現(xiàn),但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運動最終都會完全制度化,某些社會運動可能只在一定程度上被制度化。新社會運動制度化的程度,大致有三類:“第一類是可能獲得某種路徑進入主流政治和文化體系,但是運動自身的訴求程度可能會被削弱;第二類是運動自身放棄進入主流政治體制發(fā)揮影響的目標,轉而從事更基礎的工作,致力于在參與者中形成清晰的運動觀念和目標認同,形成更深層的影響;第三類則會放棄運動主題或者不再重視運動目標,轉向重視其他問題,運動個體開始關注個人生活。”[10](P130)
三、新社會運動制度化趨勢的深遠影響
新社會運動是一個極為復雜的社會現(xiàn)象,它并不僅僅指那些抗議活動和游行示威,也包括思想主張表達、行為方式倡導等行動,同時,在不同社會運動中還存在差異化的訴求目標、多樣的行動方式以及不同的參與主體。鑒于從具體角度分析新社會運動制度化的影響可能缺乏代表性,因此,我們從社會運動自身、國家體制及社會危機應對機制三個較為宏觀的視角進行分析。
(一)新社會運動并沒有因出現(xiàn)制度化趨勢而走向衰落
新社會運動制度化意味著社會運動與國家體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這一過程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人們最為關注的是,制度化是否意味著社會運動所秉持的原則被改變,運動走向衰落?制度化是否對社會運動的抗議性質(zhì)和變革目標產(chǎn)生消極影響?
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在社會運動制度化的過程中,它的確存在被整合甚至被邊緣化的可能,因此制度化往往被視為社會運動走向衰落的起點。制度化對社會運動來說是消極的,它可能會使運動失去其基本特征和有效形式,使運動的組織形式從集群的和分散的轉化為科層的和系統(tǒng)的;使運動目標從激進的轉化為理性的,使行動方式從有沖擊力的轉化為溫和的。其更大的影響是會使社會運動的抗議理念日漸消失,從而逐漸褪去激進的色彩,進而減弱和消除對現(xiàn)有秩序的改變和沖擊能力。
威廉姆·A·甘姆森認為可通過兩個標準判斷制度化運動是否走向衰落:一是制度和體制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挑戰(zhàn)群體的訴求目標。挑戰(zhàn)群體是否成為合法利益的有效代表者,這實際上涉及這一群體的地位和影響。二是挑戰(zhàn)群體及其支持者是否通過參與或支持行動獲得了新的優(yōu)勢。[11](P57-77)從第一個標準關注的目標看,無論是女權運動與反核和平運動還是生態(tài)運動和動物權利保護運動,它們的訴求目標在幾十年的發(fā)展歷程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xiàn),制度和體制在各種運動的沖擊下都有一定的改變。從第二個標準關注的目標看,對于大多數(shù)社會運動參與者來說,只要將自己的意愿和訴求充分表達出來,進而對體制和社會以及社會成員產(chǎn)生相應影響,就能視為達到運動目標,因為大多數(shù)人參與社會運動的出發(fā)點都是希望通過運動的影響,直接或間接地促進體制或制度的改變。
因此,制度化并不意味著社會運動反叛屬性的消失。制度化趨勢對社會運動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人們應該擺脫制度化等同于社會運動被現(xiàn)有體制整合的理念。原因在于,首先,制度化有利于拓寬運動目標的實現(xiàn)途徑。雖然經(jīng)過報備的社會運動的地位是合法的,但是畢竟屬于體制外渠道,制度化的運動在體制內(nèi)拓展了自己的影響。其次,制度化使社會運動可能獲得有利的合法地位。制度化使社會運動有機會在與政府合作和維護運動原則之間保持平衡,這樣的運動有機會在體制內(nèi)與體制外之間進行行動方式的切換和選擇,甚至能夠充分利用不同方式的優(yōu)勢去實現(xiàn)目標。“社會運動進入常規(guī)政治舞臺,可以利用體制內(nèi)政治提供的機會結構施加自己的影響。制度化為社會運動以一種更常規(guī)、更穩(wěn)定的形式在決策、執(zhí)行等環(huán)節(jié)中發(fā)揮影響提供了渠道。總之,不應該簡單地將社會運動的制度化等同于被現(xiàn)有體制收編或運動失敗。”[12]因此,即使出現(xiàn)了制度化,并不標志著社會運動抗議和反叛屬性的消弭。
(二)制度化趨勢表明新社會運動在短期內(nèi)仍無法撼動資本主義制度
雖然各種新社會運動促進資本主義社會產(chǎn)生變革的目標及其抗議屬性,并未因其出現(xiàn)制度化趨勢而發(fā)生改變,可是,形成制度化趨勢這一現(xiàn)實卻表明,新社會運動在短期內(nèi)仍無法撼動資本主義制度。原因如下:
一方面,資本主義國家和政府在不斷進行改良的同時,一直在努力利用制度化減緩社會運動帶來的沖擊。社會運動制度化暫時減緩了它們的壓力,它們也在努力促進這種制度化的形成。只要能夠將社會運動的行動方式保持在非暴力狀態(tài)之中,將運動參與者的訴求納入制度化軌道,成為體制內(nèi)的政治表達,使其在國家政治發(fā)展中發(fā)揮可控的作用和影響,至少暫時可減緩運動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沖擊。因此,許多西方國家在促使社會運動制度化方面一直秉承著較為積極的理念,這也是新社會運動出現(xiàn)制度化趨勢的深層原因之一。而且,一個國家面對挑戰(zhàn)現(xiàn)存制度的社會運動,能否將其制度化,或者能否在不傷及制度體制、價值原則的基礎上擴大和開放自己的政治體系,將其納入體系之中,使之在可控的范圍和趨勢內(nèi)發(fā)展,這檢驗著國家和政府應對社會危機的能力,這些國家都不想在這方面表現(xiàn)出自己的低能。經(jīng)歷了近半個世紀的各種社會運動的沖擊,發(fā)達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體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其基本制度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穩(wěn)定性和容納力。在德國生態(tài)環(huán)保運動中誕生的綠黨,從最初的挑戰(zhàn)者角色最終進入國家政治體制,成為國內(nèi)三個重要政黨之一,并且成為聯(lián)合執(zhí)政黨的事實就體現(xiàn)了這一點。但是,也有一些國家是在付出了較大代價之后才保持了制度的相對穩(wěn)定,在抗議金融危機運動中,意大利、希臘等國都是在社會運動的沖擊下,付出了政府解散、政黨輪替的代價才消解了社會運動的沖擊,暫時維護了資本主義制度。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政黨體制和民主制度也在不斷調(diào)整與社會運動的關系,努力降低社會運動帶來的挑戰(zhàn)。各種社會運動的頻繁爆發(fā)對傳統(tǒng)政黨體制和執(zhí)政方式帶來了極大的壓力。在階層結構日趨復雜、階級意識日益淡化的背景下,傳統(tǒng)的依靠階級主體支持的政黨體制和執(zhí)政方式已經(jīng)不再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尤其是隨著新社會運動影響領域的日益拓展,執(zhí)政黨為穩(wěn)定政局,不得不調(diào)整傳統(tǒng)理念,轉變執(zhí)政方式,擴展階層基礎,采取“中性政治”改革措施。因此,轉變傳統(tǒng)的認同方式和執(zhí)政方式,將抗議和異己力量納入自己的政治體系,成為執(zhí)政黨的最優(yōu)選擇。政黨體制的這種改變,對社會運動也產(chǎn)生了影響,使得“同政黨建立密切關系是社會運動實現(xiàn)制度化的重要渠道之一”[13]。同時,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也改變了社會運動與民主制度的關系。從新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實踐看,各種抗議性運動更可能發(fā)生在民主制度下,查爾斯·蒂利和西德尼·塔羅甚至有這樣的判斷——世界上大部分社會運動發(fā)生在“強能力的民主政權”[14](P71)之中。實際上,這對執(zhí)政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須具備在現(xiàn)有民主體制下將社會運動制度化的能力。
(三)制度化趨勢推動了危機應對體系的完善卻無法根除危機
總體看來,各種社會運動的爆發(fā),本質(zhì)上仍是社會危機的一種體現(xiàn)。西方發(fā)達國家在社會危機管理及風險應對等方面已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論認識和較為系統(tǒng)的實踐舉措。新社會運動的深度發(fā)展和制度化進程進一步推動了這種危機管理意識的形成和管理體制的完善,但是,無論怎樣的危機應對體系都無法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危機。
烏爾里希·貝克等學者從社會危機管理以及風險社會產(chǎn)生根源入手,分析了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中存在的危機與風險,以及這些危機與風險如何促進了危機管理意識的提高和管理體制的形成。1992年,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走向一種新的現(xiàn)代性》一書中首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并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風險在于全球化的推進和后現(xiàn)代狀態(tài)的形成,這些因素加劇了社會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西方發(fā)達資本主義社會已是一個“風險社會”或者已進入“風險時代”。斯科特·拉什指出:“現(xiàn)代的政治和經(jīng)濟制度實際上促成了各種風險的大量產(chǎn)生,這些風險包括自然生態(tài)方面的風險和其他已被察覺和認知的風險,與此同時,現(xiàn)代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制度和規(guī)范仍然在發(fā)揮著作用,并繼續(xù)導致各種風險的形成。”[15]他們還認為,由于社會進步所帶來的副作用和負面效應,現(xiàn)代社會還將不斷產(chǎn)生新的更大的風險。
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管理,我們還可以從哈貝馬斯有關政治危機的觀點中得到啟示。哈貝馬斯認為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密切相關,政治危機會導致或加重社會危機。因此,加強對政治危機的研究和分析有助于對社會危機管理的重視。他強調(diào),政治危機包括合理性危機和合法化危機。合理性危機是由行政機關等國家機器無法有效和高效地履行經(jīng)濟職能所造成的,屬于行政管理能力危機。他說:“公共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缺乏意味著在特定的邊界條件下,國家機器不能有效地調(diào)節(jié)經(jīng)濟系統(tǒng)。”[16](P47)關于合法化危機,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和《現(xiàn)代國家的合法化問題》等論著中對這一危機形式做了詳盡的論述:“合法性意味著對于某種要求行為正確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認可的政治秩序來說,有著一些好的根據(jù)。一個合法的秩序應得到承認。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17](P184)合法化危機表現(xiàn)為一種社會認同感危機,是公眾對現(xiàn)存政治體制社會制度信任度降低,屬于忠誠度不足方面的危機。他說:“合法化的缺乏意味著不可能通過行政手段將規(guī)范結構維持或建立在所要求的范圍上。”[18](P47)依據(jù)對這些風險社會和危機理論的認識,在新社會運動的不斷沖擊下,西方國家的社會危機管理意識不斷增強,應對措施亦不斷完善,社會運動制度化,即是在危機管理意識增強的背景下,國家和政府采取的有效應對策略之一。
從表面上看,隨著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危機應對意識的提高和應對舉措的加強,新社會運動制度化似乎意味著它被資本主義體制收納了,實際上,作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己力量,新社會運動這種制度化趨勢是在資本主義體制內(nèi)通過發(fā)展空間的拓展和存在時間的延續(xù),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作為西方發(fā)達國家中最具有社會主義特征的社會力量,新社會運動制度化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削弱作用不可低估。這是因為,一方面,新社會運動的街頭抗爭只是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的一個凸顯階段,各種運動背后都隱藏著深層次的制度矛盾,而且這些矛盾無法被徹底根除。雖然某一次或某一時期的抗議運動不會使資本主義制度傷筋動骨,反而會促使其不斷調(diào)整并完善危機應對機制,但是,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不會因為應對機制的完善而得到徹底消除,反而會因為實施這些短期措施而掩蓋深層危機,表面上看問題似乎解決了,但深層危機卻在繼續(xù)發(fā)展。新社會運動的制度化意味著它對資本主義制度會長期發(fā)揮削弱作用,這一切最終將危及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發(fā)達國家由于社會運動的壓力不得不進行改良和調(diào)整,它為維持制度的存在而不得不采取有利于更多人利益的舉措,這些政策和措施往往帶有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不斷積累,由量變到質(zhì)變,進而產(chǎn)生社會制度的更迭和社會形態(tài)的進步是可以預期的。
雖然新社會運動存在制度化趨勢,但從新社會運動的發(fā)展歷程來看,并不是所有的社會運動都會被制度化。一方面,一場社會抗議運動的產(chǎn)生原因、發(fā)生背景、抗議主體、宗旨目標、組織結構、動員形式都會對其能否出現(xiàn)制度化產(chǎn)生相應影響;另一方面,某一時期政府的觀念立場、執(zhí)政狀況和社會壓力都會對其是否選擇與社會運動媾和有較大影響。這些復雜因素會導致某些社會運動幾乎不存在制度化的可能。英國撒切爾時期出現(xiàn)了1984—1985年礦工大罷工,罷工工人立場很堅定,而撒切爾政府也絕不妥協(xié),最終以抗議行動失敗而宣告罷工結束,英國礦工工會的政治權力被部分剝奪,其影響力也被極大地削弱。由此可見,社會運動制度化是社會運動各要素和國家制度各要素在某些層面或某一階段出現(xiàn)目標和利益認同的結果,其實質(zhì)是一個國家的體制構建目標和社會運動的訴求目標互動博弈的過程,如果博弈過程破裂,社會運動就不存在制度化的可能。
四、對新社會運動發(fā)展趨勢的展望
新社會運動雖然是當今西方發(fā)達國家最具有上升潛力、影響最大的一種社會運動,但在走過近半個世紀的歷程之后,當前它正遭遇發(fā)展困境。其主要表現(xiàn)為理論基礎龐雜、發(fā)展路徑不清晰、主導力量不明確、組織形式不規(guī)范、抗議手段低效率等。只有直面發(fā)展困境,深入分析各種因素的影響,找到擺脫困境的出路,新社會運動才有未來。從發(fā)展趨勢上看,除了本文分析的制度化趨勢之外,新社會運動還可能走向組織化、非暴力化和全球化,同時,它還存在與社會主義運動聯(lián)動的趨勢和可能。
第一,組織化趨勢。相對于20世紀中后期的新社會運動,21世紀出現(xiàn)的以反對金融危機運動為代表的新社會運動表現(xiàn)出了較強的組織性和計劃性。尤其是以反抗政府及其政策為目標的一些抗議運動的組織性越來越強。各國的在野黨、左翼黨派、工會及一些社會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在運動中的組織作用有回歸和加強的趨勢。近些年多次出現(xiàn)的法國大罷工的主要策劃者就是法國聯(lián)合工會,它確定了罷工計劃和抗議目標,并制定了具體罷工方案。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同樣展示了運動組織化的威力。
第二,非暴力化趨勢。新社會運動主張采取以非暴力和文明表達為特征的抗議方式。多數(shù)新社會運動參與者都反對采用暴力手段實現(xiàn)其訴求,摒棄傳統(tǒng)工人階級的武力反抗或者極端民族主義者的恐怖活動等暴力手段。“非暴力主義”正在成為新社會運動中各團體、各組織不約而同采取的行為原則和斗爭策略,在發(fā)展走勢上,這種非暴力趨勢將更為明顯。
第三,全球化趨勢。全球化因素對新社會運動發(fā)展的影響在不斷增強。尤其是新社會運動高度關注的一些問題,如移民問題、生態(tài)問題、恐怖主義等問題的產(chǎn)生和解決都已經(jīng)跨越國界,因這些問題所引發(fā)的社會運動也呈現(xiàn)出明顯的全球化的趨勢。這一全球化趨勢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新社會運動的發(fā)展呈現(xiàn)出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趨勢,甚至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跨國聯(lián)合的反全球化運動。二是民族國家內(nèi)的各種社會運動同樣也受到全球化因素的影響。那些受到全球化影響的個人、組織和團體都在努力尋找自身的定位,包括尋找國家和社會在全球化中的發(fā)展方向,同時努力通過社會參與引導全球化進程朝著對自己國家有利的方向發(fā)展。
第四,與社會主義聯(lián)動趨勢。新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可能會走向聯(lián)動。一方面,雖然新社會運動的興起弱化了發(fā)達國家中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和實踐都構成了挑戰(zhàn),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又以自身獨具特色的現(xiàn)實表現(xiàn)彰顯了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追求。同時,由于缺乏先進理論的指導,新社會運動的行動方式和訴求目標中也存在一些缺陷,顯然,它需要社會主義理論的補充和引導。另一方面,傳統(tǒng)社會主義運動要繼續(xù)發(fā)展,就應吸納新的思想理念和行動方式,并構建與新社會運動的密切聯(lián)系。發(fā)達國家中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它如何確定自己與新社會運動的關系,新社會運動很可能成為社會主義變革任務的主要承接者。這兩方面因素表明,新社會運動與社會主義之間相互需要,存在聯(lián)動發(fā)展的趨勢。正因為如此,新社會運動的未來與社會主義運動的發(fā)展之間,展現(xiàn)出密切關系和多種可能。
[1] Hank,J.and M.Alberlt.NewSocial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道格拉斯·C·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jīng)濟績效》,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8。
[3][4] 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9。
[5] 《大辭海·政治學、社會學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6] Marco G.Giugni, and P.Florence.“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mplex Societies: New Social Movements betwee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Marco G.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FromContentiontoDemocracy.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1998.
[7] 查爾斯·蒂利:《社會運動:1768—200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 Patricia L.H.“Democratic Transition as Protest Cycles: Social Movement Dynamics in Democratizing Latin America”.In David S.Meyer and Sidney Tarrow.TheSocialMovementSociety:ContentiousPoliticsforaNewCentury.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8.
[9] 唐昊:《社會運動的制度化可能》,載《南風窗》,2015(1)。
[10] David S.Meyer.ThePoliticofProtest:SocialMovementsinAmerica.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 William A.Gamson.“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Change”. In Marco G.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FromContentiontoDemocracy.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12][13] 丁曄:《從國家與社會運動的互動看社會運動的“制度化”》,載《國外理論動態(tài)》,2013(9)。
[14] 查爾斯·蒂利、西德尼·塔羅:《抗爭政治》,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15] 斯科特·拉什:《風險社會與風險文化》,載《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02(4)。
[16][18] Habermas, J.LegitimationCrisi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5.
[17] 哈貝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責任編輯 林 間)
An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of New Social Movement in the West
MENG Xin
(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Socilism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91)
New social movement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social movement in the West.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to shape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one of its trends of development.The institutionalized social movement is in essence the resul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goal of stat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target of social movement.The process not only transforms social movement, but also has profound impacts on state system and social crisis governing mechanism.In terms of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nearly half a century, the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did not change the protest attribute or the reform objective of the new social movement.It is still the transformative power with the most distinguished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ism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new social movement; state system; institutionalized; trend
孟鑫: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北京 100091)